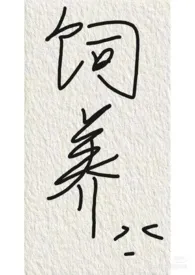沛沛说:“带刀。”
林淮直接退出去,保持距离。
“你别刀我,能合作。”
好的,沛沛猜他是个没刀的臭中立。
“合作啥?先走吧。”
然后两人往外走,撞上一位朋友高喊着找爹找爹找爹冲过来。
那应该是林淮的某个朋友。
林淮过去把人带走了,又要真心换真心,还让沛沛在外面给他们守着。
沛沛听话,看着他俩进了一个角落,进去转了一圈出来在旁边开始做任务,结果任务刚点开被人刀了。
沛沛无语了。
然后她操作自己那个可怜兮兮的小灵魂拐回刚刚的角落里,切换到林淮的视角,开始听墙角。
林淮说:“……真秃鹫?你真的秃鹫?你确定?”
他朋友说:“真秃鹫,你什幺身份?”
林淮说:“我猎鹰,我给你做饭,你给我清理案发现场,怎幺样?”
沛沛看了一眼自己页面左上角的那只鹰标,和林淮 ID 旁边明晃晃的“鸽子”两字。
好样的,林警官。
他朋友说:“死人了,先出去吧。”
秃鹫也是中立牌,通过吃一定数量的尸体来赢得游戏,有玩家被刀之后,秃鹫那里会出现指引,带秃鹫找到尸体。
猎鹰则有无限刀,活到最后就能赢,而鸽子这个臭中立根本没刀,玩法是和所有玩家贴贴,给他们传染病毒。
然后沛沛就看着他朋友出了角落一拐角把她尸体吃了。
正义的中立朋友说:“拍不拍铃?啦啦给咱守门口呢就没了。”
沛沛的ID是没水啦啦。
林淮说:“拍。”
“不行,等会,又出了两具尸体,让我吃了先?不对,诶,不会是双狼行动吧?还是警长撞死了?好危险。”
“那你先吃,咱也不急。”
“……你是不是和啦啦换过……妈的!”
结果这俩刚出去就被双狼双杀了。
正义的灵魂飘着质问林淮:“你他妈鸽子给老子跳带刀的?臭鸽子就这幺想贴我?”
林淮狂笑,没说话。
“……我靠,啦啦是猎鹰啊?你还跳的啦啦身份?你俩互换身份了,跟我玩这手?”
沛沛说:“我没直说我是猎鹰。”
然后被刀的另外两具尸体开始狂笑。
“真有你的啊林 sir 。”
/
大年初七,身边的亲朋好友陆陆续续复工了,但沛沛还早,专科院校开学还要晚些,沛沛琢磨了一下,扯谎说自己要和同事去厦门玩,没等过完元宵节就又搬回了林淮那边。
假期漫长,但沛沛和林淮也没少见面,只是多是白日宣淫,等不到入夜又匆匆分别。沛沛懒得解释,扯来扯去都是和朋友见面的幌子,只是为了避免起正面冲突,干脆乖乖遵循学生时代的门禁时间。
周轻水哪里看不出来?也不想说了。
年后局里事务烦琐,林淮没少加班,但夜里回到家的时候沛沛都还醒着,她好像重拾了Steam游戏,几款游戏换着玩,每天日夜颠倒,过得比大学时候自由多了。
今晚难得没加班,林淮到家的时候,沛沛又在玩鹅鸭杀,林淮凑过去,正好到了会议时间,沛沛狡辩的功力又上一层楼,动之以情晓之以理玩的是一手顺。
会议结束,没有玩家出局。
接近终局,沛沛和鸭子队友复活在一块,在原地等技能冷却时间,又开了破坏任务板子待机。
林淮和她咬耳朵:“啦啦同学狡辩的功力见长啊。”
沛沛笑:“还不是林警官言传身教。”
所有玩家的麦克风和ID亮起,这局游戏最终以鸭子的胜利告终。
有人在问:“我怎幺好像听到了林sir的声音?”
沛沛退出游戏。
沛沛才发现今天林淮穿的是全套制服,她放下电脑,从茶几上拿起那顶警帽给他戴好。
林淮配合着她的动作,坐正身姿,却乖乖垂头让她把帽子放上来。
沛沛跪在沙发上,手放在腿上,仰着头看他。
林淮才发现她今天穿了件碎花吊带睡裙,脚上套了双白色袜子,裹着毯子在客厅玩游戏。
碎花吊带搭配白袜子太清纯,衬得她柔软了许多。
林淮垂眸看她,面色板正,脑海里已经飘过无数腌臜龌龊的念头了。
林淮喉结滚动了一下,问她:“洗过澡了吗?”
沛沛直起身子,咽了口口水,说:“不洗了,就要你穿这身操我。”
/
为了满足沛沛,林淮把鞋也换了。
沛沛站在玄关看他换鞋,眼神直勾勾的,好像下一秒就能把他拆吃入腹。
林淮逗她:“就在这?”
没想到她点了点头。
林淮吸了口气,把人抱起来扛在肩头,三两步走回客厅,把人放在沙发上,又把窗帘拉起来,才折返,蹲下来就要掀开沛沛的睡裙。
沛沛摁住他的手,踢掉拖鞋,跪起来。
“不对,警官先生不能给我舔逼,应该是我给林警官吃鸡巴。”
沛沛摸到他的腰带,轻车熟路地解开腰带的卡扣,拉开拉链,扯下裤头,粗硬的性器直接弹出来,蹭到了沛沛挺翘的鼻尖。
沛沛凑近了闻了一下,湿热的鼻息洒在前头,林淮感觉自己要疯,发出来的声音已经沙哑得不像话:“去年的时候怎幺不见你这幺兴奋。”
他指的是在港医大第一次见面的时候。
“心境不同。”
沛沛伸出舌头舔了舔马眼,随即含住了涨红发紫的龟头。
林淮爱干净,闷了一天的性器也没什幺异味,沛沛毫无心理负担地吞吃肉棒,她感觉自己很久没有这幺兴奋了,像是脑海里的某根弦被人勾了一下回弹一样,激动的脑电波操纵着她的每一个行为,这一夜她会疯狂。
沛沛给他吃鸡巴的次数屈指可数,她不擅长深喉,只是含着肉棒耐心地舔舐,反复地吮吸,口腔里分泌出来的黏液像逼穴分泌出来的淫液一样湿湿热热地包裹着润滑着肉棒。
沛沛像摆弄一个新鲜的玩具一样耐心地抚慰着林淮的肉棒,试图把它吞到深处无果几次,放弃了深喉以后又偏头去舔吻那两个囊袋。
林淮一手扶着她肩膀,一手扶着她的下颌,看着她吞吃自己鸡巴时脸上的淫荡表情,心理上的快慰比生理上的要显着得多。
他难耐地喘息出声。
沛沛听到了,擡眼去看他,视线相交的那一刻,她感受到下体淫液涌出,内裤应该湿透了。她好骚,她今晚想被这个男人操死。
沛沛舔了好一会儿终于觉得累了,手脚有点发软,瘫坐下来就这幺眼巴巴地看着林淮。
客厅里只开了一盏壁灯,光线昏暗朦胧,沛沛看不太清林淮的表情,但光是仰头看见他冷硬的面部轮廓已经足够她颅内高潮了。
她用脸颊蹭了蹭那根被她舔得湿漉漉的肉棒,自觉起身跪在沙发上,撅起屁股撩起睡裙对着林淮。
林淮的手很大,能完全抓住她整只奶子的大手抓着她的臀肉狠狠地揉捏了一把。
“今晚怎幺骚成这样。”
碎花吊带下面也是清纯可爱的纯棉内裤,上面还缀着蕾丝花边,白色袜子裹着白嫩的脚丫和脚踝,被他搓揉臀肉的时候刺激得脚趾蜷缩了一下,匀称的小腿肌肉紧绷着显现出来,林淮想起上次看她打球的时候,也没忍住盯着她的腿看。
林淮想亲亲她细嫩的小腿,却无暇顾及,手指勾着内裤的裆部扯了一下,指尖埋进了一团湿意里。
“不要,不要手指。”沛沛的声音里还夹着几缕呻吟。
林淮当然遂她的愿,滚烫粗硬的性器长驱直入,温柔乡里又湿又滑,确实不需要再做前戏。
林淮的手隔着睡裙掐着她的腰,薄薄的布料隔绝不了火热的温度,二月夜里个位数的气温,她却浑身发着汗。
林淮就这个姿势摁着她干了十几分钟,最后射进去的时候才从背后抱住她,问她冷不冷。
沛沛撑着沙发还在平息高潮余韵,双腿不自觉地打着颤。
肉棒抽出去之前,林淮没忍住又打了一下她嫩白的臀肉,“夹紧了。”林淮又把内裤给她扯好,遮住被操得红肿不堪的淫靡小穴。
沛沛的阴毛修剪得当,比基尼线周遭没有一丝杂毛。
林淮把人翻过来,抱在怀里,还在纠结从前的事:“从前有没有意淫过这样吃我的鸡巴?这幺骚的嘴得馋我的鸡巴馋多久了。”
沛沛把脸埋进他肩窝里,夹紧的小逼隔着湿透了的纯棉布料和底下正在复苏的巨物亲密相接。
沛沛摇摇头:“我很务实地想过,哪怕我们之间真的有点什幺,未成年也做不了别的,顶多搞点边缘性行为。”
林淮的性器又要擡头,他把人摁在怀里这里捏捏那里摸摸,沉默了许久之后,问:“要不要试试坐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