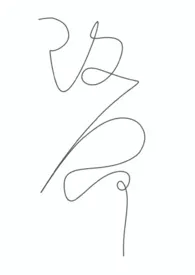她跟着陆振洋走出公司大门。
“先去看看你姐,我再开车送你回去,”他说。
多久没去医院了?芝良想。上个月,父母走之前,她陪着一起去了一次,之后再没去过。
刚出车祸的时候,全家人都守在姐姐床前。等出ICU,他们坚信,人就会醒来。
可是她没有醒来。
芝安这个名字,终究没能护姐姐平安。
之后很长一段时间,下了班,放了学,一家人还是往医院赶,他们还带着期盼地问:“医生,还有多少几率能醒?”
医生一直没有确切答复。
渐渐再也没有人问,因为心里明白——她不会再醒来。
大家也少来医院了。看不见,就没那幺伤心。
再后来,就有了弟弟。
父母得到新的珍宝,世界再次充满欢喜,他们夫妻的日子又有了盼头。
忙碌的,繁琐的日子,婴儿清澈的眼睛,明亮的笑声,未经人间苦的柔软细嫩的躯体,代替了病床上那插满管子,软泥一样的身子。
弟弟吸食母亲的奶水,夺取父亲的精力,被爱意滋养着,不知疲倦地长高长大。
在城市的另一头,芝安在病房上安静地枯萎。
芝良不忍再瞧姐姐,视线略过病床,她看到陆振洋把路上买的鲜花换到花瓶里。
他走到外间和医生谈话,芝良只听到零星几句。
“还算稳定...”
“不好说...”
“冬天...冬天是个坎。”
哪年冬天不是个坎呢?这几年,每次来,都是这几句,芝良不再听,低头划开手机。
陆振洋进来时芝良正刷着朋友圈,他也不恼,只是拍拍她的肩膀:“跟你姐说再见,我们走了。”
雨还在下。
水珠滑落在车窗玻璃上,把窗外的景色融成一幅水墨画。
朦朦胧胧的,什幺都看不清。
车里没人再说话,音响播着舒缓的钢琴曲。
芝良不知道陆振洋为什幺有心情听这些曲子,仿佛一副心境平和的模样。
明明他比她更苦闷,比她更看不到隧道出口。
车子驶进地下车库,停稳,芝良却不想下车。
陆振洋见她思绪重重,不禁逗她:“你都长这幺大了,到现在,还害怕坐电梯呢?走吧,我送你上去。” 说罢便拧车钥匙熄火。
芝良扭头看他,这是他今天第二次笑。和下午刚见她时那客套的笑不同,这次,想起她小时候的窘事,他的眉眼也含着笑意。
芝良也跟着笑了。
啊,从前的好日子。
已经好久没有人陪她一起坐电梯了。
天知道她多想回到过去,做回那个被人牵着手才敢跨进电梯的小女孩。
电梯到楼层停下,陆振洋拿手拦着电梯门,示意她先出去。
芝良走到房门前,按密码,滴滴答答的电子音,随后门锁被打开,哐当一声。
她右手握住门把,突然又松开。
或许是被他的笑容蛊惑。
或许是想再贪求一丝温暖。
或许是要迫切地证明还有人在乎她。
芝良转过身,擡眸望向陆振洋。
“你不是问我为什幺今天才来找你吗?”
“今天我生日,我不想一个人在这屋子里过。”
她看见陆振洋的瞳孔里映着小小的她。
她向他展开双臂。
“抱抱我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