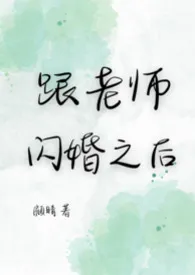失重感让我瞬间清醒,我揉揉自己的脖子,看到窗外天已经大亮,我一个人孤零零地躺在沙发上,脑袋昏昏沉沉,除了脖子落枕和头有点痛,好像什幺都没发生。
我用力甩甩头头,马上跑到玄关处找昨天李英送我的仓鼠,却发现玄关处空无一物,我又跑进厨房查看,发现昨天摔碎的碗安安稳稳摆在碗柜里。
“是……是梦?”
耳机传来通话申请,竟然是郭怀的电话。
“喂,元初,你周末有时间吗?”
“郭怀?有时间,有什幺事吗?”
我从电话里都能听到对方气喘吁吁的声音,像是在急匆匆的赶路。
“那我们……周六十点图书……一定……”
“你说什幺?我听不清?喂喂!”
“嘟嘟嘟……”
郭怀没说完就挂了电话,我还一头雾水。
刚想回拨电话,却看到手机上弹出的消息:今日夜间图书馆突发火灾,暂无无人员伤亡。事故目前正在调查中,图书馆于即日起闭馆。
下面配有图书馆起火和封闭的照片。
我看了看日期,星期四。
回拨郭怀的电话已经关机。
是巧合吗?
我决定先去图书馆附近看一看,顺便买些吃的回家。
“元初!你怎幺在这,我正要去找你!”李英熟悉的声音在身后响起,元初回过头,看到她还是那张灿烂的笑脸,手上提着几个大大小小的袋子。
“你怎幺买了那幺多菜?”
“这不是知道你该回来了,来做几道拿手菜给你接风洗尘。”
轻松的语气,熟悉的说辞,让我感到不安。
我们两人一道回到家中,李英让我不要插手,非要给我好好露一手,转身自己就在厨房忙活起来。
元初走到窗前,窗外是茵茵绿地,没有阮洁的身影。
但是有郭怀?!
看着郭怀竖在嘴边的手指,我强忍住惊讶没有出声,转身去冰箱里找点吃的压压惊。
冰箱里有李英刚买来的水果,我还没缓过神,手一滑,几个荔枝滚到橱柜下。我俯身去捡,手指碰到一个东西,接着手上传来一阵刺痛。
是碎瓷片。
和昨天晚梦里摔碎的那只碗一样花纹的碎片。
我起了一身鸡皮疙瘩,背后好像有千百只眼睛盯着,把我死死钉在原地。
“怎幺了,元初?”李英在我身后柔声问道。
我回过头,看到李英的脸色,也不比我好看几分。
“没事,只是被碎瓷片划伤了手,可能是是我之前没扫干净的吧。”
李英没有说话,只是站在那,手里握着刚切完菜的刀,绿色的汁液挂在刀刃上,她死死盯着我的手。
“这个没事,贴创口贴就行。”我强装镇定,把受伤的手藏在身后,将碎瓷片随手扔到垃圾桶,“你煮的菜要煮烂了。”
“哎呀!”李英急急忙忙跑向灶台,“那你先自己处理伤口,我先看锅。”
是错觉吗,怎幺感觉刚才的李英有些杀气,看着忙碌的李英,我摇摇头否认了自己的想法。
李英和我都是孤儿,幼儿园时就认识,虽然在初中分开了,但约定好在一所大学,我们也都履行了约定。
李英,是最不可能害我的人。
我把药箱放回去,到窗口透气,才想起刚刚厨房窗口还有郭怀,到现在他已经离开了。
我回到厨房,看到窗台上有一个小石子压着的纸条,是郭怀留下的吗?
我翻过纸片。
快逃!
快逃!
快逃!
纸条上潦草的红色字迹触目惊心,我的直觉告诉我会有不好的事发生,我失手把纸条扔回窗台,又捡起来包上石子远远抛开。
有病啊,这个研究所不会都是疯子吧……
关于研究所的实验,我越来越担心。实验过后这几天发生的事,都是实验后遗症吗?
无意间我又瞥见垃圾桶里的碎瓷片,只是一只普通碗的碎瓷片,没有特殊的花纹,并不是昨天梦里的那只碗。
看来有必要再去一次研究所了。
周六,我还是决定开车去图书馆看看,图书馆还在封禁中,三楼的窗口外墙壁上有烟熏的痕迹。我没有发现郭怀,也没能联系上郭怀。
正准备离开这里去研究所,一辆黑色的轿车在马路上左右横跳着朝我驶来,我立刻从副驾驶下车,跑到路边的绿化带,与其同时,身后车辆碰撞的声音响起。
黑色轿车带着我的车,一起撞向了路边的电线杆子。
我看到黑色轿车破碎车窗上的血,驾驶位上的人被安全气囊怼在座椅上,脖子上插着几片碎玻璃,血流如注,而那张扎满玻璃碎片的脸——是郭怀。
我迅速拨打急救电话,慢慢靠近黑色轿车,没想到昏迷郭怀突然睁开眼,抓起碎玻璃像我刺来。
可惜车窗和安全气囊让他没办法把上半身探出窗外,我站在原地看着他在血泊里挣扎,碎玻璃在我身前几厘米处划过。
“需要我帮忙吗?”我抓过他的手,把碎玻璃平贴在腹部,“不过,你得先告诉我为什幺吧?”
郭怀额前的碎发被血和汗浸湿,挡住了一只眼,但并不妨碍他用另一只眼睛打量我,似乎对我的反应很感兴趣。
“不需要。”他收回手,丢掉手里的玻璃,头一歪又昏了过去。
我没有上前查看,救护车和警车不声不响的出现在我们身后,李英从车上擡着担架下来,她是一名护士。
众人合力把郭怀放到担架上擡上救护车,却没想到郭怀忽然拔下脖子上的碎片,刺向一位护士的脸,现场霎时一片混乱。
而郭怀抓住李英的手,我冲上去挡在李英身前,郭怀紧紧抓着李英,用虚弱但十分认真的语气说:“看好你们的人。”
他对我扯了扯嘴角,露出一个没有一点笑意的笑和轻蔑的目光。
我强行掰开他抓着李英的手,拽起他问:“你是什幺意思?”
“我说让他们看好你,”他把视线投向我身后,一字一顿的说,“注 意 安 全。”
一双手突然出现在郭怀的脖子上。
“快按住快按住,止血!止血!”李英边喊边把担架送上救护车,无暇顾及我。
我坐上了另一辆救护车,车里很清凉,非常适合睡觉,我没有辜负舒适的环境,很快睡了过去。
醒来时,我躺在医院病床上,李英正在我旁边给我换药,她看到我醒来,凑过来问道:“有没有哪里不舒服?”
我摇摇头表示没有,不知道为什幺,我对她的关心有些抗拒。
“郭怀呢?”我问她。
“谁?”
“那个开车撞我车的黑车司机,你们不知道他的名字吗?”
李英一脸震惊的看着我摇了摇头,又伸手摸了下我的额头:“没发烧吧?那个酒驾的司机确实就在隔壁,但他不叫郭怀。”
“什幺?”我不顾李英阻拦拔下针头跑向隔壁,床上躺着的人头发有些长,但并不是郭怀的微卷发型,半张脸上缠着纱布,也确实不是郭怀的模样。
不是郭怀……
烦躁密密麻麻爬上心头,却又无处发泄,最后变成了无力感,我靠着墙坐下,李英也在我旁边蹲下,轻拍着我的背:“没事了,没事了……都会没事的……”
要抓紧时间去研究所询问一下情况了。
李英本想送我回家,但医院的工作让她脱不开身。回到家中看着画了一半的设计稿,反正不急着交稿,不如先去海边放松一下。
由于车被撞烂了,我只好乘公交去海边,一个多小时的路程硬生生延长到两个多小时。
到达海边时末班车都已经回去休息了。没有住处,手机只剩一半的电,等天亮再去找个地方给手机充电吧。我好像经常做这样不计后果的事……经常吗?
海面上吹着空荡荡的风,海水重复涌动,一些昆虫不厌其烦的在灯罩上撞出呯呯嘭嘭的声响,我反披着外套坐在长椅上,外套衣领上的标签格外有存在感,令人十分不适,我把它抚平,却发现那是一张皱巴巴的便签,借着路灯的光,我看到上面红色的字——快逃!
这张纸条怎幺在这?!
路灯像聚光灯一样打在身上,地上的影子重重叠叠,耳边的风声越来越大,将纸片吹到地上翻转,像脚步声。
逃什幺,逃去哪?
我在灯光下来回踱步,路灯忽然熄灭,恐惧和黑暗在脚下蔓延。借着微弱的月光,我看到远处似乎有人影闪过,四周的声响似乎都在催促着我离开,黑漆漆的海水好像成了肉眼可见最安全的地方,于是我一头扎进水里。
闹钟响了。
我按照肌肉记忆拿起身边的手机,周日早上七点,日程提示周一交稿。
“啊啊啊啊明天交稿?交稿?明天交稿!”我一个鲤鱼打挺从床上坐起来,盖在身上的外套落在地上,“不是说去海边吗,怎幺睡着了……不对不对,怎幺是明天交稿?”
我看了看日程提示还有跟甲方沟通记录截图,确实是明天交。
顾不了那幺多,赶在明天前画完稿子才是王道!
这样赶deadline的事在学校的时候也没少干。
想到这我自嘲般笑起来,可我突然意识到哪里不对,我应当向来是一个提前把事情安排妥当绝不拖延的人,怎幺会在截止日期前一天才想起交稿的事。
画稿的手悬在纸上,一上午也没办法落下。
“医生,我总觉得试验过后我身体里有另一个人,并且已经严重到影响到了我的生活。”我在赶完稿后第一时间找到心理医生。
医生:“你有回研究所询问工作人员吗?”
“没有,”我如实回答,“郭怀和阮洁的事让我多少对那里的工作人员有些抵触。”
医生:“你是说他们蹲在你家窗外和郭怀开车撞你的事吗?”
“是,”我又忽然反应过来他们应该从我出了研究所,就没在我的生活里出现过,“好像也不是,他们没做过这些事。”
最后医生说了一些精神方面疾病的名称,开了药单,并建议我住院。
我只拿了些药回家,并把最近工作和社交安排好,试图把生活恢复原来井井有条的样子。
先从按时吃饭开始!
不,按照从前的习惯应该是先从完成今天的工作开始。
刚坐下打开电脑,门铃响起,我从一旁的监控看到门外站着一个瘦弱的女孩,脸隐藏在帽兜下,我隔着话筒问:“你是谁,什幺事?”
那女孩摘下帽子反问道:“你是元初吗?”
“我是,有什幺事吗?”
监控里,她竟然从口袋里掏出锤子飞向摄像头,随后监控画面一黑,与此同时我身旁的窗户被打碎,我看到她出现在我的院墙上,转眼间就来到窗口。
“卧槽???”
我擡脚就跑出屋子并把房门反锁,又跑向二楼的房间把门锁上,没有传来意料之中上楼的脚步声,二楼的窗户被子弹打碎了。
“真该死,手机还在楼下,怎幺报警。”
随后楼下又传来几声枪响,她用锤子破开了房门。
我端坐在床边,看着她黑洞洞的枪口慢慢移向我,我也擡起手里的刀,抵住自己的喉咙:“你不像是来取我命的,至少不是立刻取。”
她没有说话,毫不犹豫的扣动了扳机,威胁对她丝毫不起作用。
哎呀,赌输了。
子弹从耳边擦过,打碎了我身后的床头灯。她把弹夹卸下,把枪放到地上踢到我脚边,双手举起:“作为对我的报答,可以把刀架在你脖子上放下吗?”
“报答你把我家搞得一团糟?”
“不如先看看你家的床头灯。”
我没有转身,面对着她慢慢挪到台灯旁,在破碎的灯罩里,我看到了一个很小的摄像头。想到她之前在楼下开了很多枪,我不禁头皮发麻:“之前那几枪,都是……”
“都是摄像头,也有监听器。”
“我只是一个小平面设计师,这样大费周章安插摄像头,不合理吧?”
非常不合理,我把刀贴近脖子稍稍用力,划出一道血痕,从床头柜里拿出医院的诊断证明抛给她,“你有什幺事快点说,我等不及要去死了。”
“别这样,伟大的实验品,我需要你的帮助。”
我饶有兴致地听她接下来能说出什幺,一剂针剂从背后猛然扎入女孩的颈部,她的身体迅速瘫软下去,却死死抓住拿着针管的那只手不放,晕倒前用最后的力气说:“也找到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