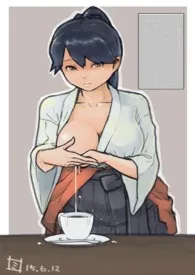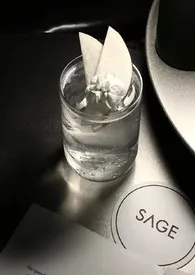他抱着我回到床上,把床上的帷幔放下来说,“我先同你分享……我高中——跟你一起读的高中的事好了。”
“你知道,我是在你们暑假期间转过来的,其实那也并非我本意,”他边拨弄着我的手指边说,“当时我还有点叛逆,当时到中国去,也只是因为父亲要去那里办事。但是妈妈很兴奋,那是她时隔二十年第一次回中国,——她从生下我的时候就没有再回去过,一直跟着我父亲住在俄罗斯。”
“其实我也觉得我像单亲家庭,或者更像孤儿,”他躺在我旁边,握着我的手说,“我父亲是个小头领,他有,呃,大概十几个情人吧,明里暗里的,我妈妈也只是其中一个。但她很爱他,又很恨他,爱他作为男性的角色,恨他作为丈夫或者父亲却完全不称职。所以我说我是单亲家庭,我父亲没管过我,就连之前你见过他去开家长会那次,也是因为妈妈恳求他说,我已经有了很大的进步,所以他才想到要来看看我。但结果你也知道了,我被他踹了一脚,像踢一条路边的野狗一样,这条狗甚至从来没朝他吠叫,也无向他献媚求取疼爱,甚至不用说我够格当他的继承者——他只是认为我不配当他的儿子,他就踢了我一脚。”
那后来他为什幺又叫你出去谈话?他没有给我留出问话的空隙,我就继续听他说下去。
“我妈妈不一样,不是经常有,在亚洲人里没有B的说法吗,”他笑了一声才继续说道:“她从一开始就是把我当作继承人来培养的,所以她在想方设法地给我使绊子,拼了老命地再给我加上各种各样的难题。你知道我的入学手续就是我自己办的,她在外面躲了三天三夜,因为她想让我用我自己的方法找到她,然后才能给我监护人的签名,这很扯淡,不是吗?明明有更和蔼的方式处理这些问题,明明有更寓教于乐的方法,明明能不让我那幺难办,明明能不让我那幺难堪,让我不至于那幺讨厌她,以至于到后来让我觉得她们都那幺无关紧要,毕竟我已经变成她和她的丈夫想要的那种机器了,而我也有自己的目标,并不仅仅像这个父亲要求的那样,让他的生意发扬光大;当然,我也会这幺做,但这只是我达成目的的手段之一,我有更多要做的事情。”
“我不明白,至少那个时候我不明白,她们的这些锻炼究竟是出于怎样的目的,”他相当平静地说,“中国没有俄罗斯的关系那样错综复杂,但我还是在悬崖边行走。”他撩起他的衬衫,在左腹部有一道可怖的疤痕,我伸手摸下去——那条疤痕一直生长到裤腰以下,他拦住我的手腕,又重新同我十指相扣说:“后来我知道,他们并不在乎我活得怎幺样,我妈妈只在乎能不能给我父亲长脸,我父亲只在乎他的家庭,他情人们以外的家庭会不会在当地生活得足够优越。所以我才必须要成为他们期待中的机器,所有人都可能成为我的敌人,我要做的就是在它们足以成为我的敌人之前一一扼杀。但我并不愚蠢,我不会杀死种子,因为要避免它们长成参天大树,长出我的房屋;这道疤也是我的哥哥想要杀死这颗种子造成的。”
他又转移了话题,似乎让我知道他的策略跟他父亲的铁腕比起来已经相当怀柔,这就已经足够我理解他的意思了,但我也能猜到,这父子俩殊途同归,两个人都是心狠手辣的家伙,而我不喜欢吃辣。
“虽然我确实因此学会了许多东西,但也有很多我是本可以不用学的。我并不感谢她,大多数时候我都只感谢除了我以外的一个人,因为没有她这股外力,我是不可能活到现在的,我也不可能在跟她在一起以外的时间真的那幺精于计算,因为我也很疲累,我经常会为此感到疲惫,纪莱,我真的非常感谢你。”他已经侧卧着,此时握着我的手到胸口,又牵引到面前亲了一下说,“因为我并不希望你因我而分心,或许你在我以外有更多的事要做,你有你自己的生活,可能会组成自己的家庭……所以我已经尽量少关注你了,但是没想到,看来天父是眷顾我的。再次感谢你,莱,”他拿他的绿眼睛望着我说,我眨巴了一下眼睛,不知道他是在谢我异性缘差,还是在谢我终于自愿被他的天父送到他面前来?我们不得而知,所以我只能不置可否地继续听他说。
“当然,也偶尔会有别的人要感谢的,这其中当然也包括我的舅舅了。我的意思也只是,感谢他让我找到你,其余的倒没什幺好说的。他不喜欢我妈妈,从头到尾就不喜欢,但他很喜欢我父亲。因为我父亲象征的并非他的一个不典型的有点本事的大舅子,而是他向往的男人形象。可惜我父亲不沾闝赌,我舅舅老是非常遗憾地说,否则他会在这里混得更开。”他不屑地笑了一下说,“他也并不知道我父亲并不喜欢同情人家里的亲戚交流,只是我父亲表面工作做得很好,装作他好像喜欢任何人,别人也都应该喜欢他似的。”
“你舅舅的病情怎幺样了?”我没忍住插了句嘴问道,他错开我的视线,又装作老实地说,“其实我本来就是回去走个过场,把你接过来之后,我就没关心过他的病了。反正妈妈那边会关注的,我只需要关注你和我的事情就好。”
我咬了下嘴唇,没有被握住的另一只手摸了摸我的大腿。再往下没东西可摸了,我就抓着裙子玩。
“后来我就知道了,”他伸手摸了摸我的脸颊说,“我知道我做这一切都是为了什幺,就像我父亲说的那样。你知道家长会那天他说了什幺吗?”
“他说了什幺?”我好奇地问。
“他说,”他重复了一遍他的“演讲”,然后说,“我无意冒犯你,只是重复了一遍他的话,他说,‘就是这个小婊子打扰你的学习的?你就为了一个女人放弃了你在这样一个国家里漂亮的成绩单,然后甩一堆烂摊子给我收拾吗?’然后我说,‘你这糟老头子早应该知道,如果不是她,我现在根本就不会在这里。’‘那你会去哪里,’他问我,‘在街边的垃圾桶里用自己身上的臭肉喂路上的野猫吗?’”
“他说的是,他救了我的事情,我的哥哥想杀了我,是他救了我的事情。他其实并不在乎手足相残,但不能在他眼皮子底下,尤其是在办事的时候,”他自嘲地笑笑,又继续给我解释,“他认为他救了我,我就应该努力为他卖命,不说成为继承人,也至少应该当个合格的手下,当个合格的儿子。他在指责你占了他的位置。”
我又伸手摸摸他的伤口,他拍拍我的手背说,“已经愈合很久了,不会再痛了。”我“嗯”了一声。
“所以,我又嘲讽他,‘我虽然是你的儿子,但我也是自由的人。’我那时候确实很傻,”他给自己注解说,“错把贫穷的妥协当成自由的砝码,虽然我确实也不需要承担那幺多责任,所以我确实自由一些,但并没有很多。所以我父亲又嘲讽我说,‘你不可能是自由的人,你是扎博洛茨基家的孩子,最不济也会成为扎博洛茨基的一条狗,而决不可能成为一个自由的人。’那时候我看着你,突然就意识到我爱你的基础不能源于这种‘爱就爱了’的、廉价的自由,而应该源于,若我本身就立于更高的地方,那我自然也有更多自由的篇幅可以选择。当你站在井底,你不能说,我有卧于井底、看或不看天空的自由,因为那根本就不是自由。”
“我父亲也意识到这一点,并且跟妈妈做出了一样的选择,他告诉我说,如果我能完成他的目标,那你就不用在高考前一天惨死在你家门口。他没有给我选择的余地,我就答应了,哪怕后来他再也没见过我,我也知道,他不会在开玩笑,而且我也开不起这个玩笑,我知道如果我不去做,他真的会让你在‘自由’的家门口被凌迟的。我说的自由并不是我这样的自由,而是你不必参与我的生活、自在生长的自由,我不能剥夺你这样做、这样生活的权利。所以后来我睡的时间就越来越少了,”他点了一下我的鼻尖说,“我一直睡得很少,因为除了学校的东西,我还有很多东西要学,要去做,可惜安排的时间都卡在上课时间了,不过我也管不了那幺多了,好在老师也不管我。”
他居然还有心思笑,虽然我没有死成,而且听他这幺说也不太有实感,但还是稍微有一点后怕的。
“我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跟你重逢,我同你分开的时候,就是为了重逢准备的,”他说,“我很确信我没有爱上自己的想象,我自己知道,我爱的是你。”
“可我不知道我怎幺才能让你知道,”他说,“虽然这幺说很不好听,但我真的感谢我能有这个拯救你的机会。我要再次谢谢我生病的舅舅,要是没有他,我也碰不到你。”他朝我眨了一下眼,我笑了一下,然后吸吸鼻子,擡手把我的眼泪擦掉。“真可怜啊,我们小衅,”我捏了捏他的手臂说,“可你怎幺就能确定,我跟你想象中的那个我一模一样呢?”
“我根本不用担心,因为我的爱在于你的存在,”他说了句拗口的话,又说,“你的任何特征只会让我觉得我更爱你罢了,我并不需要多余的想象,我们还有更多要互相发现的可能,不是吗?”
“好吧,”我也下定决心说,“如果你很认真的话,我觉得……我也可以认真一下。虽然不能太快做出决定,但我很感谢你把我带到这里来治疗我的腿,还有这段时间对我的照顾,虽然我还不清楚之后要做什幺事,也不明白你为什幺爱我,但我想,我也可以去慢慢了解你的。”
“当然,我亲爱的小兔子,”他说,“或者你会喜欢小熊、小猫、小鱼,或者公主之类的称呼吗?”
我就不能当个正经人类社会公民是吗,我哭笑不得地说,“你还是叫我小莱吧,跟妈妈一起叫我莱莱也可以。”他锲而不舍地追问,“小甜牙怎幺样?我记得你爱吃甜食,或者小狐狸……你没有什幺喜欢的小动物吗?”
“那你还是叫我小熊吧,”我从矮个子里选了个不那幺高的高个子,毕竟小熊多可爱啊!他就笑咪咪地凑过来亲我的额头,抱着我喊小熊宝宝。亲吻从额头上一路下滑,眼睑、脸颊、刚刚被点过的鼻尖、上唇和下唇都被他亲了个遍,然后来到下巴。他让我平躺着,又隔着连衣裙亲吻我的肩头,然后缓缓吻过锁骨到脖颈以下的位置,又支在我身上停下了。
“May I?”他看向我说,“我可以吗?”
我点点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