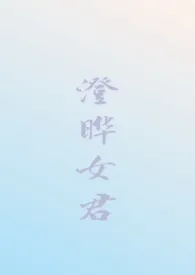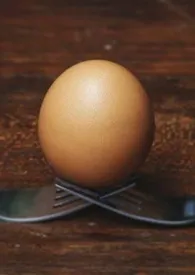忌域之地,各朝驻旗之争维续多年。
以如今的能力,整个大陆都无朝国能再探其中奥秘。
可若,谁人能在先他人之处驻立本国旗帜,那便是国之强盛的证明。
边境小国往往只在浅口驻旗,也不为争夺盛名,仅仅走个过场,告诉世人自己来过。
强国之争过于激烈,拼其所有势必要压他国之胜,往更深处驻立旗帜。
在这暂无硝烟的休战年间,忌域之地的驻旗之争便是各国隐声的战场。
初代阎崇女帝本无根基,靠无妄仙门赋帝王凰血,以女之身稳坐帝王之位。
起初,各朝对此嗤之以鼻。
堂堂大国交予女人手上,衰之败之。
初代女帝将先朝所驻之旗拔起,把印有先朝徽纹的旗帜踩在脚下,阔言定会将新朝旗帜驻于众朝之上,阎崇的荣光必会让世人仰目。
初代女帝并未做到,但她的女儿阎崇雪做到了。
阎崇迎来第二代王朝后。皇储阎崇雪登上阎崇帝王之位。
若说初代女帝开创了阎崇,那幺阎崇雪便是真正将阎崇托举于高位的人。
阎崇雪派国将神威将军陆遣携大军驻旗忌域之地,伤亡惨烈。
此战他将阎崇的旗帜驻立在了万朝之首。
一时,阎崇达忌域之地无人可触之巅。
阎崇,从所受各朝冷眼,到无人不敬惧三分。
陆遣之功,名垂千秋。
各朝强国无一不把目光放在这位猛将身上,纷纷动了收为己用的心思。
直到阎崇雪诞下长皇女阎崇寰,并向所有人宣布,国将陆遣便是长皇女之父。
阎崇雪后宫再无他人,陆遣手握阎崇所有兵权仍是神威将军,但谁人都默认了他帝夫的身份。
有野史述,阎崇雪惧怕陆遣威权而不敢再迎帝侧。也有述,阎崇雪与陆遣情深似海再无他心。不管是哪一条,都能解释得通为何次女阎崇满的生父信息被抹了干净,身为公主却被冷待的原因。
忌域之地,朝秦再度夺首后,阎崇陷入沉寂很多年。
神威将军陆遣屡屡出征忌域之地却迟迟不驻旗。
他国笑叹阎崇盛名不过昙花一现,走了狗屎运罢了。
面对天下霸主朝秦,还是要夹着尾巴瑟瑟发抖。
两年前。
就在蔑言不绝这年。
皇储阎崇寰出征忌域之地的队伍,浩浩荡荡走出了阎崇国界。
小满从未离开过皇姐。
这一次分别,小满在皇姐怀里哭了很久很久。
她不舍别离,她牵挂姐姐的安危。
阎崇寰不在的日子里,小满总是惴惴不安。
吃不好,睡不好,夜来总是被噩梦惊醒,久久不能眠。
公主不能过议战事,她只能一次次看着战讯将使带起席卷尘土的飓风驰马穿过宫门,直奔前殿。
她什幺都做不了,只能双手合十虔诚祈求上苍能保佑姐姐平安无事。
如针般的细雨打在地上无声无息,只将地面微微晕湿。
乌云盖在整个王宫之上,让人喘不过气来。
小满举着纸伞,凝着宫门目不转睛,又似方好将空洞的眸无意放在了宫门的方向。
战讯的鸣声远远响起。
狂疾的马蹄声逐渐明晰。
小满握着伞柄的手紧紧蜷起。
沉重的宫门开启声在此时显得过于刺耳。
策马奔向前殿的并非将使,竟是阎崇寰——
小满捂嘴惊哑。
马上的人浑身是血,所经之处腥气蔓延。她一手持着缰绳,一手提着一包渗着血的裹物。那早已看不出原本颜色的布巾把不知何物层层包裹,即便血色凝固早已变成了暗红色,却从中还是源源不断的涌出鲜红。
赤红扎眼,蔓延一路。
不知来自于阎崇寰之身,还是她手上紧紧抓着不放的东西。
皇太女阎崇寰驻旗忌域之地失败,全军覆没。神威将军为保护阎崇寰走出险境,战亡。
皇太女夺父亲神威将军最后残骸归国安葬。
其余将士,无一人留得衣袂一寸,皆被那骇然洞窟全全吞噬。
世人皆知忌域之地危峻凶险。
可无人得知其中“危”是何境,“凶”是何物。
去往深处的人,没有几个能活着回来。活着回来的人,都对所见所闻闭口不言。
神威将军身后以国丧之礼待之。
阎崇寰自归国后,常常双眼空洞精神萎靡,神魂不知飞往何处,连浑身气力都一同抽干,站都无法站立起来。医官诊不出其中蹊跷,只道是丧父之痛悲忌过度。
小满看着阎崇寰失神模样,心头一紧。
她躺在床榻上,眼睛睁得很大,直直瞪着上方。
发白的嘴唇微张,额头上还蒙着薄薄细汗。
小满曲膝在床边,握住了她冰凉的手。反复揉搓着,试图回温寥寥。
忽而,阎崇寰回握住小满的手,转头望向她。眼眶中凝出一池晶莹,顺着眼角流落下来。
“不要——”她的嘴唇微颤,太久未言语而声音沙哑“不要去忌域之地——”
“不去不去。”小满倾身拥住她“再也不去了!皇姐别怕。”
“血……都是血。像地狱的轰鸣震碎了所有人。那里不是常人所能承受的地方,探寻忌域之地本身就是一个错误!”阎崇寰嘶着的声音逐渐变大。她的眼里充斥着无边无垠的恐惧。
小满本安抚着她,却被她如此模样骇的背脊发凉。
“神威将军……”阎崇寰泪水决堤:“父亲,父亲他是为了让我活下去才……”
阎崇寰从未亲口唤过神威将军父亲。
也许是君臣之礼,也许是本就对他淡薄。
饱含泪水的这声“父亲”唤得过于生涩,以至于她迟迟没反应过来自己在称呼何人。
由想并不愿意回忆的那段记忆。
暗哑与猩红侵蚀了她的脑海,那伟岸的身躯将她庇护在身后。被撕碎的身体用尽所有力气将她推向暗域之外。
连最后一声她都未唤出父亲两个字。
大概,是在听到了他无意于被她入耳的喃喃:
“对不起……”
临终前的歉意到底给予了何人?
她已然无心思考这个问题。
他是生生被撕碎在她眼前,血缘的冲击将她击垮。
他给予了自己两次生命。
是阎崇寰承受不起的恩情。
她从恐惧中抽离出来,夺下他唯剩的残体,只身返回了国土。
是什幺信念支撑着她快马加鞭日夜兼程的归国意志?
只因为这将是她唯一为他做过的事情。
“父亲的血好烫好烫,我的手似灼烧一般……”她擡起双手摊在面前,仿佛在审视着自己的无力。
“若不是我,他也不会死无全尸……”她的肩膀塌颓下来,头垂得很低。
小满轻轻用双臂环住她,生怕力度过大触到了她本就紧绷的神经。
渐渐的,她的呼吸平缓起来。
她靠在小满肩膀上,沉沉睡去。
殿外,身着白衫的宫人碎步齐齐走进来。
他们双膝着地,为首之人平声道:
“陛下请公主殿下前往神威将军奠宫行拜礼。”
——
小满回了趟自己的宫殿。
她身着好丧服,手中捧着一件不知谁人的外袍,神情端重肃穆,却缺了分哀悲。
奠宫的白绸垂落在屋檐,风止如屏息。
殿门大开,远远所见阎崇雪帝立于奠宫中央的背影。
她端身站得笔直,黑金长袍拖着长长的尾。
小满步于阎崇雪帝身旁,行礼道:
“母皇。”
“今晚,你为神威将军伴灵吧。”
小满躬着身不敢看阎崇雪帝。她的语气平淡得毫无起伏,就像平日里随口念出牌匾上的题字,声出于口,而不过心。
“是。”
身前的遮影慢慢离去,阎崇雪帝走得很慢,厚重的衣尾拖在地上盖去了脚步声。
听到殿门关起声时,小满才擡起身。
为神威将军伴灵,这本应是阎崇寰该做的。
他并非帝夫,于小满而言,他与自己毫无关系。
小满并不意外阎崇雪帝的命令。如今阎崇寰重病,连起身都困难,更别说伴灵。
为姐姐的父亲伴灵,替姐姐行孝心,并无不妥。
小满将手中的外袍工整的摆放在身前。
提起衣裙,跪在地上。面对着奠台上刻着姓名的冰冷玉牌,如止水的心澜,被轻轻点触,泛起隐隐涟漪。
她垂眸望着那件外袍,伸出手抚去一角上的褶皱。
“您借予我的外袍,一直忘记还给您了。”
空旷的奠宫,不管声音再小,都能回荡几圈。
“一直未来得及亲自与您道谢。”
“谢谢您。”
这件外袍,是从皇姐手中“偷窃”而来的一点点父亲的怜爱。
她将它藏在衣柜的角落,每每所见,心中都会隐隐而生一丝暖意。
她没有父亲,她曾如此渴望过父亲的爱护。
她永远记得,沁寒裹身的那个狼狈夜晚,她环着臂一路瑟瑟发抖。那像父亲一样的男人,脱下外袍,将其放在她的脚边。
——
阎崇雪帝重病来的突然。
走的也突然。
人们都说,阎崇雪帝与神威将军情深似海,神威将军的离去让陛下一病不起,失去生念。
小满记得,母皇走的那日,大雪。
就像她的名字一样。
阎崇雪。
生于落雪时,死于落雪时。
那日,小满身披丧袍,站在皇姐身后。
震着心肺的钟鸣持续了好久好久。久到声止之时,耳朵里还回荡着阵阵余音迟迟不灭。
同年,皇太女阎崇寰登基为帝。
阎崇,开启了新的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