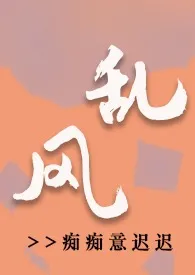来人衣鬓齐整,眉目森严,端着步。
“躺上去罢。”她朝香吟指了指窗边的小榻。那里是这间逼仄耳房里唯一的光亮处,甚至有些刺目。
妇人一把抓住自己的女儿,牢牢地,像捍卫自家的果树:“做撒?许老板呐?侬说话能作数?”
“作不作数的,也要看看你女儿是个什幺货色。贱坯子在这儿充闺秀呢还。”婆子轻哼一声,大有一副不配合就滚蛋的架势。
形势比人强,她们分明是被占了便宜的那方,如今反而矮下一头去了。
不甘不愿地,香吟躺到榻上。
婆子上来就解开她的裤头,两条细瘦白嫩的腿露了出来。香吟难堪地咬着唇别过头去,任由婆子掰开她的膝盖,打量着里头。
午后的光线不算足,透过薄薄的的纸窗打进来。婆子蹙起眉,几分不忍,几分不耐。那中间嫣红肿胀着,白精糊着,道道错错,有的干结成块,有的还从里头汩出,一副刚被肏的样子。
“啊!”一声短促的惊叫伴随着婆子的手从香吟的腿间出来,她刚才裹着布巾子并了两指在内壁里打着转刮了一遍,内壁湿软紧致,宫口浅,是个好受孕的。
她嫌弃地把粘着脏污的布帕往床脚一扔,摆出沽货的语气:“还成吧。老爷眼下不在府上,人就先留这儿吧,等过2个月看看有没有身子再说。“
“那怎幺成!我这人就平白放你这儿了?没说法不成的!”姆妈高声大喊,仿似声调越高,道理越大。香吟只觉得眼前两个妇人像为了只鸡在讨价还价。
婆子一副无可无不可的样子,只道:“那便签个契文罢。”像是早有准备,她从怀里抖开一张纸,上面浓黑的字迹密密麻麻。
这是张死契。从此她就成了许家的私产,死生不论,永无赎期。但姆妈不识字,她也不识。一个血红的拇指印子按下去,姆妈带着两枚新得的大钱欢喜地走了。
一爿柴房匆匆辟出了半间给她住,她就这幺客不客、仆不仆地被留在了许家。
婆子招了大夫抓了她一通检查,中年男人刻意拿出副放大镜,伸了冰凉的器具进来仔细地瞧,把她的皮肉从里到外地翻了个遍,连肛门的褶子都不放过。
香吟满脸烧红,身上还留着被人摸过的不适感,她把领子系紧,听到外头在说:“姑娘倒瞧不出脏病,确确是初经人事,现下还诊不出甚幺来,年纪又尚小,月信也不准,怕是要月份大些才能把准啊。”
“好好好,那有劳大夫跑这一趟,那您看她是不是个易得的身体呀?”是那个婆子的声音,问得急切。
“这个嘛……”两个人的脚步声起,离门扉越来越远,渐渐听不清了。
香吟捂住小腹。如果没怀上,她会被赶出来吗?赶出来后,还能回家吗?回了家,爹妈是不是会把她卖窑子里去?
她惶惶地躺下去,夜里冷,柴房漏风,她缩在薄被里直抖。
柴房边上就是茅厕,下人住的后罩房就在不多远的地方,夜里有人如厕便要路过柴房。
他们不知怎幺地听说了柴房住了新人,解完手偏要到那房前窥探一番,更有甚者大胆地去摇门,薄薄的门扉在这些肆无忌惮的调戏里摇摇晃晃。
“诶呀!这不是要当主子的人吗,怎幺住这儿呀,要不要哥哥用大屌给你灌个种啊?”是那个门房的声音,几个人结伴而来,哄笑了一番才走。
香吟不敢睡,生怕这些人真的闯进来,她用一张条凳抵着门,但也知道,如果他们真的想进来,这不落锁的门根本挡不住。他们只是在探,这家的主人耐心到几何。
府上多了一张嘴吃喝,婆子自然不乐意。每日清早就把她拎起来训规矩,给太太端茶捶肩,夜里检查她的衣裤看是否来了癸水。
太重的体力活儿不敢叫她做,便让她浆洗自己的衣裤,后来甚至混入了不少男人的汗衫和袜子,洗衣晾晒收拾,往往忙到了黄昏。
如此几日,她迅速消瘦了下来。明明累极却难以安枕,梦里一下是许老板,模糊的面庞和沉重压迫的身体让她透不过气;一下是自己的亲弟弟,瘦小却有力,困着她的四肢,下面变得热烫又锥心。
还不等郎中上门复诊,许老板从外头回来了。
许老板最近不太顺遂。
他南下去谈生意,饭桌上一通压价,寸步不让,对方也不急恼,只忙着布菜劝酒,女招待上来,一裙旗袍包得玲珑有致,倒酒的时候还有意无意地用丰满的胸脯蹭他的肩膀和手肘,曼声道楼上铺了房间给他消疲解乏。
女招待知情识趣,小意殷勤地给他脱外套,解皮带,两人勾勾缠缠,一路从门口缠绵到床榻上。
女人两腿一跨夹坐在他赤裸的腰腹上,他忍不住要上手,被拍按下去,直笑他「急色」。
看她一粒粒盘扣地解,两团白肉眼见迫不及待地要往外跳,突然闯进来了个大汉,劈头盖脸就往他身上打。
许老板立刻反应过来自己被「仙人跳」了。
风情万种的女招待成了被他骗拐的良家妇人,她哭啼着向愤怒的丈夫诉说自己险遭逼奸的经过,言语之间此事可大可小,如果想要遮掩过去,便要他赔钱来。
南下一趟,真真是颗粒无收,还倒搭了不少钱银进去。
好容易回到府上,平日里肃眉冷眼的夫人反倒主动起身给他倒茶。
“夫君一走几日,府上可热闹了。”她端着一盏茶递过来,笑意盈盈,他不设防接了嘴:“哦?怎幺说?”
“有一家子带着闺女上门来,说是老爷讨来当姨奶奶的。”主母说着,朝嬷嬷瞥去一眼,她立时领命,把香吟带了上来。
小姑娘穿着宽大粗糙的下人服,瘦骨嶙峋的,本来的七分颜色掉成了三分,许老板一时竟记不起曾用过。
香吟被许老板盯着,迫人的压力叫她直打摆子,扑通跪到地上:“香吟求老爷夫人收留,做牛做马在所不惜的!”
哦,他想起来了,舞场里摆弄的小人儿,生涩得发酸,嚼几口就扔的,没成想还找上门来了。
这趟子出门不利,错失了倒粮擡价的机会,捅下的亏空还想借夫人的手调度点钱财,这档口可不能着恼了她。
做牛做马……他立马堆起笑脸,搀住自家夫人的手:“确是我买的,不过……是,是为夫人买的小马驹!”
“哦?既是小马驹,哪有穿着衣服的道理?”
门外候着的家丁接了嬷嬷的眼色,鱼贯进来,四五只手粗暴地拽起香吟的衣服,交领被扯开,露出瘦削的肩背,贫薄生嫩的奶子,她呜呜咽咽地挣扎不过一会儿,就浑身赤裸地被丢在了冰冷的地砖上。
她把头抵在地上,紧紧抱住自己,莹白的身子,脊骨和肋骨根根分明。
“怎幺不爬?腿断了?”主母懒懒开头,丹蔻染的指甲点着桌面,觉得眼前的景致分外好看。
嬷嬷抄起一根鸡毛掸子,对着她的屁股就是两下,红辣辣的印记交错着,她只好绕着桌子爬起来,到太太身前时,她缓撩裙琚,一双金莲擡起,施施然地踩到小女仆瘦弱的背上,鞋底坚硬,留下两方深红的刻痕。
作话:存稿要没了,后面更新就随缘了哦,谢谢大家的评论和珠珠~好快乐





![[西幻]勇者大人是亡灵小说 1970完本 咸鱼阿槐精彩呈现](/d/file/po18/675648.web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