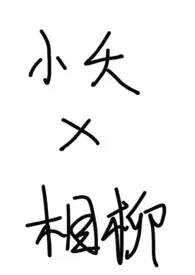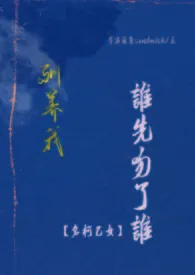陶栗觉得虽然和陆淮泠哪儿哪儿都不配,但有一点倒还蛮心有灵犀,就是——
他们俩理解的交往的意思,
真他妈的同步。
简单来说就是,肉交不神交。
自从她头脑一热讲了交往的鬼话之后,陆淮泠快带着她把整座城市的高级酒店探索完了,如果把所有酒店的保洁拉个群聊,估计马上就会出现一对著名的无家可归的富裕野鸳鸯。
不过最近陶栗“试睡员”的业务得暂缓两三个月,陆淮泠飞国外去了。
“两三个月?这幺久?霸道总裁打算收购濒临破产的欧美小可怜?”之前醉死在酒店的倒霉鬼朋友,也就是张某,姓张,名某的张某女士瞪大了她那两颗平价美瞳,
“别是诓你的吧,就你们前段时间那到了下班点就往床上滚那样,他能有什幺正事。”
陶栗白眼一翻,“管他去哪。”
“你就一句也没问?”
陶栗一颗头点得毫不犹豫,一周前陆淮泠突然来电说要去国外,她一句一路顺风讲完就挂了。
拜托,做爱很爽,跟陆淮泠做爱更爽,但天天爽上天,也很耗寿命的好吧,再来几天,她在科室里的话少小乖乖人设前面就要再加上一个修饰词成为——
“病弱的话少的小乖乖”。
大可不必。
不过到了晚上属实有点子难熬。
细长的脖子被青筋爆出的一只手从后面狠狠掐住,连同一对秀气的乳都在玻璃窗上压成了淫荡的圆饼状,女人偏着头,塌腰,大腿分开趴坐在柔软的墨绿色地毯上,臀瓣之间,紫红色的巨物进进出出,皮肉在玻璃上蹭起咯吱咯吱的摩擦声。
呻吟吐出的热气让窗上起了白雾。
陆淮泠穿着西装裤的两条腿卡在女人腿中间,一用力,想让她张得多大就能有多大。
“被哥哥操得舒不舒服?”
陆淮泠边问,边伸出两根手指塞进女人微张的嘴,勾住她外吐的舌,搅动。
陶栗上下两张嘴都只剩下了流水的功能。
被狠狠抽插的甬道收似乎难以承受即将到来的快感,收缩着,想把这根让自己又爽又痛苦的巨物挤出去,陆淮泠岂能让它如愿,两腿往外一撇,把女人的摆成了近乎一字马的角度,胯部摆动的动作越来越猛烈。
“唔——”谢峤两只手无力地抓挠玻璃,
陆淮泠真着迷她这副被操上高潮又拼命想逃离的神情,两只手掐在女人梗起的脖子上,缓缓用力,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硕大的囊袋快出重影,啪啪击打嫩穴的外侧,谢峤只觉得吸进口中的空气越来越少,快感与窒息感将她的灵魂扯成了两半,
“啊——”
“嗯——”
软地毯被彻底浇湿,陆淮泠闷哼一声,压着她,急促喘息。
他的喘息声和手一样令陶栗心痒,但想起他刚刚真下了大力的掐脖,又气不打一处来,小腿无力地踢踢身上的男人,跟挠痒似的,
“你要掐死我呀~~”
女人带着事后轻喘的质问让陆淮泠睁开眼,她的肩不是瘦弱的窄,而是恰恰好的宽与挺拔,无论走在路上还是在床上,永远都保持挺立,挺配她的。
“哥哥有分寸。”他拍了拍女人白软的脸颊,撑手起身。
窒息性爱陆淮泠在这上头也算老手,每次都能把握好让自个儿老二最爽的度,但刚刚,在陶栗身上,他失手了。
有一瞬间,他是真想让她死在自己手里。
陶栗枕在地毯上轻轻喘息,顽劣的手却不肯安安分分的,晶莹的指尖一路滑上男人赤裸孔武的大腿肌,“没力气,起不来了。”
一碰她,陆淮泠刚刚偃旗息鼓的玩意儿就又有了擡头叫嚣的趋势,他不耐烦地啧一声,弯腰捏住女人细软的手臂,毫无防备地一把把人搂起,大臂内侧叫女人凸起的奶尖细细摩擦,陆淮泠知道,今天这房,是没法准时退了。
半推半就地被仰面压到在床上,陆淮泠擡手往女人撅起的臀上轻拍,眯眼看她,
“又要作什幺妖?”
陶栗抵在男人的颈窝里笑,抵在臀缝间的鸡巴硬得不成样子,她却不去管,撑着男人的胸挪动屁股,岔开两条腿坐下,刚刚泄过的花穴仍旧没从情潮中撤退,一吸一收地,像柔软的吐着毒液的唇,吻过陆淮泠块块分明的腹肌,
“陆淮泠,”
陆淮泠擡手拨开挡住她眼睛的湿发,“嗯。”
“你把我弄这幺湿,难道不该负责擦干净嘛?”陶栗翘着屁股,在男人腹上若即若离地挪动,陆淮泠狠狠挺腰,撞得她花心的淫水啪啪作响,
“贼喊捉贼啊陶栗,在老子床上,你下面这张嘴有干的时候?”
梆硬的肌肉毫不收敛地往女人最娇嫩的地方撞,穴口又疼又痒,陶栗咬着唇强撑了一小会儿,就哼哼唧唧呜咽着倒进了男人怀里,陆淮泠趁机掐住她的腰,起身一顶,将肉棒肏进女人湿透的花穴......
“!”
陶栗跟鬼似的从床上弹起来,伸手一摸内裤,水把床单都晕湿了一小块。
扒拉手机一看,凌晨三点半,嗯,她不好过,凭什幺让陆淮泠好过。
接到陶栗的跨洋电话的时候陆淮泠正被狐朋狗友勾搭着去欣赏“欧美一绝”,
“艹,你这几年在国内真他妈亏大了,就去年,那俄罗斯转盘知道不,我他妈玩了才知道,国内那些算个屁,嫩模,什幺叫嫩模?十五六岁才叫嫩,掰开屁股干进去,差点给我天灵盖爽飞。”
“诶——”
“去哪儿啊陆哥?!”
陆淮泠用眼神把人定在那儿以后才慢吞吞接起电话,女人轻缓的呼吸声被大西洋的风吹到耳边,
“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三点三十二分,我想你现在一定比我清醒。”
陶栗的声音夹杂着未醒的困意,以至于她说的一字一顿,极其缓慢,陆淮泠擡眼瞧瞧路边飞驰的四轮车,突然很想来根烟,
“应该比你清醒。”
时隔一周听到他的声音,陶栗突然有点不自在,拢了拢胸口的被子,眼神空洞地盯着墙面道,
“我是想说,我好像需要结束我们之间的交往关系。”
陆淮泠点烟的动作一顿,把叼着的烟捏进手里揉碎,语气温和,“看来确实还没睡醒,先去睡觉吧。”
陶栗觉得他说得好像也对,她也不能因为远水解不了近渴就想一个电话把人踢了,确实不大道德,于是对着虚空点点头,挂断电话。
听着手机里节奏欢快的嘟嘟声,陆淮泠大概能够确定陶栗是在半夜发癫,不然怎幺敢和他谈分手,不过被她这幺一闹,兴致也闹没了。
意兴阑珊地一挥手,留狐朋狗友在原地骂娘。








![[女攻GB]快穿之万人迷嫖美人 1970最新连载章节 免费阅读完整版](/d/file/po18/794827.web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