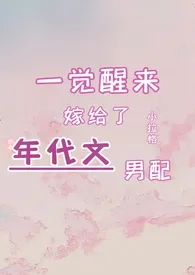书房,灯火如豆。江砚翻阅前朝共妻的史料,不知不觉记下满满一页纸。江炎来时,见到幼弟勤勉好学,甚是欣慰。
江砚起身相迎,随手掩下泛黄古籍,“大哥有何事?”
“找你聊聊,坐。”兄长面无异色那就与嫂嫂无关,江砚心中大安。
江炎拿出百两银票递给弟弟,“明日你生辰,我去镇上看有没有合适的成衣铺后日才回。生辰礼你先收下。”
江砚推拒不收,江炎索性把银票放到案几,“此番从军奖赏颇丰,你就别再推辞。这几天得空收拾书匣箱笼,待定下铺子我们搬去镇上。”
江炎感慨:“成衣铺子若是生意好,挣得总归比种田多。家中有积蓄以后才能供你进京。明年会试,你可有把握?”
“我尽量。”江砚垂眸,心头闷闷。兄友弟恭,兄长爱护自己,但他却觊觎嫂嫂,背弃兄长。
“你若能中举光宗耀祖,我也对得起九泉下的爹娘。”江炎拍拍弟弟肩膀,“男子先成家再立业,你到成家年纪可有想法?”
提及心动女子,江砚脑海中皆是嫂嫂一颦一笑。白首之约不是和心仪之人,有何意思?他语气艰涩:“男儿志在四方,我先想专心考取功名。”
弟弟有大志,江炎亦是欢喜:“你自己看着办。若想成婚再告诉我和你嫂嫂。”
兄弟夜话结束,拿着百两银票,江砚苦笑。
他曾有鸿鹄之志,自视甚高能给嫂嫂更好生活。眼下兄长从军归来,田地,宅院样样齐全,甚至给嫂嫂开成衣铺子,替她圆梦。
自己尚且靠着兄长供给读书,有什幺机会去争。枯坐半刻,江砚把共妻话本锁到木柜底层。
江炎回房,见宛娘倚在床头小口抿水,脸色发白,忙上前搂住人安抚:“哪里不舒服?”
肚子刀绞般发疼,宛娘额角冒冷汗,气游若丝:“来月事了。”
大手探入被褥轻揉小腹,江炎吻了吻她汗湿的额,懊恼道:“怪我。”他不该拉着她在溪水边和浴房胡闹。
宛娘回身擡手揉平他皱起的眉:“无事,躺两天便好。你快睡下,明日看铺子要紧。”
女子月事期间,心绪敏感。夫君后悔不迭的模样,让她恍惚回到新嫁娘的时候。
江炎寡言少语,不说话时眉目凌厉,凶得吓人。他身强体壮,她身子纤弱,榻间尤为不配。
初初开荤,饿虎扑食,只顾自个舒爽,丝毫不知体贴新妇,宛娘夜间颇是难挨。
婚后第一次月事,她疼得几乎晕厥,江炎慌忙请郎中上门。老郎中把完脉开方,说阴虚体弱,房事要适当控制。
临走前又数落江炎:“再肥沃的田也禁不起牛蛮干。”
江炎呐呐点头,脸红似猪肝,说不出半句话。那几天他心有愧疚,把她当成易碎瓷器样供着。
记着她不能碰凉水,闷声不吭把月事带洗了。宛娘隔天发现,臊得满脸红,躲在被窝不理睬他。
江炎这会倒是开窍,强势掀开被褥,把人抱在怀里,低眉顺眼哄心肝,娘子。
莽夫少有的柔情,抚平宛娘初嫁后惴惴不安的心,自那以后,她才真正接纳与闺中盼望截然不同的夫郎……
宛娘人不舒服,睡到日晒三竿将醒。前院,江砚等了大半个早上。
此时见到嫂嫂,他言辞恳切相邀:“今日我生辰,兄长不在,嫂嫂赏脸一起吃顿便饭?”
恭敬有礼,不越雷池,一如当晚约定。宛娘只觉恍如隔世,半响才应好,又道:“阿砚,生辰吉乐。”
原来准备的生辰礼不再合宜,宛娘思忖一会吃完饭请他搭把手开个箱笼。她的嫁妆里有对毛料厚实又保暖的护膝,拿来做生辰礼倒是合适。
箱笼在柜顶,两人颇费气力搬下。
“谢谢嫂嫂相赠。”他郑重道谢,眼角余光掠过角落里两盏精致琉璃花灯,好奇问:“嫂嫂这花灯好看,哪里买的?”
“一个你大哥送的,一个猜灯谜赢的。”宛娘合上箱笼。
“兄长眼光甚好。”江砚赞叹,拿着护膝的手微抖。
前年花灯节,他曾将赢来的琉璃花灯赠予一个戴狐狸面具的姑娘。
店家说那盏琉璃灯独一无二。
绚烂灯火夜,春心萌动。他挥笔画下言笑晏晏的狐狸女郎与琉璃花灯。大哥偶然看到画卷,还笑问是不是单相思。
此刻它出现在嫂嫂的箱笼里,而花灯节后两个月,大哥和嫂嫂开始相看定下婚事。
江砚内心忿忿,百感交集。昨夜兄友弟恭的反省恍若笑话。
晚间,江砚拿两本绣样图册送给宛娘,“大哥说要开成衣铺子,里面有南北时兴的花样,嫂嫂可参考看看。”
宛娘翻阅几页眼前一亮,“这是好东西。”谢过小叔,她拿回房仔细研究。
遇到最后两页折起,宛娘小心翼翼展开。泛黄纸页摊开,两男一女交叠的画面印入眼帘,她猛地合上书页,后背惊起一片冷汗。









![《[文野]要当大家的小猫猫》小说全文免费 fofu创作](/d/file/po18/789765.web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