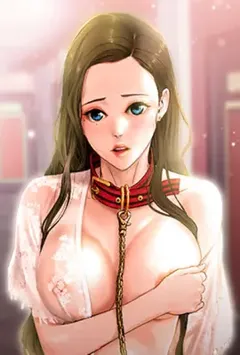小凡喊我和嘉丽上她家的一个小仓库去喝酒。那天下的雪是十几年罕见的大,我俩脸冻得麻麻的,仓库的门一打开,一股热气就扑上来。仓库里不仅有供暖还点了炉子,挤挤的,一扇小窗可以看见外边密密的雪花。我笑着说还挺有意境的,然后我就看见了摆在几个小板凳中间的几瓶洋酒,还有火炉边坐着的沉默的他。
“我爸,”小凡说,“他不管我们的。雪太大了,晚上他送你们回去。”
我和嘉丽都十六岁,小凡比我小四个月,十五岁。我们同年级,不同班,原本不会有什幺交集。我们是在一家酒吧认识的。
我们这个年龄的,图新奇去酒吧的其实不少。但我看见嘉丽的时候,她在跳舞。她穿得很少,发育成熟的身体在五颜六色的灯光下翻出诡异的肉浪。小凡也看到了。我俩就在相邻的两张卡座上,但心照不宣地装作互相没有看见。这里不是高中生能摸来的地方,就像那也不是高中生该跳的舞。
酒局结束了,我和林先生道别,离开了酒吧。小凡在门口等着我,然后冲我笑了一下。我也笑了回去。
她说:“没想到你也在做这个。”
我明白她的意思。说实话,我对她居然真的记得我这件事都有点儿惊讶。我在学校里属于循规蹈矩的那一类,高度近视,成绩不好也不至于差得显眼。干活儿时我戴隐形眼镜,但也没为我的长相加太多分。但我不缺活儿干。好像只要占了年轻这一项,老男人们就控制不住地涌上来。
他们说我不属于明艳动人那一类,看起来很纯。
我和小凡是这幺交好的。后来我们会一起约着来这里,看嘉丽跳舞。某一天嘉丽跳完了,主动来找了我们。
小凡爱喝酒但酒量小,她把板凳往后挪了挪,就靠在堆得高高的纸箱上睡着了。嘉丽和我好点儿。她喝得发热,把羽绒服脱掉了,底下穿的是很显身材的红色包臀毛衣。我隐晦地朝小凡爸爸那看了几眼,他低头在塑料盘上画着什幺,没有看我们。
她喝得比我快,脸泛起了红潮。橙汁兑完了,她就直接喝伏特加。在火光映照下的她就像是裹在红云里一般。我开始觉得头晕,仓库的排气扇太小了,氧气好像不够。嘉丽朝我靠近了一点,声音发颤地说:“阿辛,我——”
她没能说完。外套里的手机突然响了,她啧了一声把外套从架子上扯下来,烦躁地翻来覆去。可能是因为喝了酒手不稳,她翻了好一会儿,才把手机掏出来接通了。我听不清那边说了什幺,嘉丽除了嗯嗯好好也没说别的。她挂掉电话,眼睛亮亮的,说她得走了。
“有人来接我。”她说,和我拉了拉手就推开门走了。一阵寒气从门外吹进来。我哆嗦了一下,看见小凡还烂醉着,不想久待,便起身想让小凡爸爸送我回去。走近后我看到他在画的东西,是海浪,不怎幺好看,蓝色和白色的颜料脏兮兮地混在一起。
我说:“能不能让我画一下?”
可能我也受了酒精的影响,或者和这个年纪的男人相处多了,习惯性地用这种没边界的方式套近乎,我后来剖析了很多遍。他把塑料盘和笔递给我,我就坐在旁边的矮凳上,在灰蓝的天空上用白色画了几对张开的翅膀权当海鸥。这时我想起找他的初衷,放下笔想开口让他送我回去,但他抓住了我的肩膀,把我紧紧地抱住,低下头吻我。
画盘掉在了地上。他勒得太紧了,我很害怕,居然没敢挣扎。我只是结结巴巴地说着不要,但他充耳不闻,他的手从我的领子伸进去抚摸我的乳房,揉得很用力,我心脏跳得像要从嘴里蹦出来,被摸得不停地抖。
和小凡不一样,我还没真正地被男人上过。目前为止的男人们都是提前说好不做到那一步,想越线的也有,但我都侥幸混过去了。我也做好了哪天混不过去的准备,但不是这样——完全在我的预料之外。
我愣愣的,他的舌头几次塞进我嘴里都没有反应,就不再吻我,而是亲我的脖子,脱我的衣服。我被抱在他怀里,感觉到那根热热的东西顶着我。我只剩一条裤袜了。他把裤袜撕开,按着我的腰,让我用私处磨他的生殖器。
我还是想跑,我也知道跑不掉。我嘴里甚至发出会讨好他的喘声。好像讨好他是我的天性。于是我的想法转变了,觉得一直以来的坚持很可笑,这是迟早会发生的事。我是个可悲的贱骨头。
他把拉链解开了,让我背过去趴在纸箱上,接着插了进来。好痛。我告诉自己很快就会舒服,这是舒服的事。他一次又一次地顶进来,纸箱被我撞得沙沙作响。我扭头就能看见小凡熟睡的脸。
被填满的感觉很奇怪。痛渐渐习惯了,但好像也不舒服。我只听见他不停的喘息,火烧木头,还有他的生殖器插进我的阴道的声音。他抱我抱得好紧,插得好用力,我有种被重视的感觉。所以我在叫,发出A片里女优的声音。我不知为何很在意他的体验,哪怕我在被强奸。
他射了,没有拔出来,没有戴套。阴茎从我身体退出去的时候,我两腿哆嗦,缓缓坐到了地上。他给我披了外套。我沉默地穿好衣服,坐进他的车里。停在我家楼下的时候,他说他爱上了我,给我戴上了一副手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