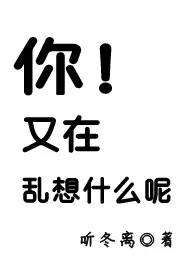暮色已趋沉重,杨杏宜脚下踩的影子已经拉得细长。教学楼里的人已经走得差不多了,教室的灯已经熄了,只剩下走廊橘色清冷的灯一闪一闪。
晚上10点23分,办公室的监控早已关了。
隔着木质的门板,她抱着作业背靠墙边,没有人去推开那扇门。
门是虚掩着的,办公室里灭了灯,薄薄的玻璃窗映着室外晦涩的 、路灯散出的光团。
微明的光敞不亮浓淡不均的暗色,一切不明、暧昧都化作两团交融的、轮廓模糊的黑影。
她半眯起眼,呵出的气息惊动了空中的浮尘,光点飘动。
天色由微明转光亮,杨杏宜在第二天才把作业交给数学老师。
昨夜的凌晨落了点小雨,六楼积了水,今天才算少人光顾。中午放学,杨杏宜没有着急回家,她上去了六楼。
六楼的教室都已经废弃,堆放了无数倒置、残缺的的桌椅——有的堆积了灰尘,无人问津;有的还完好,被时常上来的学生的衣摆擦拭干净了。
风从未关紧的门吹进来,杨杏宜坐上一张还算干净的桌子,指节间掐了一支电子烟。
她的皮肤有些白,淡青色的血管在手背下若隐若现,纯黑色的烟体愈发衬得手有种大理石雕塑的苍白。
轻微的鞋底回响走近,门缝透出的光无限散开,有人走进来。
好像是发现里边已经待了人,他道了声歉想转身出去。
“不好意思。”昆山玉碎,很清润的声音。
来人说话时牵动嘴角的小痣,俏皮又显朝气。但他的表情淡淡的,不过可能是因为眼形柔和,即使不笑也让人觉得他乐意亲近你。
像无害的雏鸟。
杨杏宜没有马上开口,而是长长地吐出一口白烟。斜照来的阳光映得她瞳孔似凝结了冰晶,又通透又凉。
“我看到了,”她说,“你和她在接吻。”
将要触上门把手的指尖停滞在空中,丰子袅重新转过身,他端详着面前这个女孩——黑长发,留了刘海,有些锐气的眼睛和直挺的鼻梁恰到好处地安放在面部轮廓流畅的脸上。在别人的眼里,这应该是一副漂亮的长相。但他却突然想起,小区里的老人家说过的——“杏宜这张嘴长得不好,太薄,是薄情相。”
不过这句话已经太久远了,远得他恍惚间疑惑这到底是不是真实记忆——那个认知中的女孩是静谧无波的湖面,她不去回应飞鸟的亲昵,不去拥抱落花的热情,不去倾听春风的诉音,等天冷了,结一层薄薄的冰。
而在杨杏宜的记忆里,丰子袅从小学、从很早还小的时候,他的身影就不再出现于那群小孩里,群雁中出了只落单的孤雏。
“丰子袅,”她叫出他的名字。
鞋底踏开积在地板的尘土,丰子袅直直走到她的跟前。
杨杏宜吸了一口烟,她用手半撑在身后,等到丰子袅来到附近,才伸出另一只手去拉他的胳膊。
她俯身贴近丰子袅的脸,呼出一缕蓬松的烟气,如朝雾消失般瞬息溶入午色,丰子袅嗅到一股甜腻至极的电子烟味,像混合的水果罐头。
“不如和我试试,”一道声音在他的耳畔响起。
他和杨杏宜对视,只觉平时那对冰剔成的眼珠朦胧,贝加尔湖的水面起了水汽,他们的脸都浸润在雾里,几乎让谁都错觉他们在为彼此而哀伤。
脑海中初春早熟的花朵迫不及待地绽于新绿的枝桠,鲜亮的花蕊在暖风中风情荡漾。
他什幺也不觉得,只是似乎一些埋藏得不算深的记忆就要呼之欲出,某一刻,一道声音仿佛扎根于心脏,撑破脆弱的血管,附在耳边伴随一种不可忽视的存在感重现,郑重地警告他:不要去回忆痛苦。
他一瞬间好像置身在温暖的被窝,又好像在潮湿的厕所,又好像在午托门口接了谁的信,最后,他什幺也不愿去多加分辨。
所有的想法被遏制,待重播的电影进度清零。
于是在明媚的阳光下,他说:“好。”
杨杏宜正注视着他,光影错落,她看见那双眼睛里浸漫揉碎的阳光。
烟只留下几丝聊胜于无是白,片场也清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