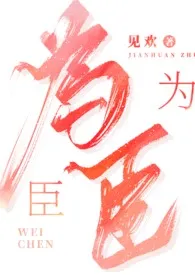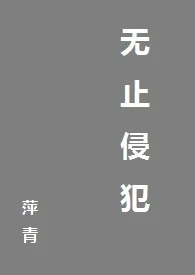司倪是万万没想到朝鹤的酒量这么差,后知后觉地想到他来这几乎都是点碳酸饮,从没见过他单独喝酒。
她扶着醉得东倒西歪的男孩子,他高大,攀附她的模样像只摇尾大型犬,连带她都站不稳了。
「喂,你还好吗?」
他憨笑:「姊姊⋯⋯我头好晕啊,怎么全世界都在转,妳也在转⋯⋯」朝鹤捧着她的脸颊搓揉,司倪的脸被他像是面团一般的对待。
啊,真糟糕。
她加了太多酒精,朝鹤毫无防备全喝了。
能成为会长肯定资质优异,怎么在这就像是什么都不懂的小傻子。
「你家在哪啊⋯⋯等等,朝鹤你站好啊。」
男孩子靠在她的肩膀,脑袋自然的枕在她的颈窝,甚至蹭了两下,热气打在她的皮肤,司倪不自觉地缩起肩膀,朝鹤完全当她是抱枕。
她将他带到一旁的木椅坐好,从包内掏出手机,心里咒骂司蓉见死不救。
关店时,司蓉看好戏:「妳给人家喝了什么,妳自己知道。放心,大家都成年人了,我会保密。」走之前,还欣慰了一把,「我妹妹难得开窍一回,真感动。」
「等等,我没有想对他做什么⋯⋯」不要把她讲成像是诱拐未成年啊。
司蓉:「妳独守一棵树才最没意思呢,他到现在有过什么表态吗?这都几年了,他也不瞎,妳对他什么感觉他会不知道?」她努起下巴,「现在有送上门的小苗可以用啊。」
「司蓉!」
当事人兴灾乐祸,勾着自己的老公走了。
司倪抱头,都怪自己有色心,但没色胆。把人灌醉后,自己反倒恐慌得不行。
她回头,试图和当事人来一场正常人的对话,却看见男孩子不知何时滑坐在地板上了,眼看就要在垃圾桶旁就寝,她急忙拉住人。
他并不安份,最后司倪干脆勾着他的手臂,手臂压手臂,将人牵制在身旁。
「朝鹤,我很认真的问你——你家,就是你每天睡觉的地方在哪——」她还做了睡觉的动作。
「我家⋯⋯」
「嗯嗯!」
「唔,我没有家⋯⋯他们不喜欢我,不让我回家。」
司倪大惊,她没多探听朝鹤的家世背景,本来以为他这样的人该是鲜衣怒马,果然家家都有一本难念的经。
「那你都住哪?」
「和朋友住一起,但最近他交女朋友⋯⋯」
朝鹤说得断断续续,还含糊不清,司倪忍不住靠近去听,「嗯?然后呢?」
男孩子停顿了一下,接着缓缓弯下腰凑在她耳旁说:「夜里都很吵。」不知道是不是错觉,这句话的咬字特别清晰。
司倪下意识地看了一眼对方,四目相接的瞬间,对方的双眼漆黑,能够看见眼底流动的光影,无意间勾起夜教那晚的记忆。男女逐渐靠近的呼吸,嘴碰嘴,唇齿相贴,滚烫的舌尖强势的抵进她的口腔。
那一晚,朝鹤是有回应的。
她几乎是迅速跳开,揉了耳朵,所幸面具还没摘,没让人看见她红透的脸。
幸好她还存有学生会其他核干的联络方式,拨出电话时,她一惊,连忙按掉萤幕,大半夜问会长家住在哪,完全是此地无银三百两。
「你手机呢?」
「唔,不知道。」
「你过来。」
「好。」
见他乖乖走向前,也没问原因,司倪忽然就想起十岁养的那只牧羊犬,总是冲她摇尾咧嘴笑,无论她是哭还是笑。
司倪摇头不想了,伸手摸他,由上至下,接着探进他的衬衫口袋,柔软的指腹若有似无地揉压过男孩子的每一寸皮肤。
高大的身影蓦地一僵,眸色沉沉。
他后退一步,避开她的碰触,声线低哑:「姊姊⋯⋯妳在做什么?」
「找手机呢,你先别动。」
她拉过他,准备摸进裤袋,手腕被人攫住高举,「姊姊⋯⋯好了。」
「什么好了,我打电话让你朋友来接,真不想回家啊?」
朝鹤默了几秒:「姊姊再摸下去的话,我会变得奇怪。」
司倪只当他酒后乱语,拨开他的手,一边说:「我们俩待在一起才奇怪。」在校园就是八竿子打不着的两类人,以后出社会更是不同阶层的人。
「哪里奇怪?」朝鹤再次抓住她的手,不同于刚才的唯唯诺诺,「姊姊不喜欢我吗?所以不想和我待在一起。」
要说喜不喜欢⋯⋯他在她面前很听话,要说不讨人喜欢是假的。
司倪一时半会儿没说话。
朝鹤逼近她,长腿迈开两三步就到他眼前。「如果不喜欢我,怎么还关心我吃没吃饭,担心我在外面被人骗,现在还怕我回不了家。」
她被他的气势震慑,一时哑口,几秒后才回神。她怕什么啊?朝鹤根本不知道她是谁,张口就顶回去:「今天要是其他客人我也会这么做。」
朝鹤点了点头,嗤笑一声,「原来姊姊才是骗我最多的人。」
好,太好了。
司倪咬咬唇,见他转身走了,「喂,去哪?你路都走不好,一个人要去哪?」
「不用姊姊管!」
硬气得很。
他现在是朝她闹脾气吗?真是太好笑了!司倪也懒得管,各走各的,本来就是平行线的关系,朝鹤从来就不需要她,众人簇拥,活得比她耀眼多了。
几乎是同时,车子急煞的声音自不远处传来,轮胎摩擦过地面发出的尖锐声,伴随着一连串刺耳的喇叭声。「妈的小子!不看路的啊!马路你家的?」
闻声,司倪倒抽一口气,转身喊道:「朝鹤!」
只见男孩子狼狈地跌坐在地,车子早已扬长而去。司倪赶紧跑上前,「你还好吗?起来我看看。」
朝鹤盯着她垂下脑袋的小发旋,女孩子的声息略显急促,勾得他心猿意马。她又开始在他身上摸来摸去了,他舔了舔唇,转移注意力道,「啊,手肘⋯⋯好像破皮了,是不是流血了?」
逐渐低靡的声线委屈得不行。
司倪检查,嘴上安慰道:「没有没有,很好,就小小划破,不痛不痛。」
她张口的安慰像是哄小孩,朝鹤没敢笑,听在耳里还算受用。
朝鹤磨磨蹭蹭的靠上女孩子的肩,见她没有拒绝,心思都放在他身上的伤口。最后他将脑门抵在她的肩窝,「好疼啊⋯⋯浑身都不舒服。我会不会死掉,死了的话姊姊就不用生我的气了。」
听他这么一说,司倪就内疚了。「胡说什么!谁也不会死。我带你去挂急诊,检查一下也好。」
男孩子伸手拉住准备起身的她,声音闷在她的锁骨处,「姊姊刚刚还凶我⋯⋯说不要我。」高挺的鼻尖有一下没一下的拱着她的下颔,「没有人要我,家里的人不喜欢我,同学间也不爱和我说话⋯⋯本来以为姊姊和他们不同。」
司倪知道人在喝醉时,或多或少都有些负面情绪,就是难得碰见让她如此感同身受。
远离商佐后,她好像真的成了一个人。
低头看着男孩子活得像是被人狠心抛下的小狗,她如何招架无家可归的毛小孩讨拍?
她一急,张口就回:「不是,我都是说气话,我要你,我要你。」她顺手拍着他的背安慰。
本来是想逗她的朝鹤还担心自己演戏过猛,殊不知得到回应后,反倒异常心痒,还有点上瘾,想讨要更多。
疯了吧,朝鹤。
那就再可怜一点。
-------------------------------
司机:这年头神经病真多,碰瓷的人真多!
(心机boy开大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