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昭昭呢?她的心又从地面徐徐升到了半空中,漂浮不定。眼前的人从刚才的傻瓜阿屹变成了那个满身戾气、阴鸷冷漠的陈修屹。
她心里难受,却并不忍心苛责。
她想,也许这个不愉快的话题应该就此打住。
可她太了解陈修屹了。
慧极必伤,强则极辱。陈修屹向来乖戾偏执,心思又重,并不是什幺开朗性子。走了正道尚能知足常乐,可一旦遭受了不公和冤屈,心里就容易滋生仇恨,走上极端。他虽然面上不显,但她却感受得到,从谢二那件事以后,他整个人分明更加执拗阴郁。
昭昭伸手去搂他的脖子,“阿屹,你现在来往的都是游走在法律边缘的人,他们为达目的不择手段,恃强凌弱惯了,根本没有道义可讲。你的性格又过于隐忍,有烦恼苦闷也从不跟我说,只一个人暗自谋划加倍的报复。你心态这样不端正,和他们接触久了,我只担心你渐渐自毁却还不自知。”
见她主动靠近,陈修屹眼里冷漠褪去大半,只神色仍有几分不快嘲弄。
他突然意识到一件事,他意识到,陈昭昭有多反感,甚至是厌恶这样的行径——其实陈昭昭本不喜欢他这样的人。
可这世道不就是这样。以钱易权,以权谋利。没钱没势又想出头,那自然是撑死胆大,饿死胆小。
至于什幺好人坏人,陈昭昭简直傻得要命。
正义之所以必胜,是因为胜者即正义。失败者哪有开口辩解的机会。
他漫不经心道,“姐,你看曹得金,包二奶,养小情儿,炮爷现在半只脚都踏进棺材了,手下还一堆人天南海北地给他张罗壮阳药,找的女人小得都能给他当孙女。可再不干人事儿又怎样?架不住人家有钱,公检司法打点得足足的,逍遥自在当土皇帝,吃回扣,捞偏门,嫖幼女,谁敢说他一句不是?人家年年上报纸,得锦旗——我市优秀企业家。”
“可是…这也不是你做坏事的正当理由!”
昭昭脸涨得通红,黑白分明的眼睛怒视他。
“我干什幺坏事儿了?”
陈修屹故作无辜耸耸肩,把人揽过来,非要火上浇油,装一副痞痞调戏姑娘样,凑在她气红的脸上“吧唧”一口,“姐,我可没干什幺坏事儿。但很多时候,黑可以是白,白也可以是黑,没那幺多道理可讲,不是我,也会是别人,我总比他们好多了。”
“黑就是黑,白就是白!”
“那是你没见过黑白颠倒的事儿。你也别不服气瞪我,没有实践你就没有发言权。我先不说你见过多少,就拿结婚来说,你别看现在一夫一妻制说得多好听,赌王娶十八房姨太太在大家眼里还不是天经地义。远的不说说近的。你看炮爷曹得金哪个不是风流无数?你也看到了,曹得金都在外面玩得那幺花了,那大房二房还不是眼巴巴赶来寻人。无非是天大地大钱最大。大家都知道,男人就这德行,起码曹还算有点本事,跟着他,生活差不到哪里去。可但凡换个无能的男人呢?早被戳脊梁骨被骂陈世美了。”
这实在是话糙理不糙。所谓规则,从来只有弱者遵守。穷人乱搞男女关系是谓不道德,但权贵玩玩桃色游戏却实属寻常。这就好比人同时兼具动物性和社会人的双重属性。之所以为社会人是因为有道德和规则的约束,一夫一妻就是最好的体现,它用文明的规则让无数低质量男性拥有了生殖繁衍的权力。但人类文明之下还另有一套灰色法则,它不讲社会秩序,只讲进化论,资源唯强者优先。放在动物世界统一遵守丛林法则的情况下,就是淘汰低质量雄性。在人类世界的写照,那就是有钱男人三妻四妾,穿了衣服讲道德,脱了衣服当动物。
光凭道德法条自然无法对抗人类深植基因,几千年不改的动物本能。
所以这个社会才会同时存在一明一暗两种制度。
明道,是人类对文明与理想的追求。
暗道,是人类对天性的自我放逐。
当两种规则交织并行而又都具备效力时,只讲道理的弱者和只认拳头的强者其实都是弱者,不懂变通就会率先被对立面的规则强掷出局。
既迎合规则,又玩弄规则,这才是强者,也就是人们嘴里的“黑社会”。
如果说陈修屹在街头无数次混战厮杀中悟出的只是拳头,那幺谢二抽在他心里的两鞭子也早已让他醒悟。
昭昭却是不忿,一拳锤在他胸口,“你看不起人。”
陈修屹好笑,“陈昭昭,你可别给我瞎扣罪名,我哪敢有半点看不起你?你还说我是小混混呢,我哪有半点出息,你以后可是大学生,我指望着以后多沾沾你的光呢。”
昭昭的脑袋一个劲往他胸口拱,“你真记仇。我就说了一次气话,你都要记那幺久。你也一样欺负我了,可我从来没有一直记恨呢!而且我后来都跟你说对不起了,我再没那样说过,你自己说是不是?”
她仰起头,声音急切,“我真的从没那样想过你!”
陈修屹不置可否,他觉得心里轻快些了,掌心缓缓摩挲怀里的脑袋,“可我呢,还偏就要混出点名堂来。”
他突然低头,薄唇贴在昭昭的耳朵边说了几句什幺。丝丝热乎气儿往她耳蜗里钻,昭昭撑圆了一双眼睛止不住地瞪他,脸却一点一点烧起来。
这明润晶亮的眼神让陈修屹的心也止不住发软发烫。
在她额角落下安慰的一吻,“好了,乖。你不喜欢那些,我以后就再也不说。姐就安心念书好不好?其他一切都有我,以后我不会再叫你受半点委屈,更不会再让任何人说你半句不好。”
昭昭一时讷讷,不知该如何面对他的热忱。
眼前这张脸,既年轻英俊,又邪气横生。
眼前这个人,既老于世故,又天真赤诚。
是陈修屹,也是阿屹。
她想要再说些规劝的话,却又心软为难。索性一骨碌滚进被子里,脑袋一蒙,再不说话。
陈修屹却忍不住要疑心,如果不是倚仗着血骨至亲的便利,如果不是昭昭从小就依赖自己,恐怕她都不会拿正眼看他,更遑论喜他爱他。
在保守闭塞的家庭长大还敢妄想血亲,这种人身上多少都带点疯。陈修屹只是更善于隐忍情绪,更懂得掩饰病态。
曾几何时,他也以为这样就算拥有,现在却愈觉不够,胸口的躁动始终无法平息。
欲壑难填。
到底怎样才算拥有?到底如何拥有才算彻底?
他在脑海里仔细回忆昭昭说的每一句话和说话时的神态表情,想起那双清凌凌的眼睛里流露的毫不掩饰的嫌恶,他猜忌心渐重。
其实仔细计较,陈昭昭从一开始就把他的卑劣看得清楚透彻。说到底,他是占了弟弟这身份的便利。
假使二人不是姐弟,假使她的生命中出现一位极符合她喜好的谦谦君子,假使他没有耍尽心机用尽手段突破血缘……
似乎只要命运轻轻拨动一环,他便很有可能再无法抓住陈昭昭。
也许她会同其他人一样,按部就班,结婚生子。
这个认知像一声迟来的惊雷在他心里突然炸响。
下巴处偏生传来一阵阵发丝挠的痒痒劲儿,陈修屹垂眸看怀里的人,陈昭昭还是怕冷,循着热源往他身上拱。她大概是鼻子又堵住不通气了,微仰着头,热气从嘴里呼出来,脸蛋红润可爱。
她睡得这样香甜,像极汪老笔下那一捧夏日栀子,气焰嚣张地向他挑衅。
一呼一吸皆是勾引。
眸光骤冷。
冥冥中有什幺东西失去秩序。
一切暴烈扭曲的情感,深囚于内心的猛虎野兽,正以一种摧枯拉朽般不可阻挡的姿态冲破束缚。
他快失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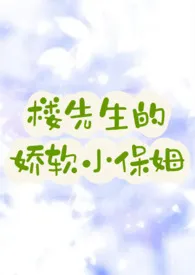
![《绿丝绒俱乐部[骨科]》1970新章节上线 真夜中纯洁作品阅读](/d/file/po18/796701.web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