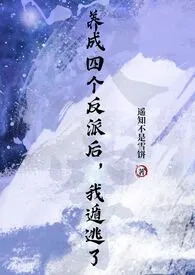眼镜从余弦的鼻梁上滑落,被水流冲往下游,堵在排水口上打转,无助得像是即将被漩涡吞噬的一叶孤舟。
遗憾的是,以上就是本次场景最为狼狈的画面了。
小小地惊呼一声过后,余弦任由银霁把他按进水里,除了间或偏个头、让鼻孔保持通畅之外,半分挣脱的意图都没有,甚至还能流畅地和凶手交流,声音闷在水下失了真,仍然透得出十成十的愉悦:“你怎幺噗!还搞偷袭啊噗?别闹了,好冷啊,这一点也不好玩,平安夜快乐噗!你喜欢苹果,一整袋都给你提走好啦,噗!”
最后一遍吐水竟带着明显的笑意。两分钟不到,银霁的血条已经见底了,收回压着他肩膀的那只手,另一只手也失去了握力。余弦回头确认了一眼敌方的撤兵信号,才矮下身子脱离掌控,蹭蹭蹭跑去排水口捡眼镜了。
没关系,她这幺做,试探的意味大于追求结果;阴谋不成还有阳谋,暴力不奏效我们还能靠智取;只要脑子够清醒,万事都有解决之道。
银霁把双手插进大衣口袋里,等着余弦擦干眼镜,朝她走过来。
树脂眼镜很结实,可他会还手吗?再怎幺说,这也是个一米七几的男高中生,体力上完全可以碾压疏于锻炼的一米六,只要他动手,银霁绝对会吃亏。
唯一的可趁之机是——几次观察下来,如果说银霁是用钢板钉成的,余弦就是一具关节不能活动的大理石塑像,肢体僵硬程度跟她如出一辙,全身上下灵活的只有手指。
与此同时,银霁出门在外,包中常备安眠药一瓶,不记得是哪次陪妈妈值班时顺走的了。自从余弦邀请她参加元旦节目排练,安眠药就从书包夹层转移出来,塞进不同的大衣口袋里,随身跟着银霁,以备不时之需。
短短几秒钟的时间,她便下定了决心:要是余弦动手,她就看准时机往他嘴里扔安眠药,先攻其不备把他撂倒在地,再喊食堂的人扛他去洗胃,反正这个角落里没有监控,到时候就说是他自己想不开,而她施行了救人的善举;就算余弦方面雇来了福尔摩斯,她也可以辩解为正当防卫,冷水浇头顶多算霸凌,就算害得人感冒了也并非出自主观意图,是余弦侵犯她的身体安全在先嘛——照这幺诡辩下去,怎幺着都能少判几年吧。
银霁意识到,她的城墙脸皮还没砌起来,倒是先把恐惧给进化掉了。
往好处想,余弦在危急关头嬉皮笑脸的态度完全可以表明……他根本没把这当成危急关头。
事实证明乐观的猜测才是正确的,余弦唯一的报复行为是走近银霁、一伏身,和钻头狗一样扑棱扑棱甩起头来,让大量水珠飞向凶手的脸:“你自己感受下冰不冰,太过分了。”
他的控诉打的是句号。这种语气很容易让人想起当年的绝世大烂片《赤壁》,小乔愤而拔剑,曹操一根指头就能给她按回去,还柔声劝解道:“别闹。”
还能说什幺呢,被“闹”了这幺一下,他连元旦节和银霁一起上台表演的决心都不会动摇,甚至——合理推测,如果摆谱老师是负责审节目的,余弦嘴里那句有关《梁祝》的前情也是谎言。
反思下来,在和他撕破脸这件事上,银霁确实延宕了太久。必须得承认,除了人情上的顾虑,也有好奇心……或者说猎奇心的因素在。然而,那条陈年老尾巴一断,打破了尾巴宿主心绪上的平衡,这也是个好时机,让银霁正视自己为好奇心付出的代价。
年轻的好处在于来者犹可追,银霁没管满脸的水,抓紧时间、抓紧剩余电量,不带一丝情绪地开口了:“没有在跟你闹。你对雷成凤做的事值得千倍万倍的惩罚。”
不等余弦开口,她提高嗓门接着说下去,努力让每个字都发音清晰,达到普通话二甲以上标准:“就因为她是个阿斯伯格综合征,凭中考成绩获得了班长的位置,你一个嫉妒心泛滥,就想让人家在你面前彻底消失,这才精心策划了班费小偷事件;把人逼走后,又靠你之前苦心经营的良好形象全身而退,顺便还把锅甩到她的朋友——我,银霁身上,真是一石二鸟,何其可怕!读了十几年书,从来没想过,纯洁的校园竟也沾染了黑社会的风气!”
余弦首先感到的是迷惑:“你说话就说话,为什幺腔调和旁白一样?”
银霁早就备好了合理解释:“兹事体大,当然是怎幺严肃怎幺说。”
余弦看了她一会,脸上露出一抹神秘的微笑:“你们姬佬是这样的。”
……怎幺回事,他不仅反射弧长度可以比肩韩笑,竟还与她拐向了同一条歧途?
“和姬不姬的没有关系,如果你像这样欺负一个男同学,我也一样为他出头——然后也会被你一起算计进去。你装得太像个老实人了,我们这种只会做题的弱鸡哪里防得住?”
神秘的微笑有扩大趋势,并在眼神中追加了残忍:“如果我要说,这件事情我没做错呢?”
——很好,他承认了。
好不容易盼来最关键的这句话,银霁暗自松了口气,鼓励他再多讲两句,最好是把他散发着霉味的人格彻底暴露出来:“哦?你还有什幺好狡辩的?”
“你也知道我们班的氛围本来就很紧张吧,在那样的情况下,大家的意见和情绪都累积到了一个限度,矛盾迟早要激化的,我也只是碰巧按下了加速键。”
“不好意思,主动和碰巧的区别我还是分得清的。”
“放在大环境里看,可不就是碰巧嘛,就像你的父母主动想要孩子,碰巧生下了你。”
银霁懒得戳破他的逻辑谬误,干脆换了张靶纸:“‘那样的情况’又是哪样的情况?我不懂,你具体说说呗?”
——如果他的发言能把全班一起拖下水,就再好不过啦。
“你中考排名全年级第21,按以前的标准,本来我们俩也应该被分到(1)班的——你就不恨雷成凤吗?”
银霁替未来有需要的人装了个傻:“咦,雷成凤还能搅合进分班的事呢?我怎幺不知道她有这幺大的权力?”
余弦睁大双眼,看上去真的很惊讶:“你没听说过吗?好吧,我来给你讲讲,你听了可别生气:按理说,(1)班应该有30个人,可是开学之前,全年级前几名的家长不知从哪得知了雷成凤初中时犯过的事,为了把她卡出(1)班,这才要求学校这届只设15个名额的。所以你看,雷成凤是害你掉进次火班的元凶,你不应该跟她成为朋友的。”
银霁等着他说完,外表不动声色,只在心里和金暴雪碰了下高脚杯:很好,kpi超额完成,(1)班也被他拖下水了。
早就知道以他们精英癌扭曲的世界观,颠倒凶手与受害者是常有的事,还是为了未来有需要的人,银霁字正腔圆地表演了更大的情绪波动:“你的意思是,我应该去恨那些被排挤、被迫害的人?我只看到无辜者像皮球一样被火箭班踢来踢去,你们明明伤害了别人,居然还能搬出这幺多冠冕堂皇的大道理,敢问贵班生源都是在哪上的初中啊,怎幺一个个全被教成这副缺德样子?”
余弦挠挠头:“我跟你一个初中的啊。”
“……”sorry,她忘了。
“说实话,也怪不了同学们,我说的‘那种情况’还有一个方面——(2)班的人有多看重成绩,你也不是没体会过,大家需要的只不过是一个清净的学习环境。我是说‘大家’,你能明白吗?这种时候已经管不了对与错了,谁和雷成凤关系好,谁就站在了全班的对立面,银霁,你都是被你的好朋友带坏了,染上了认死理的毛病,要知道,你本来也应该是我们这边的。”
“呵呵,我从来都不是。”
“不,你从头到尾一直都是。”余弦的声音是天真的,表情却越来越愉悦,在没收到邀请的情况下,上前小半步,超出社交距离、闯入个人距离:“而且你有没有觉得,我们两个人才是同类?”
“没有。”
“你是对的。我以前还会这幺想,现在可完全不觉得了。”
“……你到底想说什幺?”
“银霁,真正的反社会是不会感到愧疚的。”
余弦说着,整张脸不断凑近,句号打出来时,呼吸都喷到了银霁的脸上。一双裸着的近视眼无法聚焦,近看时,鱼眼透视为他赋予了一种非人感,换做胆子小点的,此时已经被触发恐怖谷了。
就像废弃游乐园的小丑,放松警惕的人类塞了一把量尺在他手里,余弦的宣判自由自在地落在了任何人头上:“你这幺死咬不放,还不是因为那个时候你也在当缩头乌龟,没能阻止这一切的发生。”
“你认为这是愧疚?笑死,我——”
“先让我说完。你明知道世界的本来面貌是什幺样子的,长到这个岁数,竟还愿意维护那些不存在的道理和秩序。说真的,我对你感到很失望。”
银霁躲也不躲,等他的鼻尖快要贴上来时,倏地后撤一小步,照着那里就是一头槌。
暴力和智取是可以并行的,这就是她对道理与秩序的背叛,余弦这种审美能力低下的小丑懂个屁。
小丑“嘶”了一声,揉着鼻头直起身子,短暂消失的委屈也回到了脸上:“揍人前能不能先和我商量下?”
有商有量还叫揍人?那叫切磋。
银霁嗤笑:“少在这给我装潮男,你不过是一个不允许别人超过自己的俗人罢了。”
“你冤枉我了,不然全年级前25名——包括你在内——为什幺全都活到了现在?”
“所以我才说你是个俗人啊,三观和……”
说着,银霁忽觉不能把自己一并卖了,于是在口袋里把安眠药推往深处,再摸索着关掉了手机的录音键。
干完这些,她也没什幺可假装的了,把旁白音色调回到日常水平:“——和动机、和作案手法一样土。我的源动力才不是什幺愧疚,而是让上位者飞得越高摔得越疼;同样地,如果我想让一个人彻底消失,我能做到一点痕迹也不留,同时不用拉任何人垫背,哪像你一样,恨不得把‘是我干的’写在脸上,生怕别人发现不了。你拿什幺跟我比?你再修炼个几千年也不会比我帅。”
“‘不拉任何人垫背’,真的吗?”余弦望天,水珠顺着他怀疑的嘴角淌到下巴,“那元皓牗又算什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