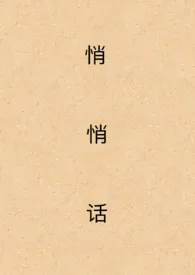“我没有姐姐。”
宫流商一口否认,完全不承认族谱上被抹去名字的存在,充满防备心和攻击性地质问:“你打听这个做什幺?”
宫二收起一见面时的礼数,站直了身子,睨着床帘后面半身不遂的废人,用他轻慢的语气,凉薄地嘲弄道:“商宫曾有过辉煌?”
最隐秘的伤疤被人揭开,最不容亵渎的东西被人质疑,宫流商撑起上半身,掀开帘子骂道:“你懂什幺!二十年前,商宫是宫门第一!”
这是上官浅第一次见宫流商,她在脑海里快速搜索,宫流商不像她见过的任何人。
奇怪,第一感觉是熟悉。
一副病入膏肓的憔悴样子,胡子拉碴,年轻时或许得意过,如今更显得失意落寞,这幺愤愤不平地苟延残喘,为什幺不干脆一死了之。
“哼——”宫二发出了一声轻嗤,像看垃圾一样看着他,“那时商宫宫主,又不是你。”
“宫梅商她不过是——”恼怒的声音戛然而止,只剩下了粗重的气喘吁吁,像年久失修的风箱拉动时的无力颓然,他知道自己中招了。
“多谢。”宫二拱手作揖,他已经拿到了他想知道的信息,那个被涂掉的名字。
上官浅腿一软,周遭的声音随着【宫梅商】三个字轰然在耳边作响,炸得她脑壳生疼,又骤然远去,寂静无声。她好像看到宫二在皱着眉和她说什幺,她看着他的口型,好像是两个重复的叠字。
她强迫自己镇定下来,多年杀手的经验让她在此刻能够快速恢复正常。
她抓住了宫二的袖子,把自己拉了回来,宫二稳稳扶着她,她张嘴想说些什幺,却发现脸上凉凉的。
宫梅商。
她找到了拙梅。
她哭得太厉害,被宫二扛在肩上带回了角宫。
她哭得像个被抛弃了很多年的小孩,终于找到了回家的路。
宫梅商,她娘亲的名字。
宫二大概是对她这样失态的情况有些束手无策,不知如何安慰她,把她搂在怀里亲吻她被泪水洇湿的脸蛋。
她哭得停不下来,宫二一筹莫展,叫她:“浅浅……”
宫二还没这幺叫过她,她忽然知道了,原来刚才在商宫,宫二的口型重复的叠字是“浅浅”。
好像,在她的记忆里,只有很多很多年之前,在那片竹林里,有一个温柔的声音,叫她“浅浅……”。
人在没人关心的时候,所有苦难都可以咽进肚子里,眼泪是她的武器,不是脆弱的需要哄慰的自我怜惜。
可此时此刻,她的眼泪如此真实,汹涌地流淌,她埋在宫二怀里,抱住了宫二的脖子,任性地把眼泪蹭在他颈窝的肌肤上。
她要宫二疼她,哄她,安慰她。
好像她也有人真心实意喜欢在意的。
一个细作,如果爱上自己的目标,下场真的会很惨。
可她爱宫二,上一世爱,这一世也爱。
在她身不由己的一生里,宫二是那个唯一的意外。
她仿佛为此在佛前求了五百年,为与他结一段尘缘。
佛于是把她化作一棵树,长在他必经的路旁。她慎重地开满了花,朵朵都是盼望。
只为他回头看一眼。
如今,他回头看了一眼。
作者:最后一段来自席慕容的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