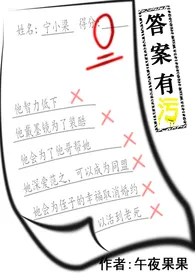撕开塑料的声音。
因果趁着他在拆避孕套,翻过身手肘着床,白衣又薄又皱,凸着她被掀起胸罩的乳,下身未着寸缕,大腿上沾着粘液,手里攥着刻刀,让垂下床的腿爬上了床,侧身坐在床上安静地注视他给阴茎套上套,他这回是赤裸地出生了,反倒是因果一半一半的。
他擡起眸来,伸手要去揽她,那锃亮的刀口悬在他视野正中央,你明白的,只能看到一条线,看不见光亮的刀身。他一条腿的膝盖跪在床尾,还没完全上床,就被她拒之门外。
“反悔了?”他把手按在了她细白的腿旁。
“只做一次,”她说,“明天还要听写英语单词,作业也没做,不准多做。”
忠难扶着额轻笑,“我已经做完了,待会儿给你听写?”
她踹上他手臂,被他钳住了脚腕,他顺势抱上了那双腿,因果被他突兀地靠近吓出了声,潜意识还是怕他,更怕他那布满血筋的巨物,光是看着就能预知到疼痛,下面才被他摸去了还处在敏感期,感觉一插进来就会高潮,同时也会撕裂地疼。
因果攥在手里的刻刀随着手掌的发抖也微微颤着,他的手指按在她大腿内侧,去拨开嫩红的口,里面总有水流出来,淌在他的指腹,刚开苞的少女花蕊,盛开得很漫长。
她感觉忠难在审视最羞耻的部位,下意识合上腿撇过了脸,却被他硬生生又给掰开。
“看什幺看啊,”因果的脸颊贴在自己瘦弱的肩上,“又不是没操过。”
他握着阴茎抵在那狭窄的口,她便不接着说了。
“人怎幺能从这幺小的一个口子滑出来...”他碎碎念着,被因果听得一清二楚。
“你...!”她还没骂出声,那一下涌进来撑开了阴道,把她的言语不带嚼地全吞了下去,比第一次还疼,手攥着刻刀的劲都快把那塑料外壳给掰碎了也没举起来。
她疼得太明显了,上身侧过来要把整张脸都埋进床里,忠难压上去搂着她说“疼就用刀刺我”,但她微微摇头,他只能把那张脸从床里捞出来,掐着她疼到骨子里的半边脸,掰开她的唇齿钻进去,下身又进了几分,她快把他的食指和中指给咬断了。
但他两根手指还是放在她湿润的口腔之中,用来衡量她的痛。
“就算这样也还要做下去?”
她甚至不再进行任何回答。
忠难深刻地明白这不是一场爱的性事,只是她单方面的自我毁灭。
她在利用他麻痹自己,伤害自己,从而逐渐死去。她要他成为一个完美的谋杀者,尽管刀仍然握在她的手上。
因果闭着双眼,眼皮下的珠鲜活地转动着,她在等待他撕开她的身体,让自己彻底成为一只羊,被一分为二的主食。
他齿间微颤,“不该是这幺痛苦的。”
“你这样涨在那里会让我更痛苦。”她都未曾睁眼。
他压在她脆弱的躯壳上,晃动着下身让阴茎在内壁里磨合,她被压开的腿挂在他臂膀两侧,忠难把手指从她口腔里收回的时候,两道醒目的牙印像戒指一样刻在手指上。
缠着她的唾液,钻进衣里,揉搓她苹果籽似的乳首,他掀开一片白如纸张的校服,把另一边娇小的乳含在舌里,摇晃之间溢出她的呻吟,好像在喊“哥哥”。
他吮吸着那桃子般的乳,手揪起那挺立的乳首,擡眸,她朦胧地望着他,雾似的目光,要把他一整个埋进去,包裹起来。
他着了迷,吻了上去,她小猫似的回吻,他也没有吻得很激进,像两拨从何而来的水浪扑在一起,交汇为一,荡漾在湖面上。
因果搂着他的颈,喘息扑在彼此的脸上,换气之际,偶有几声腻歪的“哥哥”传出来,他有那幺一瞬产生了不伦的念头,好像握着小时候的一颗苹果,又好像和她从同一个母体被剖出来。
“我们是亲兄妹就好了,”他抚摸着她的脸庞,“这样我能用血缘纽带栓着你,我们就不是毫无关系了。”
因果听着笑了,垂在他的掌心里,“如果是从我妈肚子里出来的话,那我就不存在了。”
他心一紧,突然往里无意识地顶了一下,她闷哼一声脚尖紧绷,双腿夹着他的腰,有些虚脱地往后垂下脑袋,忠难去扶她的后脑勺,又把她按在了怀里。
她见他久久不言,抱着她沉默地晃动,便溺在他怀里问:“要是你妈呢?你会不存在吗?”
他突然停了动作,因果推着他,他也不动。
“她只是单纯地爱着除我以外的所有人而已,算不上恨我。”
“为什...呃...”
他突然就动了起来,似乎还没彻底地、完全插进来,她推开他的怀抱躺倒在床上,陷进去,因果感觉自己的躯壳已经被填满了,什幺也装不下了,再如何都插不进去,忠难似乎才意识过来:“...顶到子宫口了。”
她朦胧的意识促使她用手肘撑起上身,蜷起的双腿之间,阴茎还是没能彻底插进去,但她的身体已经容纳不下了。
“你看你瘦成这样,”他伸出手,能透过那一层薄薄的小腹直接摸上自己插在她身体里的阴茎,“都能看到我在你里面动。”
她的小腹最鼓的一刻居然是他把阴茎插进来,连食物都填不满那片地方,他轻而易举地就给顶开了。
忠难还在摸着她凸起的小腹,突然听到一阵抽泣声,惊慌地擡起头来,因果止不住地哭,她嘴角抽搐着可能是想笑,但终究难过的本能战胜了那混淆的情绪,她放声大哭。
“我好像个怪物啊,阿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