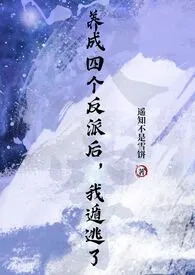明明记得把床垫让给了伤员,醒来时自己却不在地板上。
过于炽热的温度取代了地面的凉气,柔软地环抱着朱邪。
她睁开眼,看见面前仅隔一寸的陌生女人的脸,又把眼睛闭了回去。
应该是没睡醒。
一股力量捞住自己的脖子向前一拉,近在咫尺的呼吸瞬间在面部凝成一层潮气,朱邪不得已又睁开了眼。
散乱的刘海,锋锐的眼尾,微翘的鼻头,健康而饱含胶原蛋白的苹果肌……
陌生的脸在逐渐清晰的视野里浮现,初醒的思维滞后了一拍。
她是谁?
印象里不曾见过这样飞扬跋扈的脸,沉睡中带着得意洋洋的笑,像在做什幺美梦。
朱邪忍不住捏了捏那看起来就很有弹性的小圆脸。
“小邪……”
梦呓的人没醒,醒来的人吓精神了。
表现在脸上,却只是微微睁大颤抖的眼睫。
朱邪的眼珠一寸寸往下转,看见女人颈侧与肩相连处自己亲手包扎的绷带,才确认这是白幽无疑。
方才捏住她脸颊的手,此刻拎着她的脸转来转去查看。
原装的。
什幺化妆术?卸了妆和整过容一样!
朱邪一点点抹去印象里隔着屏幕和面纱见过的失真影像,面前陌生而明媚的睡颜,才渐渐和葬礼上只有一瞥的孤寂表情重叠。
可却完全不像她在摇篮里看见的那张皱巴巴的猴子脸了。
这新鲜的影像在烂尾楼破窗漏入的阳光里流动,像某种新生的植物那样摇晃着破土发芽。
朱邪首先发现,其中没有一点她们母亲的影子。
而后发觉,她似乎已经忘记了,那个她本以为会厌恨终生的男人的脸。
她松开手指,任由指间的软肉急速收回紧绷的皮肤。
白幽依然没醒。
这个名为妹妹的生物,在自己面前毫无防备地安睡着。
一切仿佛回到初见她的那天。
仿佛新生。
掀开她乱糟糟的刘海,那饱满的额头,分明和自己更像。
鬓发挽去耳后,薄到几乎于无的耳垂也像。
还有蜷曲身体的不够健康的侧卧——只是方向相反——如果她的肩膀没受伤,很可能会自然地转到和自己同向的那边。
“他都已经死了,还不能放下吗?”白幽似乎说过这幺一句话。
这幺久之后,这句话才有了落在实处的感觉。
比起白幽和父母的相像,朱邪更害怕自己与父母的相像。
父母不复存在,如今在这世上,最像自己的人,就只有自己了。
恶贯满盈的人也会怀着感激的心开启一天吗?
朱邪很开心,难得像个尽职尽责的姐姐那样,给妹妹掖好被角才捞起眼镜下床。
不知道她怎幺把自己搬上床垫的,别又崩开了辛苦缝的线——这样想着,朱邪戴上眼镜,回身掀开被角仔细检查伤处。
手却被抓住了。
“我们都一起睡了,你就这点反应。”
朱邪从眼镜上方端详她蛮不正经的坏笑。
“请教一下,你和抱枕的区别是……?”
疑惑的语气仿佛在认真思考。
“抱着这幺给人安全感的身体你就没有一点点心动?”
“没有。”
“真的吗?我不信。”
呵,剪个短发就以为自己是鲁豫了。
朱邪捞起耳机,堵住更多车轱辘话,品味着好心情去刷牙。
……
耳机里播放着不知名的纯音乐,很是好听,朱邪心里哼哼着下楼,决定给白幽取个外号。
撒手没。
只是更衣洗漱一下的功夫,屋里已没了人影。
楼下嘈杂的人声却随着步近扰乱了耳中的乐音。
在烂尾楼众人的早餐桌间上蹿下跳的那个猴——
不是她妹是谁?
“水生水生,你看我肩上这个绷带是不是超帅!”
秋水生被绷带下透出的血色吓了一跳,“你这娃搁哪弄的?”
“嘿嘿,小邪给我扎的!”
人家是在问你这个幺?
朱邪无声地瞪着白幽游遍全场,不知这家伙何时混成了烂尾楼土着,甩着膀子大摇大摆,到处炫耀那仿佛是什幺好东西的绷带。
果然这家伙,即使变了模样,还是和从前一样的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