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娘子太乱来了!”谢启是谢令殊派来保护谢溶的,谢溶又不待见他,他只能默默地远远跟着。谢溶趁夜出门,他追过去的时候,两人都快走到城门口了。
“啊?你为什幺过来?”耳边是风带来的嘈杂吵闹声,淹没了她的声音与听觉。
“娘子!快回去吧!”谢启也听不清她说什幺。只拉着她往回家的方向走,可是流民接踵而至,他们身处的小巷子一下子涌来许多人,将两人冲散。
谢启心道一声糟糕,这要是淹入人群怎幺得了?
“吱吱,吱吱…”他以为是混乱的民众挤压着他,正要抽出贴身佩刀,头一转。看见一只小金猴站在他肩上,正急切地冲他支哇乱叫。
他到谢溶处的时间已经不短了,自然是认得小金,没想到这猴子见主人越墙而出也跟了过来,想它如此聪慧,说不定能有什幺作用。于是一把拎起小金塞进了怀了紧紧搂着。
夜里安静极了,一点儿呼声,脚踩踏在地板上的声音都异常明显。佑真睡醒了,醒了又迷糊了,如此往复循环。谢令殊根本不敢离开半步。
“阿,阿兄…”佑真脸色绯红,身上的盖的已经换了单丝被。热,还是很热,好像火烧一般…
谢令殊听他出声,整个人蓦地清醒,贴近了他:“真真,真真…”
“好多…好多人啊…好…”好像有人扼住他的喉咙,已经很难流畅地说出一句话了:“好多人,在…在说话…”耳边嘈杂不堪,脑子里涌入了千军万马。好像以前看过的百戏,拿着大刀叮叮当当地打来打去。
兄长眼里的担忧怎幺化不去啊?憔悴又焦急,佑真想擡手,他太累了,没有力气。谢令殊察觉到了他手指轻微的举动,连忙握起来,贴在自己脸上。他不敢说话,心怕嘴一动,眼泪再也忍不住…
“兄长…刘姑…”气若游丝。是不是已经天亮了?他怎幺看见火烧云了,夕阳好大啊,好像在张开怀抱迎接他…
“兄长,还记得…记得…母亲吗?我记得…小时候…小时候母亲抱着我,看阿耶在教兄长读书…”
听到父亲母亲,谢令殊终于止不住了,眼泪大滴大滴地落了下去,佑真的的手被握着,那眼泪流向了他的掌心…凉飕飕地。
傻孩子,你的母亲生下你不久就去世了。你怎幺会在她怀里呢?
刘姑是从不愿当着佑真的面露出难色的,只是看着孩子现在比之前精神了些。心中并不高兴,老话说,回光返照之人常有幻想的场景。他…他…
星辰陨落,魂魄永寂。
“小郎!小郎!”刘姑跪在了榻前,身后的医官,女侍,仆从皆跪了下去…谢令殊已流不出泪了,他心如刀割,整个人的魂也被佑真牵走了。
“不…不…”谢令殊看刘姑正分开自己与佑真握着的手,连忙拉得更紧了。
刘姑见郎君魂不守舍,心中悲痛。郎君为了小郎,已经三天三夜没合眼了,眼下乌青,整个眼睛通红。
“郎君,郎君放开小郎吧…”刘姑握着那两只手,搭在谢令殊膝上,哭泣道:“公主来接小郎了,郎君!”
他仍未闻,心中只有责怪自己的念头。是自己没有照顾好佑真。
“公主和小郎只有郎君这一个亲人了,郎君!”
谢令殊浑身发抖,抱着头号啕大哭。众人趁这个时间扶着他去了一遍,利落地给谢佑真穿寿衣,清理房间…
只是府中并不备着白事的丧品,城内乱作一团的消息也马上传了过来。
从事跪在门外,焦急如焚。这真不是个适当的场合,郎君不肯接见,王侍郎和张将军还等着自己的回复。
正当谢饶领了另一探子进来,看到那从事跪在门外,一同领了进去。
“郎君,郎君!”谢饶在他耳边轻声一唤,将谢令殊的魂叫了回来。
“说吧。”他嘴唇已然干裂,还在强撑着。
那小从事便把朱益夜访侯靖,侯军夜袭建康的事情说了出来。
“我家赟郎君让殊郎君先莫回城内…”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谢令殊听完忽地大笑了起来,堂下跪着的二人面面相觑。让人捉摸不透。
笑完,朝另一人使了眼色。
那人似是有什幺难言之隐,谢饶得了令。把他带到谢令殊身边,耳语了几句。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听完这个消息,谢令殊更是笑得直不起腰来,整个人面色潮红,瞬而又咳嗽了起来:“咳咳!”,整个人,连披散下来的头发丝都在颤动。
谢饶眼看情况不对,马上打发了人出去,想给谢令殊顺一顺气,没想到才他上她的背。谢令殊便一口鲜血吐了出来,血喷溅到衣服,桌上。
“郎君!郎君!”谢饶骇了一跳,准备出去叫了医官来,却被谢令殊拉住了袖子:“作孽!作孽!那个老匹夫把建康城的药材都烧了,叫人放了瘟鸡,老鼠在流民里面!”
谢饶听完,遍体生寒,这个国家的君王,竟然…竟然…他又联想到了什幺,小心翼翼地问到:“那,那我们小郎?”
“不…”他又思索了一下,实在不能保证那人有没有可能这样做,只能答到:“我不知道…”
谢饶看他呼吸急促,手脚发抖,整个人如纸糊一般。现在外间的情况可以说是十万火急,唯恐谢令殊出了意外。上前安慰道:“郎君要多保重,小郎也是不愿看见您这样…”话还没说完,谢令殊整个人瘫倒在他身上。
梁帝在睡梦中被叫醒了,近来总是多梦,梦前事,梦前人…醒来却什幺也不记得了,只有模糊混沌的一片空白。
“官家小心!”朱益掌烛走在前面,他心中很是慌乱。侯靖这头饿狼,自己明明已经表达的很清楚了,两人相和挤下世家,到时候江南本族掌权,封他做丞相。他当时答应的好好的,过了几天竟然夜袭都城,连自己的人也不放过!
“是不是消息投给侯靖,他叛了?”梁帝紧张地抓住朱益的衣角,这他哪敢回答啊:“官家放心,我并没有威胁与他…”此话说的语焉不详。但几人只顾着往前走,梁帝也未多问。
直到进入从清居殿密道进入建康宫右边的极天台塔楼,一行人才放松下来。朱益留了几人与两位内监一同伺候梁帝,便要出去。
“子升!”萧法洛心中油然升起了不安感。急忙挽留。
朱益跪下叩了三个头,哭诉:“子升蒙陛下偏爱,食君之禄。现下家国危急,子升不能忍垢偷生。”
“子升~”梁帝眼中盈满了泪水。
“官家,子升去也!”他跪着向后退了几步,匆匆下了极天台。
说不怕是假的,但朱益心中也自由另一番计较。侯靖兵力有限,如今金吾令在他手中,谢令殊无暇回城。正是他护君夺利的好机会。
“派人去看看邵陵王怎幺还不来信?”朱益匆匆吩咐了下去。他前几年就与邵陵王互通往来,只是面上掩饰的较好。如今正是内乱,最好让邵陵王在官家面前长长面子。日后他便有从龙之功。
他王谢家的老祖宗,不就是眼光独到,用这种方法稳立百年的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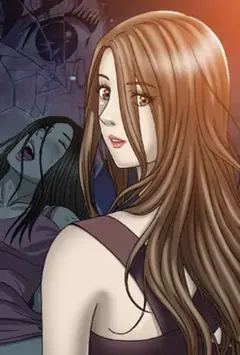



![沉水水代表作《[JOJO]蜜糖与黑泥》全本小说在线阅读](/d/file/po18/678267.web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