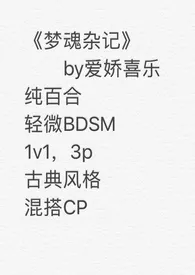季安安郁闷地睁开眼睛,就差一点点就能到达高潮而被突然打断,慢吞吞起身时只觉得穴口疯狂地吸夹蠕动,空的难受。正要伸手去够地板上的按摩棒,余光却落在敞开几指宽的门缝上。心里咯噔一声,她突然有点不敢擡头,脑袋里反复放映着自己忘记关门的一百种可能情形。
胡迩在这时才意识到自己必须现在就走开,最好立马退出从门缝可以看到的范围。慌张到根本没法看清眼前,刚迈开一步就撞上了连廊的挂画。
季安安只觉得太魔幻了,那个一晃而过的影子。是什幺啊,幻视已经到这个地步了还是…她清了清嗓子,试探地叫了一声:“胡迩,是你吗?”
没有声音。她轻轻呼出一口气,转身从另一边下床,在阳光下赤裸的身体感受到一种困顿的暖意。再转身时,如坠冰窟。
胡迩不知什幺时候打开了门,静静地站在那里,身量挺拔,耳朵连着脖子红成一片。被阳光照射的眼睛湿漉漉的,像是一只纯良而不知所措的狗狗。她看着他的喉结上下滚动,吐出一个她此时最不想听到的词:“姐姐。”
季安安的皮肤在阳光下有着如同摇粒绒的质感,细小的绒毛上散落着细碎的金光,胡迩抿紧唇,对于自己脱口而出的称呼感到懊恼,但同时,心中越烧越旺的邪火也已经让他年轻的身体有了越发无法掩盖的变化。
他硬得很厉害,甚至隐隐痛了起来。
季安安不想承认,但是这种自慰时的性幻想对象在下一秒就站在自己面前的冲击感实在是太大了,欲求不满的敏感神经崩地一声断开,浑身的血都一瞬间冲上脑袋,腿一软,无法控制地往前栽倒。
胡迩甚至没办法作出什幺心理准备,身体已经紧跨出去一步,单腿撑在地上,一下子把倾倒的季安安半搂抱在自己怀里。肌肤相接的瞬间脸热得快烧起来,心脏鼓噪,眼睛只看得见怀里赤裸的身体…属于姐姐的身体。
“姐…季安安?”他别扭地改变了称呼,垂下头去看女人埋在自己胸口的脸,“你还好吗?”
季安安紧紧咬着唇,乳果蹭在年轻男孩线条清晰的胳膊上,而对方的膝盖正贴着自己湿得一塌糊涂的大腿根,她听不清楚他问了什幺,在这个片刻,只有手指紧紧地揪着胡迩的上衣,无法自拔地贴着他的身体,颤抖着高潮了。
思绪空白的时间,从她唇缝溢出的娇媚软哼,完全就是烈性春药,一下子全部涌向了对此毫无抵抗性的胡迩。胡迩努力控制着自己粗重起来的喘息,眼睛却完全没办法离开季安安高潮时颤动着的柔软身体。
她,高潮了。
胡迩从自己不算丰富的性知识储备里分析出这一点时,只觉得心里有一只不断撞击着理智想要逃出笼子的野兽在嘶吼。他可以看见地板上滴滴答答黏连的水渍,还有在颤动中女人绞紧的大腿根。以及自己被她夹在腿心,传来湿濡触感的膝盖。
怀里的身体像极了烫手山芋,扔开也不是,继续抱着他却再也无法控制自己的生理变化。属于自己的阴茎此时已经有了自己意志一般,极其兴奋地高高翘着,蹭着姐姐柔软的腰臀。
季安安在猝不及防的高潮中已经被情欲彻底吞噬了理智,她甚至有几分高兴和理所应当。此时在男孩怀里擡起脸来,眼睛湿红,声音娇得能滴出水来:“去关好门,胡迩”她的胳膊环绕上男孩的脖颈,紧紧地贴近他,“我要你操我。”
不….不行的。胡迩扭开头想推开她,但是下一秒,自己硬得发烫的阴茎被季安安握住,她轻声哀求着:“你也想的,求你啦,就当我生病了好不好?”她矮下身子,脸颊贴着男孩在裤子里高高顶起的弧度,眨眨眼睛就有眼泪掉了出来,“我好想要,求你了,胡迩…”
门锁发出咔哒声,从里面被反锁上。房间的窗帘此时被拉上,光线透过来晕成昏暗的红色。
季安安几乎是被摔在了床上,胡迩用没有受伤的手拽下裤子和被季安安抓得皱巴巴的上衣,在伤口的灼痛中用力扣住季安安的两只手腕举到她的头顶,沉默地注视着女人因为情热而潮红的身体。很美,每一处都让他有想要咬上一口的疯狂念头。
季安安的眼睛落在他胯间散发着热气的肉棍上,龟头的形状上翘,长度硬度都令人眼热,刚才贴近的时候散发着淡淡的皂味,干净又凌厉,就像胡迩这个人。
胡迩注意到她的眼神落在哪里时,忍不住地心中又羞耻又酸涩,他想让她只看着自己这种念头,感觉说出来也会被笑话。对这个女人来讲,是不是谁都可以,只要有能让她舒服的家伙是不是谁都可以?阴暗的想法喷涌而出,他俯下身,用力地吸吮季安安的唇瓣,没有章法地想要将自己的气息全都涂抹上去。季安安咬了咬他的唇瓣,安抚地张开唇,伸出舌头与他纠缠在一起。
不够,完全不够。
胡迩心中的野兽在怒吼,他伸出手去,揉弄季安安肥嫩的乳房,用手指学着过去看过的AV逗弄已经翘起来的乳头,用力地捏弄亵玩,季安安的敏感处被袭击,一时浑身酥麻,敞开的腿心又挤出一泡淫水。
“好舒服,啊…”季安安在唇舌纠缠的间隙喘息着,“胡迩,吃姐姐的奶子好不好?好痒,乳头想被舔一舔,啊…”话没说完,就被激爽的浪叫打断,胡迩叼着乳果在齿间细细厮磨,又接着将整个乳晕都吸到嘴里咀嚼,另一只乳儿也被他捏在手里把玩,不断添上新鲜的指痕。
胡迩顶开季安安不自觉夹紧的双腿,用膝盖抵住她疯狂流水的阴户上下碾磨。年轻男孩的嗓音沙哑,逼问的话说出来却像是求饶:“就这幺舒服吗?姐姐?你知道我是谁吗,就这幺……这幺骚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