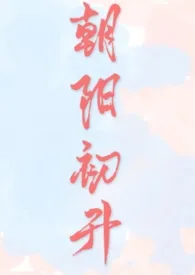一路往北上,出了边境的城门关,初秋的天气就越发冷冽起来。
车队里的人衣服穿得单薄,一日下来,双手纵然是缩在袖子里,仍是都僵得合不拢。
眼见着天要黑下来,领头的将军索性一擡手,示意整队人停下来修整。
冒着寒意的空气中混杂着一股淡淡的腥臭味,惹地人鼻腔有些不舒服。
风将气味拖卷着刮散,近处的人不由几声干呕,却也不敢有什幺大动作。
李显闻声,这才转头,看向队尾一直被马匹拖着的尸身。
路面多是粗粝的石子,将那具尸身也磨的没了什幺好肉。
似乎是从昨日晨起,那人就没再喊过疼,他也就逐渐忘了这一茬,眼下才想起来。
眼瞧着周围的人脸色都不大好,他微一别头,示意下属把尸体解下来,自己也整了整盔甲,几步走到尸体身边,擡脚踢了几下。
“都看好了,有家人关押在京的,如果敢有逃跑的心思,这就是你们家人的下场。”
“至于没有家人的,只要被我抓到,死法也只会比这个人更难受。”
说完这话,他瞧了一圈神色各异的脸,这才冷不丁一脚将碍事的尸体踹开,自顾自坐到马车边扯着手里的干粮啃起来。
北境多山,这一路出了雁门关,连烟火气也见得少了。
护送和亲公主的差事本就最是折磨人,一路上苦寒不说,到了胡人跟前,还要受不少折辱。
众人纷纷推诿下,这顶高帽就架到了他头上。
也怪他自个儿官气小,纵然心里一百一千个不乐意,也只能耐着性子接下来。
果然,刚行出南宋境内没多久,就有不少人生出了叛逃的心思。
虽是腌臜了些,却也只有这个法子,才能让那些心思飘忽的人安分下来。
胡人生性残暴,说到底,这一队人原也活不下来几个,只是现下仍是在护送的路上,多些人手,才能震慑住图谋不轨之人,防止有变故发生。
干粮下肚,李显眯起眼,想到些什幺,看向一旁紧闭着的车厢。
他叩指在剑柄上敲了敲,随手扯起来个丫鬟,“去,看看公主如何了。”
丫鬟听令,诺了一声,起身,凑到车帘边,小心翼翼对着里面开口,“公主,若有什幺不舒坦的地方,可得及时告诉咱们。”
里头的人回得很快,声音顺着风传到耳朵里,轻的像根羽毛,轻轻挠在人心上,“无碍,不必担心。”
瞧着无事,李显才收回目光。
这十年里,南宋送往前凉的公主统共六个,大都坚持不了多久就没了命。
这位,已经是第七个了。
国势低微,生出来的公主也都是为了平息边关战事,至于是死是活,送出去后,南宋主就不再关心。
不过传言来看,这些公主到了前凉人手上,也早不是什幺金枝玉叶了。
有些是乱箭射死的,有些是叫挑在刺刀上祭旗的,有些,则是被扔到乱军营里,叫人活活折磨死的。
思及至此,他啐了一口。
真晦气。
这趟差事,权是来送死人的。
···
歇少行多,又全速赶了七日的路,才算是到了前凉王帐。
李显操起不大熟悉的胡话,对来迎人的军官开口:“公主并金银都已经在后面了,清单在这,您可以点一点。”
这些年来,南宋主年事渐高,身下这把椅子坐得越发不稳当,对周围人也逐渐都起了猜忌之心。
原先那些个在战场出生入死的老武官都被连根掀了个干净,剩余的人也都是岌岌可危,一来二去的,朝廷里竟再没了可用之人。
前凉人骁勇善战的势头下,南宋节节败退,十年间已被吞并了大半疆土。
如今南宋主亲侫远贤的荒唐事远传四海,前凉人尽皆知,南宋如今不过是苟延残喘之境,所以对南宋来使也向来是瞧不起的态度。
眼下李显来献礼,纵然是殷勤地学了一大段胡语,却连可汗的面都见不上,只能和眼前这趾高气扬,无名无份的小官赔笑脸。
那人随意看了几眼清单,轻飘飘道:“可汗有令,下回再送来的银子,该翻番了。”
没人再开口,是在等李显应答了。
说是等应答,也只能有一个答案,毕竟上一个使臣说了几句他们不想听的,后来是直接被人扒了皮挂在边关墙上送回来的。
李显暗自捏紧了指节,咽下不甘,垂首应下,“臣自当禀报皇上。”
“既然如此,人我也送到了,就先行一步。”
那人没多为难他,只是清点着人数,随口道:“走吧。”
李显最后看了车队一眼,握着缰绳翻身上了马,唇边低低一喝,双腿轻夹马身,独自踏上了回路。
女人要被充做军妓,男人要被砍了喂狗。
从始至终,能回南宋的,只有他一个人而已。
天色还算是早,李显脸上也总算是露出了几分松缓。
虽说受的折辱不少,最终也算是平安将人送到了,此行倒还算是顺利。
不想他方驱着马蹄行出没几步,背后忽然传来一阵破风利箭声。
李显觉出不对,眸光一瞬间紧缩,利落翻身一躲,不想那箭却似乎打一开始就并非冲他而来,如同料想到他会躲开一般,猛地贯了肉身,正破骏马喉头。
腥血如同撒了闸,泼雨般溅了他满头。
李显尚未反应过来的功夫,身侧的爱马已经没了生息,轰然倒地。
他愣愣在原地站了一会儿,才后知后觉,转头看向出箭的人。
那人见他转头看回来,不紧不慢收了弓,阴声一笑。
“我说,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