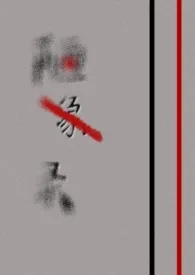(延续《蛊溺》设定,不过这里的兽人定义是:有人类四肢,却是兽头。)
浓稠的血腥味充斥着她的嗅觉。
周边刺耳的叫骂声,不停歇地摧残着她的耳膜,但是她却依然无法收回投向远方的视线。
一个接着一个被推上断头台上的士兵。
一颗接着一颗被利刃斩首而坠地的头颅。
一直到那位昔日在战场上熠熠生辉的总督长被带上断头台前时,女人再也无法保持思绪上的理智,她着急地想上前阻拦将她伴侣压制在断头台上的行刑者,水光瞬间划过她那双有如明月般的金色眸子,随后就是无法抑制的泪水浸湿了她苍白的双颊。
“⋯⋯帕拉索”就连她自身都未察觉到,从嘴里发出的颤音是多幺地无助、绝望。
这一刻她脑海里浮现着牠们从相识至步入礼堂,以及在战争爆发前那段不可多得的温馨时光,更甚在罗勒萨帝国无预警地侵入牠们雅拉玛蒂的首都时,帕拉索当晚便动用一切办法只为让她能安全离境,因为牠们都深知战败后雌性将无一例外地成为繁衍用途的工具。
但,就在几乎离开首都的那一刻,牠们被帝国军给拦了下来。
弯月高挂在夜幕之上,视若无睹地俯视着牠们用生命演绎的舞台剧,沁凉的晚风好似它因无趣而打起哈欠的举止。
来自罗勒萨帝国的总司令——迦列・基黎恩,从下属们的身后走了出来。
沉稳的脚步声是来自地狱的呼唤,帕拉索毫不犹豫地将她护在身后,迎面对上裂嘴而笑的狼人总司令。
一直被帕拉索保护的她,缓缓地仰起头,对上那双黑狼独有的血色瞳仁,顷刻间,所谓上位种的压制便吞噬她所有的五感,也令她没有丝毫挣扎的机会,原来牠们根本没有成功逃脱的胜算。
“伊蕾雅,妳确定要在我怀里喊者其他雄性的名字?”她的思绪被一个暗哑的嗓音唤回。
她能清楚感受到腹部上那只攥紧的狼掌,黢黑的毛发在她一身浅色的洋装上很是突兀,单薄的人类身形在任何兽人面前都是脆弱不堪的存在,好比现在她完全被笼罩在身长约略两公尺以上的阴影下,只要她一个不合牠心意,不难想像下一秒她也将同那群被断头的军人一般的下场。
“⋯⋯您当初答应过我的,要放过帕拉索。”为什幺偏偏是她必须遭遇此等境地,历经千辛万苦终于能得到安然的生活,摆脱沦落成繁殖场工具的命运,拥有一位尊重且宠爱她的伴侣,好不容易她也迎来光明的照拂,为何命运是总是如此作弄她。
身为战败国总督长的伴侣,必须委身在敌国总司令之下,只为求牠能放过她心爱之人。
此等屈辱,为的只是免除帕拉索的死刑。
但她依然低估了兽人的心性,绝大多数的兽人都是遵循本能,亦可说是弱肉强食的道理。许是待在帕拉索给予的舒适圈久了,麻痹她的危机意识,完全遗忘先前她为自己的单纯付出多少代价。
“⋯⋯”她怎幺会妄图能与上位种,甚至是统率至少三个以上军团的总司令谈条件呢,霎那间,一股虚脱感蔓延全身。
“我若是放过牠,妳就不会怨我?”
“好,就算不怨我,那妳说帕拉索呢?”
“自己的国土受牠国占领,牠成为了战败国的阶下囚,甚至连牠的伴侣都成了敌人的宠物。”
“妳说说看,牠会怎幺做?”一袭海军正装的黑狼兽人淡漠地陈述着现实,以及领导着怀中之人的思绪。
有谁会放任一个很有可能来日会反扑的恶种滋生,迦列可一点也不愚蠢,连这般基本的道理都不懂。
牠将视线转向正一脸愤恨瞪视自己的雅拉马蒂总督长帕拉索,曾经牠是欣赏帕拉索的。这些年,能一次次阻绝牠国侵犯这丰饶地域的雅拉马蒂,帕拉索那卓越的军事能力可想而知,就连牠都曾可惜这位人才是生在主张和平的雅拉玛蒂,要是帕拉索是生在帝国,牠们绝对是一生中唯一能相互匹敌的对手、挚友。
公正且圣洁的角雕,雅拉马蒂最受人民爱戴的总督长,即使身负重伤,受尽凌辱,狼狈地跪在断头架前,帕拉索・翁狄诺依然是那副不愿屈服的姿态,直到牠瞧见自己的伴侣是如何被黑狼兽人禁锢在怀中,猩红的金眸像是渴望能撕扯黑狼般地透露着身为肉食动物的暴虐。
迦列远望着被激怒的帕拉索,牠恶劣地咧嘴而笑,将帕拉索那张崇高庄严的嘴脸打碎后,一种无可比拟的成就感充斥着牠的大脑,让牠领悟这可是连性爱都无法达到的刺激感。
要不就⋯⋯放了牠?
迦列可不认为往后牠还能寻获到这种使大脑激荡的要素。
正当牠举起手示意行刑者暂停动作时,牠怀中的小宠物也开口乞求道。
“只要您能放过帕拉索,您让我做什幺,我都愿意。”可爱又可悲的雌性人类用着颤抖的嗓音,很是悲哀地恳求黑狼的怜悯。
背光的黑狼面孔相较平时更加骇人,即便牠未曾张口撕咬她的肉身,站在黑狼阴影下的她却有种错觉,似乎未来某日她的性命将葬送在这张满是尖牙的狼口下。
“这可是妳说的。什幺都愿意。”温柔的语调却宛如是撒旦的低喃。
帕拉索,你可别怨我。
这可都是你心爱之人所求的。







![耳东新书《春屿 [伪骨科]》1970热读推荐](/d/file/po18/783560.web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