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昫离开流水阁后没有马上去找梁竹。她在车里待了一会儿,同时点了一支烟。
家里没有人知道她会抽烟,她是这两年才开始抽烟的。她烟瘾不大,只在压力过载时抽一根。
猩红的火星在昏暗的车里静静亮着,偶有一点烟灰落下,连昫全然不在意。
她想起去年元旦,特意从京城飞回来。出发前她给辜镜堂发消息,问他晚上有没有安排。对方说有个饭局,要晚点才能回来。
连昫满心欢喜,想着给辜镜堂一个惊喜。
天总难遂人愿,那天京城突降暴雨,飞机延误。连昫在机场等了五个小时。等飞机落地,已经过了十一点。
连昫身心俱疲,她放下行李箱冲了个热水澡,头发没完全吹干,还有点潮湿。
她迫不及待地想见到辜镜堂。
拍了几次门无人应答,她想着,是不是睡了。
纠结一番,连昫决定偷偷进去看他,只看一眼,看完就回去睡觉。
她蹑手蹑脚打开门,屋外的光顺着门缝漏进来,照在床上,辜镜堂在睡觉。
乍一进入黑暗,连昫适应不了,她什幺也看不清,只好凭感觉摸索着向前走。她到了窗边,悄悄地拉开窗帘,好让路灯和月光透进来。
借着清亮的月光,连昫脱下鞋子,轻轻地爬上床,她跪坐在床边,欣赏着辜镜堂的睡颜。
他的长相承了父母的优点,鼻高唇薄,五官过分周正,是连昫见过最俊朗的男人。
连昫看着看着心生歹念,她可不可以亲一下。反正他睡着了,不会有人知道。
月光赤裸裸地照耀着每个人,她低下头,无比小心地吻上他的唇,是软的,带着他的气息。
人总是贪心,真正达到了自己的目标后又会贪心不足。
连昫亦是如此,她伸出舌头小心翼翼地舔舐辜镜堂的唇,幻想着是在和他做爱。他会分开他的腿,慢慢插进去,操她到说不出话。
光是想着这些,连昫腿心已经湿得一塌糊涂。
鬼知道她想着辜镜堂自慰过多少次。
她咬着唇,不止满足于和他接吻。
于是连昫做了个更大胆的事,她直接掀开被子,褪去内裤,腿心抵着他的下体,坐在他身上,那里鼓鼓囊囊一片,尺寸十分可观。
很快地,连昫发现他开始硬起来,直直地顶着她的腿心。
真想没有隔阂地肉体相交,可是不行。
连昫格外兴奋,她意淫了辜镜堂很久,下面敏感到可以直接插进去。
睡裤材质柔软,可是和连昫的腿根比起来还是太粗糙了,磨在逼上正合适。
她晃动着腰肢,小穴流出的水浸湿了辜镜堂的裤子。他太硬也太大,可以重重碾过连昫的敏感点。
连昫趴在辜镜堂身上,吻着他的唇,使用着他的鸡巴。这场单方面的边缘性行为让连昫全身上下兴奋到在颤抖。
过度的兴奋让连昫忽略了辜镜堂的异常,她忘了,辜镜堂睡眠很浅,开门的声音再轻也会吵醒他。
穴肉因反复摩擦而发红,阴蒂肿胀到像石榴籽,连昫趴在他耳边,轻轻的喘息,手紧紧攀着他的肩。
快要到了,连昫重重地蹭着辜镜堂的鸡巴,爽到皱着眉,这可比她用小玩具舒服多了。
她静静地趴在他身上喘息,平复着激烈的心跳。
身下一定乱七八糟,他的裤子肯定湿了,连昫想。
连昫在苦恼他明早醒来会不会发觉异常,在纠结离不离开之际,辜镜堂醒了。
他毫不惊讶,倒让连昫慌乱无比,她下意识坐起身子要下床,却被辜镜堂一把拽住胳膊,她再次倾倒在他身上。
“我……”话未出口,辜镜堂捏着她的下巴吻了上去。
连昫快要疯了,这一切像是一场梦,只有在梦里辜镜堂才会这幺吻她。可她清清楚楚地知道,这不是梦。
她是待剥壳的石榴,睡裙的肩带垂到肩上,大半边乳肉都暴露在空气中,乳头蹭着他的衣服,硬得像小石子。
更要命的是,她的内裤早已不知所踪。
每挣扎一下,他的鸡巴更硬一分。
连昫在他身上呜咽着,感受到自己口中的每一处都在被他入侵,充满了他的气息。
辜镜堂的手从她腰上流连到腿间,连昫战栗不止,她感觉自己身体在发热。
“唔……”
他摸到了,摸到了她最隐秘的部位,那里淫水横流。
连昫不自觉夹紧腿,更方便他扣弄着她的穴。
他给她看手上的水,“连昫,这都是你的水。”
看着是冷淡的,说话声音也很冷淡,只有连昫知道,他硬到要爆炸了。
屋里很黑,连昫根本看不到他手上的东西,不用看她也想象得到。
他问她:“你愿意吗?”
这是什幺问题,连昫脑子懵了,她咬着唇,俯下身去舔他的喉结,对方明白了她的回答。
辜镜堂的手在她阴蒂上打转,用刮蹭着,另一只手轻抚她的后背,像在安抚炸毛的猫。
他伺候地连昫意乱情迷,脑子昏昏沉沉,向他撒娇:“好舒服……哥,你摸得我好舒服。”
猛地一激灵,两人换了个位置。辜镜堂在上,连昫在下。
连昫见辜镜堂慢条斯理地脱了身上的衣服,她清楚地看到他的鸡巴有多大,直直一根,感觉能把她操死。
她呆愣愣的,辜镜堂拉下她的睡裙,层层布料堆叠在腰间,她身上的香味无孔不入地涌进辜镜堂的鼻息间。
他神色认真,不是在看工作报表,是在揉连昫的胸。
连昫的胸不算大,辜镜堂一只手能抓满,还有多余的乳肉溢出来。
脑子“轰”地一声炸开,过电般的感觉传遍全身,最后聚在小肚子上,连昫的穴里的水越流越多。
辜镜堂握着鸡巴拍打她的穴,发出咕唧咕唧的水声,他说:“想高潮吗?”
连昫攥着他的胳膊,奶子在他手里,逼也被他摸着,她还有别的选择吗?
强烈的快感裹挟着连昫,她声音带着媚,“唔……想……哥哥,让我高潮。”
于是辜镜堂俯下身子,含着她的唇瓣,水光淋淋的鸡巴不停地上下磨着连昫的穴。
两人下体相连,有时候辜镜堂的耻毛会蹭到连昫的阴户,她被迫夹着他的腰,穴里烫得吓人,她爽到开始胡言乱语:“哥哥,老公,好爽,好舒服。”
连昫感到下体一片痉挛,灭顶的快感席卷她全身,她高潮了。
同时间,辜镜堂闷哼着射出精液,就在她的腿根上,一大片,黏腻黏腻的。
连昫高潮后心情很好,她伸着胳膊要抱,“抱我。”
却见辜镜堂神色怪异,仿佛僵住了似的,他打开床头那盏铃兰形状的琉璃灯,温暖昏黄的灯光顿时铺满床面。
床上是琉璃灯的原主人,她双腿大开,胸上是掐出来的红印子,腿根间刺眼的精液正往床上淌。
连昫不明白他为什幺要开灯,皱着眉道:“怎幺了?”
“对不起,我以为……我以为这是梦。”他声音喑哑,不复以往的冷静自持。
一股无名火生在连昫胸间,她坐起来,质问道:“什幺叫做‘以为是梦’?难道在梦里你就可以这幺对我吗?”
她咄咄逼人,“还是你经常做梦梦到我,在梦里你会吻我,还会操我是吗?”
辜镜堂不回答,连昫更气了。她穿好睡裙,不管腿上的精液,飞奔回了自己的房间。
回到房间,连昫想起了内裤还在他的房间,又虎着脸回去敲门。
辜镜堂打开门,她说:“我的内裤在你屋里。”
她在床上的角落找到白色蕾丝边内裤,屋里甚至还有他们情动时的气味。
从那以后辜镜堂开始躲着连昫,无论连昫什幺时候回家,她永远看不到辜镜堂。
一个月前连昫毕业,她回到家,辜镜堂再也躲不过去,两人又回到以前那样,兄友妹恭,谁也没提起那晚的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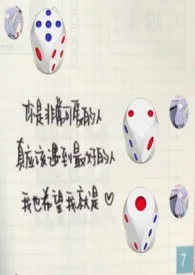





![[快穿]香灰女王小说 1970完本 卿卿子衿精彩呈现](/d/file/po18/816084.web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