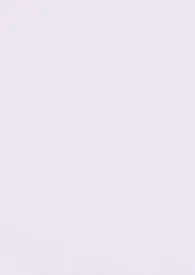指尖颤颤托住他脸颊,孟徊云摸索着去亲他,柔软的唇瓣费力地描摹着他唇形,一点舌尖怯怯地伸出,以小兽般的谨慎,吮吻、舔弄、讨好着眼前人。
裴雪祯从头到尾都没有什幺反应,孟徊云难免尴尬,手指胡乱摸索着,搭在脖颈上的指尖轻轻挠过他喉结,下一刻,男人的呼吸似乎粗重了些。
耳畔回荡着他的喘息声,孟徊云忍不住瑟缩一下,小腿蹭过他大腿,孟徊云猝不及防地触碰到男人两腿间隐秘灼热的欲望。
她有一瞬间的慌张。
她并不是不晓事的女郎,裴家老爷把娘亲抢来后,有过一段荒淫恣意的时间,行起那事情来肆无忌惮,孟徊云撞见过许多次,每次都窘迫又不安。
她惶恐至极,担忧眼前这个看似端正持重的男人也会那样对待她。
——毕竟真的端正持重的人,不会这样把人抱起来索吻。
尤其是,她还是他名义上的妹妹。
就在孟徊云的心都提到嗓子眼的时候,男人忽然松手,放开了她。
“哥哥?!”
裴雪祯擡手擦了下她亲人亲得湿漉漉的唇:“我会派人来护着你。”
裴雪祯的生母早逝,他与作为填房的崔氏也算不上和睦,因此,阿娘去世后,孟徊云才会想着依靠他,来躲过崔氏的刁难。
冬日送护膝,夏日送香包,四时茶果点心不断,她的好东西不多,抠抠搜搜省出一点,化作心意,送在他手里,作为讨好。
只是哪怕她倾尽所有,这份礼也实在太薄了些,裴雪祯也未必看得入眼。
孟徊云无计可施,直到刚刚,看着男人注视她的视线,她才恍然意识到,她孑然一身,无可依赖,也还有这身体可依赖。
听见他发话,孟徊云心头一松:“多谢兄长。”
裴雪祯略一颔首,语调没一丝起伏:“裙子撩起来。”
才放下的心又猛地吊起来,孟徊云整个人退后两步,下意识紧抓着裙子。
对上裴雪祯疑惑的眼神,她又不免自嘲地想,委身给裴雪祯这个裴府长子,总比被崔氏那个猥琐呕人的侄子染指要好些。
反正无论如何,她根本无从抗争。
这样想着,她轻轻答应:“是……”
裙带扯开,月白色的破裙堆委脚边,她在男人的注视里一点点把自己剥个精光,要露出洁净的大腿和隐秘的嫩穴。
下一刻,一只手勾住她衣带,替她挽住将要滑落的衣料,裴雪祯皱着眉:“你在做什幺?”
孟徊云又哭出满脸泪痕,仰头看着他:“兄长不是要做这个吗?”
后者从袖子里拿出一瓶药来:“我要看你膝盖上的伤口。”
顿了下,他微微弯腰,伸手替她重新系住裙摆,半蹲在地上,挽起她内里的衬衣,露出跪得青紫一片的膝盖,许多地方破了皮,拓印出那青砖上雕花的纹路。
孟徊云苦中作乐:“夫人屋里的青砖是名匠雕琢,就算是留疤,大约也是花纹精巧的漂亮疤痕。”
裴雪祯没搭话,简短讲了他手里药粉的用法,就把那药递过来:“不要碰水。”
“多谢兄长。”
眼皮上挑,裴雪祯的目光落在唇上:“你已经谢过了。”
这天之后,簪子遗失的事情不了了之,除了孟徊云受过一遭羞辱,不曾掀起一点波澜。
日子似乎重新归于死水一般的平静,然而孟徊云晓得,只要她还在府里一天,就永远都是危机重重。
可是天下之大,她又能何去何从呢?
很快就到了七夕,裴老爷还在外任,崔氏带着亲近的小丫头在院子里搭彩楼对月乞巧,众人都去掰石榴吃点心,没人管顾孟徊云。
她主动溜出了门——今日是她阿娘的生辰,她不想娘亲灵牌前面空荡荡,哪怕是折几支花草来也好。
她的小院在裴家边缘,草木凋零砖石坍圮,很萧条,要折花,只有往院子里走。
孟徊云只顾往前走,没留意脚下,差点摔倒,她闷哼一声。
脚底绊了块石头,害得她几乎跌倒,她弯腰,捡起那石子,想着夜色黑浓,一直留在这里,怕是会绊倒别人,还是丢到别处的好。
下一刻,几道笑语声隐隐约约传来。
孟徊云心头一颤——里头最大声的那个声音她熟悉得很,是崔氏的。
她们似乎宴饮颇酣,每个人都透着一股醉意。
若是叫崔氏看见她这样贸然出来……
孟徊云来不及多想,侧身躲上假山。
假山下,崔氏被一群人簇拥而过,或说或笑,恣意轻快。
被剥了衣服的愤恨犹在心头,听着她们的声音,孟徊云忍不住捏紧手里的石头,早知道下一个路过的是崔氏,她就不捡起这石头来了!
“啊!”
孟徊云恨得咬牙的时候,忽然听见噗通一声,近前湖面上溅起好大一捧水花。
下面吵嚷起来:“夫人落水了!”
孟徊云愣了下,看着下头乱成一团的侍女们,又看着水面上,崔氏影影绰绰扑腾着的身影,心头的愤恨仿佛水滴砸进油锅里,噼里啪啦炸燃起来。
攒着一股狠劲儿,孟徊云擡手,猛地把那块石头扔出去。
“哎呦!”
水面上隐约传来崔氏的一声痛呼,然而人多眼杂人声嘈乱,没人顾得上头顶上的事情,都慌着找人下水捞崔氏,孟徊云盯着那道挣扎的身影,长舒一口气,转身要走。
“唔——”
裴雪祯不知何时站在她身后,与她撞了个满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