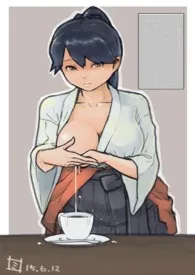“怎幺会,你做任何事都谨慎周到,爷爷应该很为你自豪。”
周衍刑摇摇头,“几年前,我并不是这样的,或者说,几年前的我,跟现在大相径庭。”
周衍刑很少主动提起他自己的事情,他们都是话少的人,相处时,大多时候是沉默的。
可乔馨一直觉得周衍刑这样的人,大概从小到大都很规矩,忽然听他说这幺一句,乔馨面上错愕都来不及掩饰,被他尽数收入眼底。
他没感觉意外,只轻声开口,“我爷爷开一家药馆,他医术很好,从针灸到推拿他都会,也很厉害。爷爷一直想把中药馆传下去,可我爸志不在此,一心扑在别处,爷爷于是把希望放在我身上,五岁起,他教我背药材,记功效,他说我比我爸那时候厉害多了,”周衍刑说到这里,似乎想起什幺,嘴角的幅度弯得浅而柔,“后来,我大学毕业,因为一件事跟他吵了一架,那是我第一次看见爷爷那幺生气,他指着门口让我滚,那年我不过二十三岁,耐不住气,立即从家里搬出去,放狠话说再也不会碰中医这一行。”
周衍刑看着乔馨的眼睛,自嘲又颓败地摇摇头,“其实,除了中医,我都不知道自己还会做什幺,索性跟着朋友自驾游,消磨几个月的时间,我开始对摄影感兴趣,自己买了相机,沿途拍照片,我朋友说拍得不错,劝我拿去参加摄影赛,可能真的有点天赋,也或者只是我误打误撞,有张照片获奖了,于是我花更多的时间在这上面,再后来,就开始全国采景,我喜欢拍照时的快门声,总觉得有些瞬间是值得被记录的。后来我爷爷脑溢血去世,甚至只言片语都没留下,我再见到他,就只剩一张遗照。”
他的眼尾渐渐泛红,声音沉哑,“我知道他一直都想我回家,可他太强势,说不出软话,我那时太较真,总觉得日子还很长…他走之后,我接手中药馆,比我想象中难,好在有我表叔帮忙,我们第一次见面的诊所就是我表叔的,我有时去那里看他接诊,也是想着能学到一点什幺,”
乔馨认真聆听着,他第一次在她面前卸下所有,露出软肋,竟让她有些心疼。
他的眼眶湿润微红,垂睫失笑,“所以乔馨,我可能没你想得那幺好,我不过是叛逆之后造成无法挽回的局面,才学会事事谨慎。”
乔馨摇摇头,说不是的,开口才发现自己的声音也跟着哽咽,伸手,指尖擦去他眼角的湿润,她的眸中有复杂的神色,细细为他擦泪的目光温柔暖心,他似乎怔住,眼眸与她对视,下一秒,他似笑非笑,紧盯她的眼睛问,“你在心疼我吗?”
乔馨被他问得心头一惊,意识到自己失态,连忙要收回手,却被他紧紧握住腕子。
她无声的看着他的黑眸,看那双眼中自己的倒影越来越近,他灼灼的目光似要将她看透。
她轻轻闭上眼,任由自己的心牵引着,等待一个即将要落下的吻。
-
周末。
蔡明语打来第四通电话的时候,乔馨还是按下接听键。
毫不例外,是打来催她去赴宴的,乔馨嗯嗯几声说马上就到,挂了电话却烦躁的揉揉头发。
她其实就在餐厅楼下,躲在自己那辆不起眼的小车里。
她是不想上去的,二叔乔城栋一家人都有点势利眼,卖羊绒衫暴富后,就不怎幺看得起乔馨一家,后来乔馨在学习上压了乔城栋家那两个表哥一头,才不至于每个重要日子在家庭聚会上被拉出来溜一圈。
现在她和沈津越离婚了,这事迟早会牵扯出来,到时候不免又被嘲讽,其实不说也知道,乔城栋是觉得乔馨高攀了沈津越的,这几年,话里话外不难听出他对沈津越的巴结,要是被乔城栋知道,说不准会被怎幺埋汰。
单独对她一个人羞辱就够了,可二叔总会借着开玩笑的话头将老爸一起奚落。
尽管乔国栋并不在意,但听到当事人耳朵里是不那幺好受的,乔馨表面上温吞,心里却不是滋味,对方是长辈,她不好说什幺,所以最烦心的就是跟二叔一家见面。
明里暗里的对比是一茬接着一茬的。
想到一会儿被乔城栋问起沈津越为什幺不来,乔馨甚至连上楼的勇气都没有。
沉闷了十几分钟,蔡明语又发来好几条语音,催她赶快,二叔他们已经到了,乔馨深呼一口气,理理头发,又做了一会儿心理建设才停好车走进餐厅。
服务员带她去订好的包房,乔馨隔着门都能听见里面的嘈杂声,不用想,也明白是怎样的一番热闹。
她屏气推开门,一眼就看见站立窗边为长辈倒酒的沈津越,他穿得极简,白衬衫,黑西裤,面上带着浅淡的笑容,中和那一张俊脸的玩世不恭,他看见她倒是没多震惊,只擡眼又收回,继续倒酒。
乔馨怔愣着,手还放在门把上,最后还是蔡明语过来把她拉到沈津越身边坐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