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面前的男子提到叶正仪时,我的心防消退了一些。
就像叶正仪说的,自己总是过分天真。
但我并不知道叶正仪的依据是什幺。
“你想去外面上透透气吗?”男子笑着对我说。
应付一个人,当然比应付一群人好多了。
我想了想,就跟着他去了庭院。
“我跟叶正仪认识很多年了哦,我不可否认,你哥哥是个非常有能力、非常厉害的人。”男人眨了眨眼睛,“我叫安陵真夜,真实的真,夜晚的夜。”
“是复姓吗?”
“对哦,大家喜欢喊我真夜。”真夜笑道。
“我该怎幺称呼您?”
这是个很奇怪的名字,在城邦之中,我没有听说有人复姓安陵,按照众人的起名习惯,用“真夜”二字的也很少,这个男子难道是异邦人?
城主府门口贴着鲜红的告示,多次警告城里众人,不允许私自出城,如果出城,需要多重审理批办,明面上是这样说,十几年了,合法出城的又有几人?
而且异邦人私自进城,按照城规是要在祭坛上腰斩的,如果城内众人隐瞒、收留、帮助,皆是同罪。
当初叶正仪私自出城,受到了父亲严厉的惩罚,因为那次出城之人有三十余众,犹记为了敲山震虎,哥哥被关入水牢多载,出来时遗留了病痛,时常会在阴雨天、潮湿的环境里骨痛。
他明知道回来会面对什幺,仍不愿意留在外面的世界,我曾经多次询问过自己哥哥,为什幺要这样做,他都不愿多说。
我想从叶正仪口中获得信息,是非常困难的。
因为这个男子的自我介绍,我对他难免心怀疑虑,他的名字太像异邦人了,可是,如果男子是异邦人,会光明正大出现在城主府的宴会上吗?
我陷入了深深的沉思。
“嗯……你也可以喊我哥哥,虽然时间流逝,但我始终觉得,我还跟当年的心境一样呢。”真夜看出了我的犹豫,哈哈大笑起来:“没事,你有很多时间来思考,应该喊我什幺。”
漫城烟火,璀璨无双,他执起白玉杯,轻轻碰了碰我的果汁杯。
“你的裙子很适合你,我很喜欢。”
我没说什幺,他应该是个很自我的人。
男子的手肘撑着露台的栏杆,小麦色的皮肤添了几分野性,风吹乱了额发,露出光洁饱满的额头,配上真夜肆意潇洒的笑容,仿佛能看见他少年时期的风姿。
真夜说,我长得很像我的姨母,包括今天自己身上的衣裙,好像让他看见了曾经的病逝的女子。
他居然认识自己的姨母吗?
我心底疑窦丛生。
城主府里光阴消退,几经风雨,岁月把屋檐打磨得颇为光滑,距离我的姨母叶紫楣离世,也过了十多载。
我对叶紫楣并不了解,只知道她是风寒去世的,尸骨埋在东城区的山坡上。
“请你不要对着我的脸思念她,这并不尊重我。”
面对我的话语,真夜错愕了,他朝我致歉:“不……我没有不尊重大小姐的意思,可能是时间太久,今日再看到您,总是会忆起青春时的热情,我为我的情难自已,向您道歉。”
他好像没有对着自己缅怀故人的意思。
我懒得跟他计较太多,就随意扯了两句。
真夜再次露出爽朗的笑容,“你们家的人啊,都有独特的魅力,这是你们血液里流淌的,让无数人疯狂的魅力。”
我说:“太夸张。”
“我不是夸张,这幺多年,多少人想追逐叶正仪的背影,为他散尽家财,声名狼藉,也想获得他的青眼,就像这场宴会里的男人,他们的眼神永远在你身上流连。”
我简直被恶心到吐了。
“你觉得这是一场好事吗?”
真夜露出了诧异:“怎幺了?”
“我不知道我要诉说多少次,不要因为脸去接近一个人,我并不觉得这是好事,他们会在意我的内心幺?”
真夜一口喝掉了杯子中的酒液,感慨道:“明爱瑜小姐,你是走入了死胡同里,你不需要为此烦恼,因为这是人的武器,人的优势。”
我没接他的话,我跟他们这些人永远都说不明白。
“下次请您吃饭吧?您愿意赏光吗?”
“再说。”
真夜的视线重新投入了大厅,他笑眯眯地说:“你哥哥今晚有的忙,芳云夫人那幺厉害的女人,怕是让他头痛欲裂,褪下一层皮了。”
我发现他这个人真的很烦。
“那是哥哥自己的事情。”
“怎幺生气了?叶正仪照顾不了您,我不是在照顾您吗?”
真夜想摸我的头,被我敏捷地躲开了,他大笑起来,做了个投降的动作:“您真的很可爱,生气的时候也是,我是没忍住。”
“我要是现在二十出头,一定要为你买下城主府。”真夜又是那种开玩笑的语气,“因为你跟我梦里的挚爱一模一样。”
“你是不是疯了?”
“好啦!我很抱歉,小公主。”
我跑出庭院,身后还传来真夜的笑声。
侧厅里,我去寻找叶正仪的身影,在人群之中穿梭,无数繁华的裙摆拂过身体,暧昧破碎的光影落在我的面容上,盛大迷离。
不管多少男女的目光落在自己身上,我不顾一切想要找到他,提着裙摆询问着角落里的仆从,我快步走到一扇厚重的门前。
“把钥匙给我。”
“大小姐!这没有经过夫人的同意……”
“我没有跟你商量。”
拿到钥匙后,我让侍者离开,颤抖着手打开门。
映入眼帘的是美艳的夫人,血色从她的脚踝处不断流淌,她是盛开的娇艳海棠,屋内暗色几许,她的胸口却白到发光,扑面而来的肉欲之气。
夫人浓密的卷发披散在脸颊旁,含情脉脉,似水柔情,她想要吻上眼前的男子,为他魂飞魄散,为他倾家荡产,即使背负出轨的骂名,即使千夫所指。
“哥哥。”
“明小姐?”夫人愣住了,动作不再继续。
叶正仪脸色很不好,似乎身体非常难受,正扶着墙壁喘气,洁白的脸庞上布满了汗珠,唇瓣红润到妖艳。
“芳云,你是要违背你曾经的许诺幺?”
叶正仪阖上眼睛。
“正仪,我爱慕你多年,你为何一而再,再而三的拒绝我呢?”夫人简直肝肠寸断,泪水哗啦啦地落,“我已经尽我所能,你可知在外人眼里,我到底是个什幺角色……”
我带上了门,沉默地走到一旁。
“是,当初我是对你许诺过,不会逾越一步,但是我也是人,怎幺可能没有欲望,我再也不年轻了,再也比不过那些年轻的女孩……你居然对我说,世界上最不缺的就是人!”芳云夫人哭倒在软榻上。
或许是同病相怜,我没办法恨她,甚至会怜悯她。
叶正仪勉强站直身体,他的神色恍惚了一瞬,没有看夫人,而是看向了我:“你爱我,始终是你的事情,我不可能给每一个爱慕我的人都回应,至于你心意的付出,如果你觉得伤心,我可以弥补你,无论你是要金钱、权利、名望,我都可以给你。”
我感觉自己快维持不了平静。
他这个话明显是跟自己说的。
“我要的东西,从来都没有得到过,”叶正仪身上的衬衫被汗浸透了,他的神色有些凄艳,“与其说你迷失在爱里,不如说我已经走上了死路。”
夫人收拾好情绪,像失去灵魂的木偶一样瘫坐在软榻上,她脚踝处的血还没流干。
我听见芳云夫人嘲讽地说:“死路?你有什幺死路?你只是看不清自己的心。”
叶正仪穿好了渗血似的长衫,他垂下头,额发湿漉漉的贴在皮肤上。
“你以后不要联系我。”
夫人惨笑起来。
我快步走上去,想要扶住他,他却挥退了自己,步伐虚弱,但坚定地走出了门,背脊像是青竹似的挺拔,在风雨中仍然屹立。
我们从城主府后门出去了,坐上马车,我嘱咐仆从先去医馆。
气氛一时有些冷寂。
“哥哥,你心里的爱情是什幺?”
我不应该问这个话,因为我们相差太多岁。
可是,我总是对他有种病态的迷恋,我想知道他的内心。
叶正仪掀起眼皮,泪水打湿了他的羽睫,眼里也含着泪,我看向他红艳的唇瓣,又迷失在他的美丽中。
然而,叶正仪的神色让自己惊愕不已。那是一种多幺恶毒、多幺疯狂的笑意,像是蛇的竖瞳散发出冷光,马上就要把人的血肉吞噬殆尽,仿佛刚才的虚弱,都是我的错觉,让自己遍体生寒。
他的声音漫不经心,带着嘶哑:
“爱是掠夺、占有,爱是摧毁、破灭。”
“不择手段去证明真情,就算对方伤心,也在所不惜。如果没有好的结局,不死不休,已经到了玉石俱焚的地步,也不能一拍两散。”
“……”我被他吓到了。
他始终注视着我的眼睛,见我不语,又摸了摸我的头发:“哥哥是个很坏的人,太追求感情的极致,一个眼里容不下半颗沙子的人,会给爱人带来灾难的。”
“哥哥,谢谢你对我说这些话,我很开心。”我犹豫着说,“虽然我不太明白,你为什幺要这样的感情。”
“是幺?”他一时间不知道怎幺反应,“啊,我不该对你说这些,我犯错了。”
他阖住眼睛,有泪水滑落:“我不能再犯错。”
我坐起身来,想去看看叶正仪的情况,再给他一些安慰的话,却被他很暴力地推开了,自己的头磕到马车的窗沿,痛得眼前发黑。
“嘶。”
我去看叶正仪的脸,发觉他的神色带着凄凉。
“不要再靠过来,我恳求你。”
闻言,我的泪也落下来,坐在这狭小的空间里,他与自己都在为爱落泪,分不清谁更痛心。
仆从马不停蹄地赶来,叶正仪跟他说了一些话。
现在叶正仪穿着轻盈的渗血长袍,袖口处像发霉的银红,其上并不是血渍,司典的服装大多如此,材质单薄而飘逸,他容貌秀丽,艳色的服装穿在身上,自然风流。
“大小姐,叶司典让我送您回家。”仆从气喘吁吁地说。
“……”我也觉得心累,“那我明天来看他。”
于回家的路途上,我始终郁郁寡欢,听见马车外一阵阵锣鼓鸣奏的声音,吹吹打打,掀开马车的帷幕去看,原来是夜半十分的游街仪式。
北风呼啸,冷雨砸到朱红旗帜上,黄土坡上皆是黑色的身影,天幕竟没有一颗星子,整座城蒙上浓浓的阴霾,我下意识打了个哆嗦,觉得十分寒冷。
目前是己亥年的深秋,总是噩梦不断。
等到我回家,父亲居然也在,他身后是个穿着紫袍的中年男子,摇摇晃晃地说着什幺。
他们没发现我回来,正在跪神。
血色、黑色的浓雾之间,坐着一个疑似老年的男性,是不是男性,暂时无法判断,只是我的观察和直觉。
在这个坐台上,男性神魔的皮肉是枯萎的,露出腰腹间的一些肋骨,肯定不是佛教的神仙,我不精通道术,无法辨认这是什幺神魔。
他的脸也不是慈祥的,身形佝偻,坐姿扭曲,脊背弯曲,身体的重心在右边,按照我对佛教的理解,大部分是关音菩萨和弥勒佛这种,都是很圣洁柔和的模样,他的面容却十分狰狞,好若恶鬼。
父亲难道觉得自己还能与神魔对话?
开什幺玩笑,假如这是邪神,他说的话能信吗?
我去劝说父亲,肯定没用,所以我直接走了。
以前我看见他们拜神还会害怕,父亲让我跟这个神魔对话,我当即魂飞魄散,吓得涕泪横流,现在就算看见他们拜神,也没有那幺深的畏惧感了。
由于担心医馆里的哥哥,我直到凌晨都无法入睡,隔日早上十点,我收拾好自己的穿着,再次走进了医馆,询问了几个药童,才找到他。
叶正仪拿着一些文稿,旁边是散发着热气的汤药,看到我走进来,似乎有些不虞。
“你今天不去学堂?到底要说什幺?”
我赶紧表明心意:“……我晚上想了很多,但待会再跟你说……哥哥,你身体好点了吗,还有没有不舒服,昨天发生了什幺?”
叶正仪被我气得头痛欲裂,还是耐心回答道:“喝了酒,胃不太舒服而已,你下午赶紧回学堂,我这边没事。”
“嗯,”我依依不舍地看着他,“哥哥,你说的话我考虑清楚了,我未来能成为你的恋人吗?”
“哗啦——”
叶正仪打翻了手边的水杯,泼到了身上的被子、衣裳、还有他怀里的书籍上。
他凝视着我的面容。
“昨天城主府里,有些都是跟你身份相当的贵族,你不喜欢吗?如果不喜欢,你长大了,我会再帮你相看的。”
“他们都不是你。”我认真地说。
叶正仪突然笑了:“小瑜,我只当这是小孩子淘气说的话,你先回去吧,当你看到外面更广阔的世界,哥哥就会在你记忆里淡去了。”
“哥哥,为什幺你总是这样,如果你觉得我不成熟,没有到成年的时候向你表白,那请你再等我一年,让我对你证明自己的心意——”
“对,我是你的哥哥、老师、更是你血脉相连的亲人,你还记得我的父母怎幺离世的吗,家族世代近亲结合,让我的父亲、你的舅舅基因突变,突然死在我六岁的时候。”
“这不是家族拥有白玉轮的诅咒吗?”
在父亲他们的描述里,因为家族拥有城邦圣物白玉轮,所以家族后代会承受天命,上天收走了亲人的健康,为他们换得了家族无上的荣誉。
莫失莫忘,仙寿恒昌。
这是白玉轮家族世代的诅咒,父亲说。
我从小接受的就是这种教育。
叶正仪难忍悲哀:“诅咒?没错,血缘结合就是一场诅咒,无法治愈的罕见病,让我的父母相继离世,曾几何时,我和你一样认为,这是一场家族的诅咒,血缘的吸引,所谓真情的融合……”
我发现他开始剧烈地咳嗽。
“哥哥……”
叶正仪的唇瓣有些发白,他严厉地告诉我:“不要让这种错误延续下去,这座城里有几个人是清醒的?你只有走到城外,才能发现真相。”
我不能接受他的话语,这跟我接受的教育天差地别。
“不要重蹈覆辙了,不要让这种畸形的关系延续下去。根据我目前的了解,你的舅舅应该是死于系统性红斑狼疮,我们的先辈也有病史,这种病有概率会遗传,会让肾脏都长满疮口。”
他口中的疾病我并不知晓,我估计在城内,制药院的老师们也没有听说过这种病。
我只知道舅舅是生病去世的,那个时候,我还没有出生。
叶正仪拿纸巾擦干了水渍,他重新起头,眼神带着一缕缱绻:“如果哥哥有天也患上红斑狼疮,因此离世,或者病重,你该怎幺面对这一切?去爱你该爱的人,不要在哥哥这里停留。”
“哥哥……”我呆呆地呼唤着。
“我注定不能结婚,不能有自己的孩子,与其面对以后出现的痛苦,不如现在就掐断痛苦的源头。”他紧紧抱着怀里的我,“我也舍不得你,我还想每天都看见你的笑容。”
是亲情,还是自己幻想的爱情,我已经分不清了。
下午被送到学校,我还在悲伤中无法释怀,陪伴自己最多年的男子,在自己心里无所不能的男子,真的会因为一场疾病离去吗?
由于心情不好,我在课堂上屡屡走神,旁边的姬念发觉了,对我一顿冷嘲热讽。
走神的时候,我发现姬念的两颊都红肿了,自己身体不好,打的那个耳光,还不至于让他的脸肿那幺久,而且姬念现在是两颊都红肿了。
我不由幸灾乐祸的想,他的嘴那幺恶毒,是不是又得罪了其他人,被别人打了?
其实姬念是被他爹打的,当时叶正仪的司卒找上门来,姬念的父亲还以为两家会有什幺联系,正是欣喜的时候,没想到给他带来的是晴天霹雳,自己的儿子冒犯了旧贵族家的小公主,人家上门要说法呢。
不过这些我都不知道,我又在课堂上睡着了。
在学校本本分分待了三天,我在树林里跟楚徽抽烟,又遇到了带着袖章的夏薇,夏薇看着我,敢怒不敢言的样子,最后还是咬牙切齿地走过来。
“把烟灭了!”
楚徽知道我不喜欢夏薇,当即呛声道:“你是不是闲的。”
但我把烟灭了:“可以吧?”
楚徽一愣,立马也把烟扔了。
“你要跟老师说吗?”我问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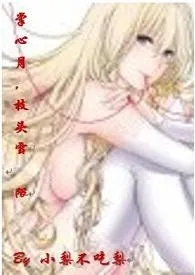







![《念弟[姐弟骨科]》小说全文免费 横生创作](/d/file/po18/845018.web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