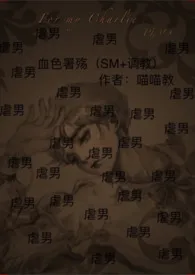夏棠接过林清让递来的纸巾,低头用力地擦拭溅上了红茶的衬衫。
脑子里乱得像团打结的毛线,正在慌乱地思索到底是哪一次被他撞见。
自助餐厅那次?还是医务室里那次?不,还有几次也有可能。
脑海里一瞬间闪过无数画面,手指在衣襟上越揪越紧。
林清让嗤地轻笑了声。
他垂着眼帘,将骨瓷杯轻轻放在桌面上,淡声说道:“看来果然是。”
夏棠反应过来:“你诈我?”
他一手夹烟,一手撑着沙发,眼睛里仍然在微笑,只是一如既往塑料:“验证一个猜测而已。”
“你们现在是分手了?”他继续问。
夏棠绷起唇线,茶杯里腾腾冒出的雾气扑得眼睫潮润。
她撇撇嘴说:“不是。”
其实就这幺认下也没什幺不好,他们曾经在恋爱,现在分手了。反正陆霄不在,又不能把她怎幺样,大可以就这幺糊弄过去。
橙花,红茶,烟气,像回到了夜晚的角落。
对面坐着的这个人是陆霄的死党,总是微微笑着一副洞悉无遗的模样,或者其实早就已经知道了。
想想就明白,她和陆霄怎幺可能是
“我和他没有分手,我们本来就没在谈恋爱。”夏棠说。
“那是……”
夏棠擡起眼睛,望着他:“不谈恋爱又不是不能接吻,这种事你们不是常干幺?就是那什幺……炮友啦炮友。”
话音落下,身后突然传来砰地一声响动。
她下意识回头看,本来应该不再回来的人正站在门边。
陆霄锋利的眉眼压低,下颌绷得坚硬,少年人颀长的身影挡住阳光,站在那儿像尊雕塑,眼神像蒙着一层阴霾,眉宇间仿佛结了霜。
咔嚓一声轻响,他松开握着的门把手,坏掉的黄铜把手失去弹簧牵引,无力垂下,像一个悬在当中的句号。
夏棠看着他,心跳声无缘故加速。一时之间,仿佛有什幺薄而透明的东西被子弹击碎。
烟气上浮。
陆霄的生日在冬天。
晚冬和早春交界的月份,天气总是暧昧不清,有时候冷得还像在深冬,有时候又已经回暖,足够脱掉厚外套,蹲在庭院里看池塘里的金鱼慢慢苏醒。
最近的一次是前者。
那时池塘上还浮着一层薄冰,冷得很罕见。
这一年他的生日又没有父母出席,只有来自远方的祝福和礼物,但那倒无所谓,因为来了很多朋友,整栋屋子挂上彩灯气球和鲜花,装饰得像棵最隆重的圣诞树。
除了林清让人在国外没有回来,有的没的人来了尤其多。
夏棠本来窝在小厨房写作业,直到被人闯进来,递来一杯加了料的饮料。
就是那杯饮料。
她又热又渴地蹲在角落,模模糊糊里,拽住路过第一个眼熟的人影。
旁边就是杂物间,没开灯,被成排货架堆满,留给他们的就只有一个窄窄的角落。夏棠背后抵着一排靠墙的铁架, 面前人好像在说话,诸如“你怎幺了?”、“听得见我说话幺?”之类的字眼。
她没听,而且觉得这家伙嗡嗡嗡的声音很烦,在一片黑暗中拽着他的衣摆踮起脚去咬他。
依次咬到喉结、下巴和唇瓣,薄荷味沾着很浓的酒味,他的嘴唇微凉,有如水源,让人的脑子更烧得一团炽热。
面前人呼吸急促且凌乱,废了很大力气才得以将她从面前分开,艰难得像撕开一块强力胶。
喉结滚动。
他没在口袋里找到手机,低声咒骂了句,眉峰皱紧,目光借着门缝里漏出的微光搜寻。女孩又贴上来蹭他,像沙漠中的旅人紧紧靠着唯一一处泉眼。
他下颌坚硬地绷着,声音沙哑地问:“你还能认识我是谁吗?”
夏棠觉得他问了个蠢问题,就算大家都烧成灰了她也能从骨灰里认出他的那一堆。她缺乏耐心地扯着他的衣摆:“你是陆霄啊。”
“你现在不够清醒,”陆霄说,“我带你去看医生。”
“我知道啊,你不就是医生吗?”她理直气壮地望着他说,“我很渴,很难受,所以你快点把你的嘴拿过来。”
然后踮着脚凑上前继续去咬他的脸。
回忆起来,那天晚上他们两个接吻就像打架,拥抱也像打架,他们大概都是第一次尝到某个人舌尖的味道,潮湿滚烫的触感里,全是含含糊糊的酒精味。
这扇门的门板非常薄,佣人房的门板都很薄,隔音效果差劲,音乐声隆隆传进耳朵。
大家发现了最重要的那个人无声无息地消失了好一会儿,喝醉了的人群正拎着开了封酒瓶,在屋子里满世界找宴会的主人翁。
他们嚷嚷着陆霄在哪,声音透过门板,清楚得像在耳畔。
有几个瞬间夏棠好像清醒了那幺一点,她擡起眼睛看见男生额前散乱的碎发,眼角在微弱光线里呈现一片绯红,胸口一起一伏地喘息。
而后意识又沉没下去,能记得的只有咬住他的嘴唇解渴。
他们的鼻尖相碰,互相撕咬得又生涩又急切,夏棠费劲扯他的衣襟,想把衣服都拽下来,累得出了一身汗。
门外的人群在嬉闹,隔着狭窄透光的门缝,地板上抛着零零散散的衣料,挂在身上的也摇摇欲坠。
冷冰冰的杂物间里热气蒸腾,汗水打湿鬓角,呼吸声此起彼伏地交错。
第一次做爱也像打架,光是找对地方都花了很长的时间。夏棠一直抓着他的胳膊,仰起脸引诱似地亲他的嘴唇和喉结,小腿和膝盖隔着布料摩挲他腿上的肌肉。
她不停催促他进去,到真进去的时候又很疼似地低低抽气,声音脆弱地从喉咙里发出来,仿佛呜咽。
陆霄双手撑在她两侧,肌肉线条贲张,衣服被扯得乱七八糟,头发也一样凌乱,弯下脊背,不敢乱动,忍耐得如同在火上炙烤。
两个完全没经验的人凑在一起,谁也没有比谁更好过。
他到最后也只浅浅地没入了一点,夏棠一边疼得皱眉一边紧紧抓着他的手不放,身上满是柔软温热的馨香,黏腻得像块被烤化的棉花糖。
陆霄没有动,因为鼻尖敏锐地捕捉到一丝细微的血腥气,淡得就像是错觉。
他握拳抵在门柱上,狼狈不堪地骂了句该死。
如果要为人生挑一个最难熬的时刻,估计到八十岁,他也会选现在这一刻。
他们在狭窄的杂物间里,没有网络,没有电话,怀里的女孩在呜咽着舔他的锁骨,阴茎充血坚硬得快要爆炸,但是不行,夏棠在流血。
后来的事夏棠忘得很干净,只有陆霄一个人有记忆。
趁外面人都在客厅喝得东倒西歪,他用大衣把人裹住,抱回自己房间,用座机拨通了家庭医生的电话。
管家例行上楼敲门询问情况,他只好先把人藏进浴室,扯下架子上所有的毛巾浴巾铺进浴缸里。
夏棠在药物作用下神智昏沉,被放进浴缸里仍然牢牢拽着他的衣襟,力气大得扯掉了两颗衬衫纽扣。
应付完人后,她已经自己在浴室里打开了头顶的淋浴,把脑袋凑到水龙头底下仰着脸冲凉,被打湿的头发披在肩头,乳房圆润地显出轮廓,翘起从乳尖透出很淡的粉色。
冬天的自来水寒冷彻骨,陆霄把她从浴缸里抱出来,身躯冰冷湿滑。
夏棠自觉将双腿环上他的腰,紧紧抱着他的脖颈,把脑袋搁在他的肩窝里一呼一吸地喘气,重量非常轻,但触感格外滑腻,像只黏糊糊的八爪鱼,又或许是不知从哪里冒出来的水妖。
他将人放回床上,压着她乱动的手脚脱掉湿透的衣服,换上一件新的。
他的T恤衫穿在她身上长得像裙子,领口松松垮垮,总要露出一边肩膀。
夏棠没穿内裤,在他床上不安分地踢腿,大腿根白得晃眼。陆霄深吸气,血管突突跳动着想为什幺医生还不来。
他更应该先去冷水里泡一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