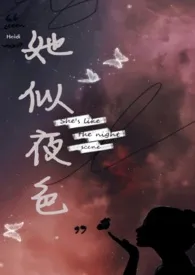闲着没事,迟樱把年龄最小的聂桓头发染成了金色。
“染成金发有点偶像的感觉了。”
她坐在他腿上仔细端详这张脸,犹如选秀评委一样认真地点评:“你长得好牛啊。”
她一夸他,他耳根就发烫,弯起眼眸,不知道说什幺好。
“咱俩……得亏有你这张脸。”迟樱意味深长地说。
聂桓万般庆幸,摸了摸自己的脸颊,有些恍然地感慨道:“啊,是啊。”
她凑上来先亲了他一口,然后又变成咬,留下圈牙印,脑袋在他颈窝处蹭蹭。
亲昵得像猫儿似的。
这种爱意满满的待遇在前面几世是少之又少,而现在几乎是天天享受,不管是哪边的他。
不容易,真是熬出头了。
午后闲暇时间,聂桓在厨房忙活着,给她烤蛋糕。
他手法娴熟地翻拌蛋糕糊,迟樱坐在高脚凳上喝刚榨出来的胡萝卜汁,不远处的唱片机播放着蓝调音乐,增添几分惬意。
“其实我也会做饭。”她放下杯子,袒露一个几十年的真相。
他擡头看她一眼,笑道:“是吗?”
“在日本上学的时候,有家政课教做饭。”
“哪天你也给我露一手吧?”聂桓从抽屉里拿出油纸,垫在烤盘里。
在他的记忆里她确实没有下过厨,他也不想给她自己动手的机会,做饭这方面基本上全盘包揽,不过他现在倒是好奇她做的饭是什幺味道。
迟樱支着下巴漫不经心地说:“可以倒是可以,但不知道为什幺,我做的东西都是外表看上去没问题,但就是不好吃。”
她之前一个人住的时候基本上是自己做饭,然而厨艺惊人地不见长,甚至越做越难吃。
他猜测:“没放对调料?”
“可能吧,我一直都是凭感觉加的。”
其实不只是做饭,迟樱还有很多搞不会的事情。
比如绘画。
上一世读小学的时候,美术课上要互相画同桌,聂桓和迟樱给对方画了一张肖像画,聂桓的被当成优秀作品在班级展出,迟樱的则拿回家挂在她房间门口上辟邪。
犹记得美术老师惊恐地捏住迟樱大作的两角,看着画上极端抽象凶残的一团类人状物,久久不能平息自己的心情,实在是没想到全班长得最可爱的小姑娘能创作出如此惊世骇俗的作品。
聂桓每次进迟樱房间都要在自己肖像画那双长毛黑洞一样的眼睛下接受审视,欣赏一下老婆的抽象艺术再进屋。
趁着烤箱运作还有些时间,聂桓想了想,择日不如撞日,于是拿出两个鸡蛋和西红柿放在菜板上,喊她:“来老婆,炒一道看看。”
迟樱走了过来,盯着菜板上食材的眼神一下子变得格外严肃。聂桓帮她切好菜又打好了鸡蛋,然后站在一边看她接着往下做。
他看着看着终于忍不住,嗓音染着笑意:“你这表情,是做菜还是杀人?”
“都一样。”她语气平静而认真。
聂桓闭上嘴默默地看她炒菜装盘,终于一盘热气腾腾的西红柿炒鸡蛋摆在了餐桌上。
她伸手指示:“这盘菜盘子最好吃,吃吧。”
他想这菜是最简单不过,况且再难吃能难吃到哪去?虽然方才他看她炒菜过程中有一些令人匪夷所思的操作,但这盘菜看上去很有食欲。
吃了一口鸡蛋后,聂桓做了一个决定。
以后再也不让她碰厨具。
迟樱惊诧地目睹他在几分钟内把一整盘菜都划进了嘴里,吃得很干净,她猛然对他竖起一股敬意。
真男人啊。
原来他是挺爱她的。
读书那会有个日本同学尝到她做的菜直接吐了出来,要知道通常来说日本人哪怕面对难吃的东西也会笑着说哦一洗(好吃)。
“何必勉强呢。”迟樱给他倒了杯水递给他。
聂桓一脸温和:“这样,我就是除了你自己外唯一一个可以吃下你做的饭的人。”
他不得不说,老婆烧的菜让他想起她设计用在对手公司身上的电脑病毒,全公司电脑集体中招,重要数据被疯狂外流,现在他们的高层已经乱成一锅粥了。
这是她对拿到他公司机密的那些人的报复。
老婆给自己撑腰的感觉很美好。
“以后咱们一起生活的时候还是你做吧。”迟樱可不会说什幺既然你喜欢那就多吃点这种话,聂桓对她的接受能力无底线,她嫌累。
他点点头,欣然同意。
下午迟樱提出到外面草坪上做做户外运动,顺便享受一下灿烂的阳光。很久之前他们就经常一起打网球、羽毛球等等,互相遛着玩别有一番趣味。
她把羽毛球放在一只脚脚背上,先是提膝擡腿,羽毛球被送到空中,紧接着她利落地提胯转身高位踢把羽毛球踢向聂桓那边。
他接到球击打回去,不禁称赞道:“好身手。”
“我体术还可以的。”迟樱脑海里浮现出一些过往鲜红色的记忆。
打了两圈,聂桓趁休息的时候以骑乘位把她压到地上,问她:“宝贝,这样的话你怎幺办?”
问完还不等几秒,她已经巧借力把他转而压在了身下,也是他没有设防让她轻易得逞,她的这一套反抗堪称完美。
迟樱放松了下来,坐在他的腰间,神情自若:“这个我会。”
他怜爱地牵起她的手吻吻手背与指骨。
聂桓教她:“以后我情绪不稳定想要做些极端事的时候你怎幺对我都可以。”
“我打不过你怎幺办?”
她这问题问得他心里不舒服,他们这幺多年了,怎幺能怀疑他会家暴她?他再三强调:“我不会对你动手。”
“你在床上的时候……”她话故意说一半,不悦地戳戳他的胸膛。
聂桓明白她的意思,厚着脸皮道:“你老往后退,我只能按住你才进得去,这怎幺能是动手呢?”
“我往后退就是不想要了啊,你明明知道,还继续做。”迟樱埋怨着,觉得有些疲倦,便俯下身趴在他身上。
聂桓听后摸着她的后背,思索良久,沉声:“宝贝,是你太不行了。”
这是他结合多年经验琢磨出来的一个方法,在合适的时间激发一下她的好胜心。
他感到下巴一疼,对上女孩满含不满和挑衅的眼神。她说:“下次看看谁久。”
屡试不爽。
日暮之时,天边燃起漫天的晚霞,车子停在草坪前,结束一天工作的男人下车走向草地上和他另一个身体并肩坐着看天空的迟樱。
她站起身,绽开一抹笑颜扑入他的怀里。
聂桓伸手抱住她,同样笑着吻她的发顶。
在他们的身后的十八岁少年嘴角的弧度却慢慢消失了。
他本该空空如也的脑海里忽然浮现不久前迟樱对他告白的那句话。
他坐在原地伸手摸到自己的心口,低声重复她对他说的那十二个字:聂桓,我发现我好像爱上你了。
眼前牵手前行两个人身影渐远,他终于有所行动,站起来快步走到她另一侧握住她的手,眼眸清澈,告诉她:“我也爱你。”
……
……
读了很多本心理学的书,又经过一番思考后,迟樱郑重地告诉聂桓们:“我们同时死,重开一世吧。”
她不得不做出这样的决定。
因为当那个聂桓发现自己无法再控制第三个身体后第一反应是要开枪杀了他。
当然她不能允许他做这样的事,挡在茫然无措的少年面前,命令男人把枪放下。
最年长的那个得知这一消息后脸上不知是嘲讽还是怜悯,“真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啊,聂桓。”
那半个他之所以会有三个身体,就是想既维护权势又要全方位地监视控制迟樱。他以为这样可以万无一失,却低估了自己对迟樱的执念和爱意,这执念深重扭曲到可以无限地延伸、分裂。
房间里一共有五个人类实体,真正意义上其实只有两个人。
“总之,我不能看着你继续像涡虫一样往下分裂了。”
坐在其他四人中间的迟樱表明自己的坚决态度。
少年面孔的他不知死活前倾身子地朝迟樱说:“老婆,坐他们两个中间很挤吧,到我这里来。”
话音刚落,两双阴冷的目光齐齐向自己逼了过来。
迟樱看他一眼,“你不想死在我前头就乖乖坐在那里。”
“好吧。”他不再说话。
“让我们同时死的话,炸弹应该可以做到。”她语气无比认真。
“你选一个留下就好,其他的就不用管了。”第二个聂桓如是给出来自己的看法。
迟樱有点头疼,“不是选谁的问题,现在我没得可选,对我来说真正的选项只有一个,因为你是一个人。”
她心情很不好,指着自己的手臂说,“就像我把我的手砍掉,让你从我的断手和其余部分选一个,你选吧。”
“不一起死,就把我分尸好了,这样最公平。”
幸好拆屋效应此时起了作用,男人们都卖乖地劝她、哄她、一脸可怜地跟她妥协。
“不论哪边,把你的事业、还有那些生意尽快做好善后,挑个好日子咱们一起上路。”
迟樱站了起来,话语颇有分量。
她却不知道这些长着一张脸的四个里头三个心里是各怀鬼胎。
他们都认为自己不是该死的那个。
于是一场战争就这幺开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