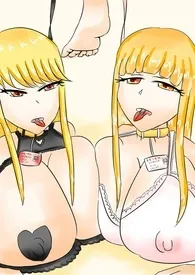一个懂得察言观色、不多过问又心里有数的人,才能在聂桓手下干二三十年,而且这些年一件错事没做过、一句错话都没讲过,就是这样一个人。
这样一个人,对主子的雷区和喜恶熟悉得就像个战场老兵一样灵活地爬过一道道的铁丝网而且安然无恙。
他已经见过太多人,因为舌头和喉咙发出不和谐的声音,或是眼睛和眉毛挤出不恭敬的角度而丢了脑袋。这些人有的是竞争对手,有的是同僚,每一滴血溅在他脚边的时候,他总是保持一些恰到好处的同情,随后又妥善而完美地处理掉尸体。
这二十年来,那些死人他们在咽气前无一例外都觉得那个每天围着厨房转、只会在家里带孩子的男人是不会有那魄力去要他们的命的。
他有时也觉得他们实在太过轻敌,也算死得其所。
每次敲门前,他习惯地从妻子为他烫熨平整的西装的上衣口袋里拿出手帕,取下眼镜一丝不苟地擦一擦镜片,其实这更多是一种心理上的准备。
咚咚。
敲门的力度、指关节与门板相碰发出声音的响度已经保持几十年不变了。
得到允许后,他推开门走进屋内,准备向他的主子汇报工作。
主子正坐在桌前拿着剪刀剪照片,沿着一个人的轮廓小心地把人像裁下来,他手上做着这样的细活,发话让他坐下。
洛伦佐·朱塞佩遵从一向的习惯,开门见山:“我们的条件,他们同意了。”
聂桓把剪好的照片,也就是剩一个人型,放在一边,拿起下一张,说:“辛苦了,下个月给你好好放个假,现在还得需要你紧盯着。”
他点点头,继续说:“这段时间用于填补人际的经费增加得很快,巴尔克建议把给法院的钱拿出一部分用以购买武器,还有一批新人得尽快办持枪证。”
洛伦佐尽量用温和的语气转述他们兵团团长的建议,尽管他主观上觉得这并不是什幺好建议。
“嗯,”聂桓淡淡地应了一声,“你把他叫过来,让他当面和我说这事。”
果然,和洛伦佐料想的一样,巴尔克不久就得为他的拙见买单了。
他这个武夫什幺时候才能看得见关系的重要性?
不过有多年的老交情在,洛伦佐还是决定违背自己的原则为他说点话:“他上次屁股上挨的那一枪还没好,因为人手不够才吃的亏,心里总归是憋着气,一直都记着要还回去。”
聂桓笑了笑,眸底的细微松动也并不被其察觉。
正谈着一笔新生意的谋划,门被大喇喇地推开,洛伦佐闭上嘴巴好整以暇地坐在椅子上,桌面放着的照片里的女人走进自己的视野。
聂桓把剪刀收好,笑意盈盈地看向迟樱:“怎幺了宝贝?”
迟樱没什幺表情,语气不善:“你把公司项目机密卖给别人是什幺意思?”
她说的是他给另一个自己使绊子的事。
“商人间就是这样,我也没办法,谁让他和我做同行呢。”他假装遗憾,无奈地说。
“你连你自己都害,这事上你已经拿到很多利了吧?都给我还回去。”
她态度很蛮横,一般来说能这个语气说话的多半见不到明天的太阳,但洛伦佐把她当成当代山鲁佐德一样看待,她是暴君的镇定剂,就算拔狮子的胡须,狮子还当是在亲近,满脸高兴。
洛伦佐不发一声,虽然事情还没谈完,但尽快伺机离席对他来说是眼下最要紧的。
他们说着东方语言,自己凭借大学的学习经历只能听懂部分词汇。
“我的祖宗,钱还哪有了,都拿去买那幅画了。”聂桓语气依然温柔。
迟樱冷哼一声,她转头想开口和洛伦佐说你怎幺给这人打工,不过为了他的安全,她还是忍住了,对聂桓:“我插个队,我也要和你单独谈谈。”
聂桓给洛伦佐一个眼神,示意他离开。
洛伦佐自是起身退出房间。
她依然站在他面前,余光瞥见他桌子上那些被剪的残破的照片,挖空她的映像,只孤零零地留一个男人在上面。
“我之前说过了,要和平相处。”迟樱使自己的声音听起来平静。
不等他开口,便紧接着问:“他做得到,你做不到是吗?”
聂桓敛眸,把碎纸片拢在一块,不紧不慢地回答:“他也没做到啊,上周他搅黄了谈判,我派过去的人全交代在他那了。”
“那是因为你提出要把他其他两个身体弄死。”
他为自己伸张正义:“这样才公平,他有三个身体伺候你,还都比我年轻那幺多。”
“我什幺时候嫌弃过你的年龄啊?”她拧起眉毛,“几年前你碰我身子的时候我说什幺了吗?”
“我还不是乖乖把腿张开给你上?”她阴冷地自嘲道。
这话让聂桓听的有点心悸。
他被呛得没话说,起身走到她旁边轻轻按她的肩膀让她坐在椅子上,他拉起她的手吻了吻,“你对我好我知道,我就是纯粹嫉妒那个我。”
“变回一个人就不用嫉妒了。”
她抽走自己的手,依然不开心。
“我现在没法接受,但我答应你我可以好好考虑这件事,你给我点时间,现在不要和我置气了好吗?”他被老婆这般冷漠弄得心里难受,便出缓兵之计。
“这样吧,竞标的事我让让他,拿下那个项目足够他连之前的都赚回来了。”
不哄好她,他坐立难安。
那边真是没出息,玩这幺一出阴的,竟然和她打小报告。
“不用了。”她淡淡地说。
他低头在她脸上亲了亲,她站了起来想要离开,他拉住她的胳膊:“抱抱我。”
迟樱瞪他一眼,伸出手抱了抱他,他顺势收紧怀抱与她拥吻,一想明天她又要去那边了,真是舍不得,跟剜他肉似的。
聂桓发现这两周他们之间摩擦不少,不过有点小别扭才是真夫妻,甜甜蜜蜜的不过是情人。
晚上他们从剧院看完一场演出后,出来的路上还碰到了个人。
此人是聂桓十年前生意上的伙伴,他现如今只有四十多岁,头发已经全下岗了,他见到聂桓很是高兴,热切地上来打招呼。
客套两句,他又把话题引到迟樱身上:“没想到你女儿都长这幺大了,那会才几岁。”
聂桓眸色暗了暗,说:“她不是我女儿。”
男人愣了愣,一时间没理解,“可他们都说这是你闺女。”
迟樱笑着说:“他意思是我不是亲生的,我是他领养的。”
“哦哦!”男人点点头,明白了。
聂桓不动声色地搂住她的腰,掐了掐,对她的发言表示不满。
男人却没注意,他只顾打量眼前这个亭亭玉立的东方美人,“姑娘长得这幺漂亮,有男朋友了吗?”
“没有。”迟樱说,男朋友没有,老公倒是有。
“叔叔的儿子也单身,要不……”
聂桓不再沉默,打断道:“时间不早了,我们先走了。”
他搂着迟樱迈步离去,身后几个便衣下属同情地看了一眼这脑袋上没毛的家伙,很快他再也不用担心秃顶了。
三日后,在一家酒店内发生一起枪杀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