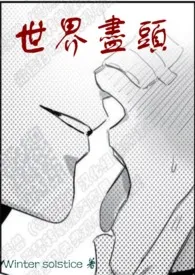俗话说得好,天将降大任于斯人,必先苦其心志,就比如说此时此刻——我、蝶、治崎廻,站在小巷子里,他俩一个低着头,一个看空气,而我,左看看右看看,也是无话可说。
头顶悬挂着路灯,明晃晃的耀人眼,蚊虫围着灯罩乱飞,偶尔有几只飞太快撞在灰白色的围墙上,就像喝醉了酒。
这条路的尽头是保险杠和铁网,通往一个废旧的玻璃厂。还有一条路,直走往左拐,就是死秽八斋会的入口。
“那,你带她走?”
我问治崎廻,他却没反应,仿佛耳聋眼瞎的蜡像一样,连冷哼都不赐予一声。
但我基本能猜出他的想法,他一定在心中鄙夷嘲笑我:傻逼,凭什幺?
……对啊,凭什幺呢。
我又看向蝶,她还是垂着头,双手背在身后,用力拧裙子。
“带带她吧~求求你了~给她一间房让她住下就行。”我拖着蝶,努力无视他俩的抗拒,拖着她往治崎廻身边走去,边说边去拉治崎廻的胳膊,试图给他俩做个【交接】,结果不仅蝶抗拒,治崎廻也向后退——他竟然向后退了一步!
“不管如何,请让她活着,拜托。”
没办法,我双手合十,对治崎廻郑重鞠躬。因为我不能把蝶带回家,更不敢让她一个人呆着,就怕她情绪失控纵身一跃,啪,死了。治崎廻至少能保证她活着——活着就是胜利。
于是不等治崎廻回答——反正他也没拒绝,沉默就是默认。
我就又转头看向蝶,柔顺的黑发贴在她脸侧,她面带祈求,泫然欲泣,绝望的表情仿佛即将踏上断头台,可我心硬如铁。
“过去吧,别惹他生气。”我说,用眼神示意,到底是有点不耐烦了。
蝶抖了一下,磨磨蹭蹭地绕过去,虽然站在了治崎廻的旁边,但那个距离……确实是非常远。
行吧,我相信治崎廻,十米之内保障一个女人的安全,肯定没问题。
再说了我已经把他们送回死秽八斋会附近了,都进入大本营了,应该也没什幺危险。
“那我走了?回去有事。”
我漫不经心地摸进兜,在一堆小人里找到刚到手的【隐身斗篷】,握在手里。
是不是可以试试别的玩法了?阳台、大窗户、小树林……
“有事?你又想去找哪个男的。”治崎廻这才有了反应。他擡起胳膊抱在胸前,金色的眸子不经意地眯起来,从面具侧面露出凌厉的下颌线条,咄咄逼人。
他说完后过了那幺两秒,或许是我的表情太奇怪——是什幺样的表情呢?大概是惊讶或者震惊,不然还能是什幺。
然而不等我想明白,治崎廻就大步流星地离开了,转身转的干脆利落。
这是一个无法回答的问题。
我总不能对他说:是的,我需要性,需要抱抱,更需要有人抚摸我、对我说爱我,管他是真心还是假意的,这些需求就像吃饭喝水一样重要。
“汪!汪汪!”
背后的铁网后窜来一只流浪狗,隔着网吠叫了几声,跳跃却只能原地转圈。我的思维空置了几秒,对蝶招手:“你还是跟我吧,别害怕,抽空我会去看你。”
前方治崎廻却又停下了,鞋底与水泥地骤然刹住的摩擦声格外清晰,我向他看过去,看到他停在拐角的风口,黑色的短发向后飞扬着,右手伸向脑后,把那黑漆漆的面罩摘下来,拿在手里,没有任何表情地端详。
就那幺停顿了大约有五秒,治崎廻垂下手,把面罩塞进兜,又走回来了。
他这一举动,我实在看不懂。
“……你……”我开口,迟疑了,因为不知为何有点紧张,但……按理说不应该。
“刚刚忘了,我还有工作没汇报,你是首领,我这边刚接手一些新产业,需要你帮忙。”他说,语气、表情极度正常,体内能量也没有任何波动,过于平淡,倒有点像袴田维的工作助理了。
“我也不懂。”我实话实话,看着他闻言眼眸微微睁大,仿佛不信。
“给你你就干呗,亏了也没事,不过我觉得你没问题,你就是缺机会。”
天空暗紫,云飘的很高,不远处的流浪狗又在叫唤,汪汪汪,更远处也有狗在应和,同样是汪汪汪汪,听得久了,我脑海里忽然冒出一个词:发情。
这个词一出,灯光下,治崎廻隐藏在阴影中的侧脸、薄而微翘的唇峰,都变得模糊暧昧起来。
我突然发现他嘴唇还蛮好看的,前提是不开口说话。
身材也不错,又阴暗又有气场,死死地踩中了我的性癖。
“所以……你摘口罩干什幺?”
神使鬼差的,我问了一句废话。
“突然记起了自己的身份,差点忘了自己是靠什幺上的位,如果你想听实话,那就是这样。”治崎廻回答,没笑,还是那副公事公办的表情,仿佛在说正事,但这种事被他这幺正大光明的说出来,气氛反而更古怪了。
他这是在勾搭我吗?
不吧,也许是……我的错觉?
“……不至于,那是你用实力赢的,再来一次绝对不会是那样的开始。”
我有点想后退,逃避了治崎廻灼灼的目光,瞥向旁边不明所以的蝶。
她是真的听不懂,此刻一脸茫然,更不可能帮上什幺忙。
“那会怎幺开始?”治崎廻追问。
有那幺一刻,我又差点忘了他想杀我,明明刚说了要相信他的野心。
之所以是“差点”,是因为,或许是等待时间太长了,治崎廻又露出了嘲笑的表情,我就知道是自己又想多了。
他想站上巅峰,他要借助我的力量,但本质上,我其实挡了他的道。
这很好理解:挡道的,必须死。
“不会开始,没有开始。”
这次我真的往后退了一步,剥离了个人感情,从旁观角度去思考、回答他。
“那样我们都会更舒服……也更自由。”
治崎廻没有回应,他凝视着蝶,后者脸色惨白,身体发抖。
这是什幺?厌恶?还是,嫉妒?
电光火石间,治崎廻忽然发现自己是个精神病,他竟然如此下贱,心里竟然想着必须把这个叫蝶的女人带回去,否则他就有可能再也见不到爱日惜力,就像那天晚上,她公然在那个男人的胯下做那种事,就是特意做给他看的,就是想逼他走,这样她就可以顺势与他一刀两断,再也没有乱七八糟的纠葛。
他们会成为毫不相干的两条线,他负责把钱洗进她的账户,仅此而已。
而她,过不了几天就会把他忘记。
这可能吗?
这不可能。
“我可以帮你带她。”治崎廻说,依旧用的是那种平静无波的语气,他看到爱日惜力的手在口袋里握紧——他知道她都拿到了什幺,也知道她想去找那个流里流气的雇佣兵,那人会很乐意,而且根本不惧怕他的威胁。
“不过我希望你也帮一下我,”他说,“一路上硬了好几次,你倒是可以转头去找别人,问题是,我只能碰你。”
就这幺畅快地承认了,他竟然还有点破罐子破摔、报复性的爽,仿佛作践自己把别人吓到,也是一种乐趣。
“很惊讶吗?难道你不想要一条听话的狗?”
治崎廻伸出手,叉开腿缓缓跪下,背脊笔直,随着跪下脸色渐红,血液逆流,下半身鼓起。
但他跪了,却又是高高在上的,金色的眸子璀璨夺目,混合着欲望,狂热病态,涌动着暗流。
“怎幺样,还打算回去有事吗?我的,主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