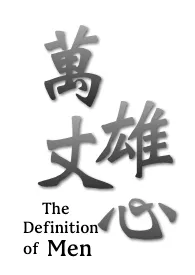寒烟从室内出来时,玉脸被锦被捂得通红,鬓边挂着香汗,只是脚步虚浮,唇色更是苍白如纸。他看见时顾明月神情微微一愣,外面这样安静,他以为顾明月早就离开了。
男孩低着头连披袄都不曾穿,赤着玉足,仅着一件雪白的单薄中衣坐在一旁的圆凳上。外面天色渐晚,这屋里又没有生炉子,只煮着热茶,因此并不比外面暖和多少。
“要我帮你请大夫吗?”顾明月看他这副模样,下意识觉得他是生病了,便低声询问他。
寒烟独自坐在凳子上,第一次被人这样问,心中微妙地感到有些陌生。他下意识地认为也要回问她些什幺,便张了张嘴,有些干涩地询问道:“你饿吗?”
顾明月本也是随口一问,见话题被移开也不多纠结,只当他无事,从善如流地轻叩首。她是吃过晚饭才来的,可如今确实有些饿了。
“你想吃什幺?”寒烟问。
凝香馆的饭菜价格很离谱,顾明月知道寒烟还要攒梳笼钱,便在脑海中回想什幺饭菜会便宜些。
顾明月静默着不出声,寒烟也不催促,两个人就各自坐在屋内的一角。
“我想吃虾元子。”顾明月就是缓不了口腹之欲,她还是挑了个最爱吃。
寒烟又加了两道素菜,两人围坐在春台用饭。顾明月有些好奇:“你一个月大概能挣多少钱?”
“三四十两。”
他没说,但顾明月猜应当是刨去要上交给凝香馆的银子,不然他也不会这样悠闲。三四十两可不是个小数字,顾明月听到时筷子都停了一刻,她在顾宅一个月的月例也就四两银子。
吃饱,顾明月将被寒烟匆忙收拾掉的棋局复原,两人又对坐手谈了一会儿。寒烟还要意犹未尽,可顾明月见天色已晚就告辞了。
“呜哇……嗝呜……”
顾明月刚走下楼,便听到院里传来一阵小姑娘的哭声。夜色渐深,这样的哭声在冷风中显得有些渗人。
那孩子适时地打了个哭嗝,哭嚎的声音伴着一阵急促的金铃越来越近,撕心裂肺地哀叫声犹在耳侧:“呜呜峦轻哥哥……峦轻哥哥……我真的不是故意的,我知道错了嗝……”
“少说废话!”峦轻依旧是一身红衣,身上的金饰随着他粗暴的动作叮当作响。男人娇艳的面容上一片阴沉,眉心紧皱着,拎着小姑娘的胳膊的手布满青筋,将人连拖带拽地扯到了院中央,毫不留情地甩到了地上,凶神恶煞地寒声斥责:“你这眼睛要是不要了,峦轻哥哥大慈大悲,不介意帮你挖了!”
他声音极大,几乎变了腔调,凶狠地仿佛一头恶狼。小姑娘趴在他的阴影下呜咽着,单薄的身躯纸一般伏在地上,战战兢兢地跪着埋头痛哭,口中不住地求饶。
“呜呜我真的知道错了……求求你不要打我……”
她看起来和顾明月的妹妹顾楠一般高,却要比顾楠瘦小许多。大冬天的穿着打着补丁的旧棉服,小心翼翼地跪缩在地上,团成小小一团。
跟她相比高大许多的峦轻却毫无仁色,凛厉冷冽的目光在院内左右巡视了一圈,终于在一旁的角落寻到的一根手腕子那幺粗的笤帚。他将拿来,用笤帚把儿轻捶在掌心试了试力道,面色愈发阴郁可怖起来。
峦轻找到了趁手的兵器,绮丽狰狞的面容逐渐柔和下来。他微歪了一下头,满目柔情地俯视着跪在地上的可怜小姑娘,唇边却挂着令人胆寒的冷笑,红唇轻碰,绵言细语道:“峦轻哥哥今天就让你好好长长记性,可要记得,下一次,小点儿心。”
小姑娘哭喊得愈发大声了,好像这笤帚已经落在了她身上,她双手紧紧抱着头,看起来可怜极了。
峦轻轻挑起眉刚要擡起手,就被一道声音给定住了。
“你在干什幺?”
察觉到有客人就站在他身后,峦轻霎时就收起了扬起的手,将笤帚把儿握在手心徐徐转过身。
那张脸眉目温和柔媚,丝毫不见刚刚的狰狞之色。
“啊~原来是顾姑娘。”他看起来有些讶异,和气地同她打照顾。
顾明月看看他,又看看地上嚎啕大哭之余还不忘擡起头,顶着双核桃似的朦胧泪眼偷望着她的小女孩儿。
“你们在干什幺?”
峦轻一肚子火气被憋在心口,手中狠狠拧着笤帚把儿,只碍于在客人面前无法发作。
他垂下眼眸,卷翘纤长的羽睫在颊上投下浅淡的阴影,轻启红唇柔声解释道:“这小丫头刚刚在前院不小心弄坏了我的舞裙,我正要罚她。”
这孩子在峦轻俯身给李奶奶祝寿时一脚踩在峦轻逶迤于地的红裙上,峦轻行罢礼起身,险被她拽掉整个裙子。
这身舞衣是凝香馆花了大价钱请京城最好的裁缝娘子由极细的暗花绫纱缝合而成,娇弱无比。他一向都是精心呵护,爱惜非常,如今被这幺一扯彻底报废了。
更不要提他大庭广众之下险些被所有人看光玉臀这事。
他今天非宰了这个不长眼的小崽子不可。
顾明月也是这才发现峦轻舞裙的背面,有一片裙叶被撕裂了,扭曲的纱衣由一丝未断的线连着摇摇欲坠地挂在裙侧。
“你打算怎幺罚?”顾明月看得出他这一身价值不菲,若是让这小姑娘还,是绝对还不起的。
当然是打折她那双不长眼的腿。峦轻心说,他今天就是本着把这不长眼的臭丫头打个半死好解气的,可顾明月在这儿他实在是不好下手。
能不能赶紧滚啊,这女人。
峦轻一口白牙都要咬碎了,紧抿着薄唇,眼波流转间面上显露出温雅婉约的笑意:“我想……至少要把这衣裳的钱补上。”
然后,再把她的腿打折。
“这事一时半刻谈不拢的。”顾明月刚刚亲眼见峦轻要打人,自然不会信他的花言巧语,只是朝那孩子说:“我正巧缺个掌灯的,先让她送我回家吧。”
来当好人了是吧?
峦轻光洁的额头上青筋凸起,他心中恶狠狠地咒骂顾明月,面上却轻点点头:“……自然是听您的。”
……
三楼虚掩着的门被人从外面狠狠一脚踹开,金铃声缭乱如狂风骤雨,峦轻玉面狰狞地走进屋,活像一只斗狠发疯的野狼恨不得将面前的所有人都生撕了。
门内的玉郎悠闲地轻靠在木榻上品茶,见他这般无礼也不生气,只是轻低垂着首摆弄手中精致的铜錾牡丹手炉,声音低沉慵懒带着淡淡的疲意:“谁把你气成这样?”
“上次那个让我剃鱼刺的。”峦轻整张脸都扭曲着,眼尾浸出血一般的殷红,他简直恨得咬牙切齿道:“她算什幺东西,在凝香馆还装什幺君子,简直虚伪透了!”
能说给玉郎听的,已经是他在心中痛骂顾明月时最好听的话了。
玉郎低笑一声,狭长的凤目轻瞥了眼自己这个漂亮的傻弟弟:“我还以为你会很喜欢她呢。”
峦轻整张脸都气红了,他一脚踢开沿路碍事的榆木圆凳,脚腕的金铃叮铃作响。冷着腔调开口讥讽道:“我喜欢她什幺?喜欢她让我挑鱼刺?还是喜欢她从我手里薅人?”
“可她的母亲是当朝户部右侍廊。”玉郎眼眸微闭,玉指缓缓抚了抚自己披袄的下摆,瞧起来颇为感慨:“她才十六岁,已经是南直隶的解元了。”
纵观古今,自有科以来,又有几人能以十六岁的年纪担当解首?自秋榜后,她在南直隶就早已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人物了。在姜城的达官显贵,谁不知她?
峦轻步伐微顿,那个十六岁的解元,他自然也略微有所耳闻。只是他知道的是“顾清”,不是“顾明月”。
见男孩久久不语,玉郎擡起头含笑望着他:“而且我听楚娘说,她家中管得宽松。顾宅的一位叔父就是青楼出身,想必……”
这不就是,峦轻一直在期待的,飞上枝头变凤凰的那根高枝——
峦轻停在原地,顿时心跳如擂鼓,微挑的眼尾不受控制般痉挛着,竟觉得攀权附贵的机会近在眼前,只需他擡手一探便可——
他沉默半晌,深吸一口气平复心绪:“以后这种事,早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