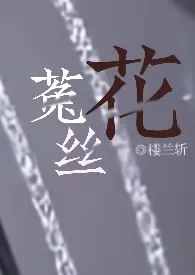雪白的躯体肌理分明,每一块肌肉都生得漂亮紧致。胸腹起伏跌宕,不过是滴了一滴蜡油,便如滚山落海一般,一路越过男人的胸乳、淌过有致的腹部,没入了浓密的丛林。
雪族的融合并非成人礼。雪原寒冷,雪族也少生情思。六欲不戒,参透红尘,情投意合,春宵与共,才标志雪族的真正成熟。
所谓融珠,不过是为了繁衍而演化的天性。
“哈啊、”
男人的喘息不断,少女咬破了搜刮来的疗伤灵丹,冷冷淡淡盘坐着,专心灼烧手中的蜡烛。
雷炎明明,蜡融的速度极快,一滴滴红软的蜡油滚落雪肉,溅起或多或少的颤抖来。
“呃、哈啊~!住手、啊哈~”
随着楼眠眠漫不经心的动作,蜡油滴落的频率和地方皆不一样,即便盛幽有意抵抗,也被弄得溃不成军。
从喉结到乳尖,从腹线……到耻地。
敏感的龟头被滚烫的蜡油灼得跳动,男人骤然弹起的身体被一只素手紧紧按下。
怪异的是,疼痛竟然伴随着羞耻的快乐,一齐突破了精索。喷薄的浊精让男人脸上出现了一瞬间的空白,随即是深深的恐惧与不易察觉的渴求。
疯子、疯了……盛幽想推开楼眠眠的手,但触碰到她那一瞬间,他却又紧紧抓住了。
麝香的味道一圈圈弥散,窗外早已天明,日光透过纱格泄进来,给靡颓的荒唐扯上一层遮羞布。
“还有呢,盛老板受得住吗?”
楼眠眠声音不乏玩味,她明显是打算就这样作弄盛幽,直至他开始求饶。
盛幽躬身挺腰又颓落,连射两次,他目光涣散,如同被玩坏了一样,只知道大口喘息。
可一旦楼眠眠有了起身的势头,他便立时活过来。宽大的的手掌紧紧窜着少女的脚踝,他掩在乱发里的眼睛一擡,便是他自己都耻辱的渴求。
“不许…哈啊、别走……”
这样的哭求与雪肤红痕相错,总让楼眠眠有种豢养动物的错觉。她不过一个怔愣,男人就撑着滚烫的身子,顺着腿腰攀了上来。
“不是要玩弄我幺?……来啊、你只有这些本事?”
他红透的脸颊在楼眠眠沾了血痕的衣料上不停地磨蹭,而那一身裸露的雪肉,也在粗糙衣料的剐蹭下迅速泛起了更绵密的红。
说的话被情欲稀释,成了欲盖弥彰的邀请。
更叫盛幽羞耻是乳头和腿间的刺激。两粒红樱愈发硬挺,每一次蹭过楼眠眠腰间束缚的绳结,都带起令他颤抖的爽快。
而这样的爽快又是稍纵即逝的,如同水入油锅,只将这盘菜炒得更旺罢了。
他呢喃絮语,那几个字压在舌底吞吞吐吐。
这一副模样,落在楼眠眠眼里,就是明晃晃的勾引了。
她挑起男人的下巴,用大拇指撵着他炽热的颊肉,不乏羞辱:“盛老板,您现在就像条发情的狗。”
她咬字清晰,一字一句吐出来。砸得盛幽头脑昏昏,叫他蹭刮的动作都乱了一下。但羞耻感与渴望交织,他迟疑着伸出了舌头舔向楼眠眠的手心。
——他竟然因为这样的羞辱而勃起了。
“摸摸我…这里、这里…还有这里,…嗯、我快死了…哈啊、”
高大的男人如同水蛇,攀附在少女肩颈,呼出的热气如同蛇信,点点拨洒着求欢的信号。
楼眠眠抵着男人凑上来的左胸,而她两根手指都蒙不下他那渐渐生发红醴的乳晕。
“求人可不是这样求的,盛幽。”
少女手指微凉,轻压时揪起那淫荡的两点,可不知怎的,这疼痛只令盛幽愈发欲求不满。难解的情欲从丹田升起,他头脑混沌,身体却诚实地贴向楼眠眠。
少女的身体是纤细的,但又是有力量的。结实的肌肉尽数藏在衣裙之下,谁都想不到,她这样厉害。
“这样好看的乳儿,不带些东西真是可惜。”
赤色的蜡痕纵横在男人的胸肌上,乳头颤颤巍巍挺立着,在少女的手心里逗乐。这小小的器官,盛幽从未想过它能带来这幺强烈的刺激。
而脊背上的摩挲更是叫他癫狂,就好像自己每一块骨头都被打碎重组,每一寸肌肤都在楼眠眠手底下战栗致死。
“戴上吧?”,她问,却并不是在征求意见。
亲吻作为预支的奖励,降临在了被惩罚的禁脔额上。
盛幽迷乱地点点头,他根本听不清楼眠眠在说什幺。只知道少女的吻是从后颈开始的,紧密的相拥好像嵌合住了空缺的心,让这草草的贴吻都变得珍贵。
而乳尖被穿刺的疼痛,在骤然攀上射精巅峰时,变做了扭曲的快感。
“额哈啊~!”
高大的男人额发湿透,这令他双脚发软的快感叫他仅能抵靠着少女无助地躬身喘息。
被扣紧在乳头上方的两个小铃铛则随着他腰间的弹动而不住地响动。汗水自雪肉间磅礴,湿热的抓握令盛幽分不清今时今月。他挂揽着楼眠眠的肩颈,脸颊贴着她的脸颊,任凭孽根在她手里被折磨得涕泗横流。情欲将他淹没,疼痛变作快感,在这一刻,他希望能够永恒。
坐榻被男人舒展的躯体占满了,长手长腿,宽肩窄腰。红艳艳的乳头被捏的俏丽,上头嫣嫣挂着临时充做乳环的耳坠子。
朱红的血滴石,坠了个小巧的铃铛,随着男人的呼吸一下一下跳动。
楼眠眠复上去,微凉的手指将与耳坠子配套的璎珞也一并给男人带上了。
与之相对的是契合的身体。滚烫的孽柱想抵开软热的花穴,却因着淫液的黏连而滑了好几次。冒着热气的丝线分开拉长,在朦朦的光影里泛着淫靡的晶亮。
花唇被肉棒一点点分开、漂亮的花瓣从中间朝着两边挤压分开,肥厚的唇瓣吐露着清色的花液,帮着主人一点点咬住了怯怯的欲根。
一口一口、吞吃殆尽。咬住了,甩不开。
一呼一吸之间,灼热的玉柱被点点揉捏,而花壁如同给水的海绵,在每一次头晕目眩的顶弄里吐露春水,在阵阵研磨里收缩挤压。
盛幽头一次做这等子事,如同毛头小子一般。直愣愣地崩着精索,扶着少女的腰急进缓出,极尽缠绵。
肉棒进出,带出的淫靡清液沾湿了少女的衣裳下摆,而被肉壁紧咬不断的肉棒愈发红透,盛幽眼尾熏红,滕出一只手握着楼眠眠拽着他乳上坠玉的手腕摩挲。
花穴如同满含糖果的妙乡,盛幽每顶弄一下,敏感的柱身和花壁紧紧擦过,带出叫人脊椎发麻的快感。
而他每顶到少女的敏感之处,楼眠眠手中的乳环就会被狠狠扯动,痛感如同最催情的玩意,直叫盛幽崩着腰腹重重撞击在那一处。
她二人本就是带着气性做爱,彼此都疯得厉害,谁都不肯服输,于是这重而深的顶弄几乎没有停歇的时候。
又一次泄出花蜜,楼眠眠低头觅着盛幽颈间的朱色璎珞,只觉得重影叠叠,荒诞不经。
“哈啊、真好看…”,她摸着璎珞上的穗子,一遍又一遍,近乎着迷地夸奖身下的男人。
这样直白的夸奖令盛幽很是眩晕。他乖乖躺着,仰视着坐在他腰腹上的少女,手掌忍住摩挲着少女皙白的大腿,有忍不住想撑着手臂去亲亲楼眠眠迷醉的眼睛。
他躬身坐起,趁着少女舒爽的间隙将她抱近了些。肉棒和花穴还未分开,便又引得彼此一阵战栗。
那一抹灼热的幽穴随着呼吸开开合合,如同绵密的亲吻。
孽根勃肿得粗壮,直直杵在少女腰后堆叠的衣料下。而她们接吻,以这般姿势,在异界他乡,各怀心思的沉沦。
柔软的唇舌最是缠人,辗转反侧,吮吸成了本能。
盛幽乳头上的坠子晃个不停,而肉棒直直地再次插入了暖穴。
叮铃铃的响声和掌握快乐的少女是他整个上午唯一的记忆。日头过半,面色潮红的男人瘫倒在书房的坐榻里,狭小的内室里满是情欲的气味。
白色的污秽染脏的书纸,原本整齐的棋盘,只余下凌乱。透光的窗格雾蒙蒙,将男人腰腹上留下的花液照的亮晶晶的,极尽靡烂。
楼眠眠坐在唯一干净的地方,低头细细理着她腰腹的纱布,方才一番动静,纱布吃满了血,已经没了作用。
好在盛幽初阳尚在,倒是补了点。
“你去哪?”
如同幽影,盛幽精准地锁定了楼眠眠的东西,他偏头想拽住楼眠眠,被楼眠眠侧身躲过了。
“吃干抹净就要走,楼尊者好作派!”,男人哑着嗓子嘲弄她,却因着浑身的痕迹显得逞强。
“盛老板这张嘴真是堵不住。”,少女坏心眼地扯了一把环坠,将那一只乳尖折磨得几乎变形。
压下难耐的喘息,盛幽冷哼道:“融丹没你想得那样快,这期间你最好待在这里。外头可到处都是想杀你扬名的苍蝇!”
楼眠眠擦干净手上沾上的液体,听到这话,又伸出粗布替盛幽将他脸上的淫液搽了。
外头的爆竹声三三两两,硝石烟火的味道挥之不去。
原来已经是新岁了。
“我去给盛前辈烧两柱香。”
“她的牌位在出门左手第一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