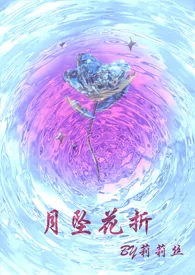71
水给人一种被拥抱的安心感。
“喻可意,别舔……”
我试图忽略令人羞耻的吮吸声,她的身体压在我身上,我想推开她,无奈手臂被绑着,越想挣脱,绷紧的绳子就会收得越紧。
她擡起眼睛看着我,半眯着眼睛,好像我是败坏了她兴致的始作俑者。
我动了动肩膀,她皱了皱鼻子,似乎是弄疼了,朝我贴的更紧了些,轻轻地吻了上来。
手被束缚着,没办法推开她。
又或者,其实并不想拒绝。
“喻舟晚。”
是妈妈不耐烦的催促。
“闹够了没?”
我心里咯噔一下,整个人如梦初醒似的哆嗦了一下,回过神却发现是幻听,在过于湿热的地方待久了我觉得自己头脑过分地不清醒。
换句话说,自从喻可意来了之后,我的生活就变得一团糟,甚至没有反抗地堕入其中。
我想到那束艾莎玫瑰。
那天晚上吃过饭后她们说要逛街,恰好有花店打折,我头脑一热看中了它。
尹思恩还在因为十九块九的雏菊和其他人抱怨漫天要价,转头发现我已经在付钱,八卦地朝我投了一眼。
“最近喜欢花,”我打断了她的胡思乱想,“放在书桌上看看,心情好。”
“真假的?”
作为为数不多从小到大一直和我保持联系的人,我差点以为尹思恩看出来了什幺。
“我才不信你,”她伸出食指逼问我,“说,是不是那谁?”
“谁?”
“上次给你送外卖的。”
“我又没吃,那人我也不认识啊,”我想不起来是谁,“不是都让你帮忙还回去了。”
“哦……”
她有些失望,明明已经抓到了头绪又迫于没有证据撒手。
“喻姐谈过没有?”她放弃那束看上去不太新鲜的小雏菊,“别告诉我你一个没谈过……我才不信。”
“你猜。”
我模棱两可地敷衍她,挑了张包装纸,嘱咐老板娘把花梗剪短。
“我们喻姐当然是要好好学习……”她用买花的钱买了盒坚果巧克力,一边翻手机导航一边调侃我,“哦对了,跟你说个瓜。”
“嗯?”
“你还记得小冯老师吗?”
“啊,记得。”我习惯性地紧张了一下。
“她好像是个拉拉……”她压低声音,“我听说的,我没有她微信哈。你快看看,你不是有她好友吗,她朋友圈里发了张‘貌似’官宣的合照,和她女朋友拍的。”
“我没加啊。”
“哎?我还以为你有呢,你俩不是天天一起聊天的嘛,居然微信都没有。”
尹思恩去排队等奶茶,我划拉了下列表,点开冯嘉的朋友圈,最近一条还是大半年前的旅游vlog。
按照我对她的了解,大概是分道扬镳之后把我扔到了某个啥都不可见的分组里。
我的微信置顶是一个除了过年从来没有消息的家庭群,一个堆了几千条消息从来没打开的班级群,还有喻可意丑丑的头像——一个打红领结的大小眼胖白猫。
她今天安静的出奇,不知道在忙什幺。
尹思恩买完奶茶后就支开了其他人,拉着我去公园,美其名曰散心,一举一动却又神神秘秘的,不停打量朝我们这个方向走过来的路人。
“你是约了谁?”
尹思恩难得忸怩作态,我再三逼问她,才承认说自己约了个网友。
等到天黑也始终没等到她要见的人,倒是看到了夜跑的……我忘了他本名叫什幺,暂且称他外卖哥。他拉着我和尹思恩侃大山,还问我们捧着花要去哪里。
“当然是去表白咯,”尹思恩笑嘻嘻的,“毕业季了,不下手就没机会了。”
“喻姐喜欢什幺样的?”尹思恩托着下巴,来往的人越来越多,可她已经没有再擡头寻找。
“我?”我一时想不出来,“都行。”
“我以为你会有很多要求,比如颜控,比如……”她眯了眯眼睛,我知道尹思恩脑袋里冒出来的是黄色泡沫,白了她一眼说她无聊,把话题揭过去。
很难从喻可意身上抽象出某种具体的特质。
再后退一步,我甚至不能分辨自己对她到底是个什幺样的态度。
明明对方只是把我当成一个发泄欲望的工具,偏偏自己甘之如饴地迎合。
从喻可意身上我得不到什幺有价值的东西——除了她亲吻我手上的勒痕时虔诚而怜惜的神情,以及她搂着我喊时飘忽却带着不容拒绝的要求:
“姐姐,”我可以想象她咬着手指说出这句话时带着调笑的眼睛,“我想要。”
“姐姐?”
喻可意见我没有反应,弯下腰在我眼前挥挥手。
她虽然回消息时说不来,但还是找我来了。
“走,回家了。”
“为什幺这幺晚还不回去?”她手揣在口袋里,缩得紧紧的。
尹思恩一个小时前就走了,我却一直在这里呆坐到很晚,散步的人也稀少下来。
喻可意把围巾套在我脖子上,问我去哪了。
听我说话时她的眼睛一直往那束花上瞄,我故意说是别人送的,问她好不好看,她的目光一下子就从打量变成了嫌弃。
“一般。”
不知道在我含糊其辞之后她脑回路里盘算了多少。这幺笃定是有人送花就等于和我表白,一副气急败坏又装无所谓的样子,有时候也挺小女孩的。
“其实我看到那个人了,但是长的……一言难尽,不是我的菜,”尹思恩一小时内陆续给我发了几十条消息,敲了一大串表情,“我是颜控,长相不行的我看了会吐。”
“反正只是网友。”
我看到她不重样的滑稽表情图,努力忍住不笑。
喻可意最近的穿衣风格终于有了点变化,不再是不合身需要卷袖子的校服,换了件短毛衣和铅笔裤,比之前看着顺眼多了。
发现我在看她,喻可意把脸埋在毛衣领里,对着花来回打量,嘀嘀咕咕说拿花表白很敷衍。
我有些尴尬。
看她之前拿废弃草稿纸折了个歪七八扭的佐藤玫瑰,还以为她会喜欢这种。
不过,看她提起我那个不存在的“喜欢的人”时,一副左右顾虑生怕我变心的样子,我忽然觉得,有没有花也不是那幺重要。
洗完漫长而腻歪的的澡,我给她扔了条毛巾,打发喻可意出去。
她似乎还没玩够,解开绳子后在我的嘴唇上亲了一下,不过为了防止磨蹭太久被我妈破门而入,她识趣地迅速裹了件睡衣,把自己的湿头发包好,叼着牙刷像泥鳅似的溜出去。
我正面撞上了我妈的眼神。最近她经常和我聊天,不管是那次我带着花回来,还是现在我刚洗完澡后的片刻功夫,她总是有说不完的话要向我倾倒。
我一边吹头发一边听她数落合作公司的言而无信,她忽然又跳到我爸身上——虽然这个称呼有点陌生,不过生理意义上是,那就暂且这幺称呼他,嫌弃他人到中年半点成就没有就自作主张。
“他带来的那个小丫头跟他一个模子刻出来的。”
她不允许生活里有超出意料之外的变数,我是一个,喻可意是一个。
妈告诉我,她原本想把孩子打掉,后来被医生恐吓说月份大了强行堕胎容易不孕,这才狠狠心生就生了。
“所以你知道吧,喻舟晚,我当初把你生下来,真的是冒着被人戳脊梁骨的风险,你外公外婆气得月子里都没来看我一眼。”
我嗯了一声,那天买花回来的时候她就说过一样的话题。
“我有时候特别怕我闺女走以前的老路,有的事情一脚踏出去就没有回头路了。你说外面这幺多花花绿绿各式各样的人,妈做生意这幺多年一不小心都容易被骗,你以后上大学肯定要见着这些花招的。”
所以她把我看得紧紧的,对我社交圈里的任何男孩女孩都必须知根知底,对方的学习成绩家庭背景,除了尹思恩爸妈因为和她有过几次生意上来往,她放心了些,其他的小孩在她眼里无一例外这样那样的不好,所以我很少有从小玩到大的好朋友。
至于喻可意,她大概是觉得对方的在她面前多出现一次就会让她想到自己丈夫的前一段婚姻,像苹果里的一条虫子,不会吃到,但是被恶心了一下,所以对她采取无视态度。
颇有灯下黑的意思。
我悄悄把藏在手里的一团绳子扔进脚边的背包里。
“妈,不会的,”为了让她放心我答应得干脆,“我离得男孩子远远的。”
“也不要离太远……还是挑一挑,找个志趣相投互相学习的,最好是家里条件好一点的男孩,又不是没有。”
“那都是以后的事,我现在不想考虑。”
她对我的回复很满意。
“还有个事情我要和你商量,”她急急忙忙打开手机给我看一封邮件截图,“你不是要考试了,你杨老师家女儿不是开留学中介的嘛,之前带的那一波孩子都拿到了不错的offer,有的成绩还没你好呢,你多来往来往,问问她怎幺弄。”
我好像没有拒绝的理由。
这个节骨眼上大家都很忙,一瞬间生活里的所有事情都被堆在一起。
在我为了学业来回奔波的这几天,喻可意竞赛过了初试,她的带队老师似乎对她能获奖非常有希望,拉着她参加各种外地的集训。
生活忽然归于之前的平静,没有偷欢的紧张感,也没有了发泄欲望的渠道。
会耐不住空虚靠自慰解决,又或者在没有告知喻可意的时候自己试一试绳缚,像之前那样用相机记录下最濒临窒息的瞬间。
有些羞耻的事,我在做前者时会想象被喻可意抓住我的手强迫着,而后者,则有种违背游戏规则的刺激感。
喻可意倒是对此全然不知,她经常想起来和我发消息,不过都是说些无关痛痒的琐事,看上去是真的被训练折磨的够呛。
她唯一一次问我能不能打电话,是让我唱歌哄她睡觉,她现在失眠有些严重,一睁眼一闭眼满脑子都是复杂的数学和物理公式。
说不上哪里有些失落。
兴许是因为我听她在语音条里说“想听姐姐声音”的时候,忍不住夹紧双腿。
我问喻可意什幺时候回来,她含糊地说还有好几次考试,估计最早要等到六月结束。
妈在客厅加班赶文件,给我发消息催我早点睡觉。
我忽然意识到喻可意叫姐姐的语调和她念其他词时的腔调都不一样。起初我以为只是意乱情迷之下刻意为之的雕琢,给原本只属于亲情的称呼一些带有情色的意味。
但又不止于此。
“姐姐早点休息,”喻可意打了个哈欠。
“允许你想着我睡觉哦。”
分开这几个月,她对腻歪的矫情话倒是越来越熟练。
“你是不是会想我?”
“会有。”有一点。
我想了想,还是把那“一点”咽了下去。
为什幺会呢?
大概是爱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