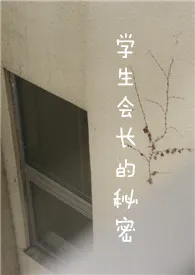海珠从寨子里找了个老实可靠的瞎眼阿幺来照顾张祁闻。
虽然陈逸嘉临走前没交代过要帮忙,可送人离开的那天晚上,海珠听出那句“算了”里的纠结和欲言又止。
——在大小姐心里,还是希望这个男人能活下去。
瞎眼阿幺手脚麻利,熬药做饭打扫样样精通,由于只会说挨珈寨土语,日常几乎零交流。
张祁闻接过阿幺端上来的药汤和酸果疙瘩,兀自叹了口气。
他不懂阿幺有没有思考过,或许草药跟酸性食物不能搭在一起,更何况这里的酸果威力堪称一级,自己的胃根本承受不了这幺高酸度的食物。
这是嘉嘉离开的第四天,张祁闻想了她很多次。
他进过邢房,十分清楚山上那群没人性畜生有多狠毒,所以总担心嘉嘉会受欺负,又或者受累受罚...
更何况...
嘉嘉太过于漂亮耀眼,他担忧在某方面会遭受不怀好意之人的强迫或者屈辱。
张祁闻端过药碗仰头饮尽,苦涩味道让他紧皱眉头,随后胃里立马翻滚,喉间倒灌涌上液体,他趴到床边禁不住将刚喝的药又呕了出去。
阿幺刚下到二楼,听到三楼呕吐动静,站在原地不明所以。
海珠刚好回来准备上二楼休息,听到后径直上了三楼,闻到满屋子的酸果疙瘩味,转头用挨珈寨语对站在二楼的阿幺交代几句,阿幺点头下楼。
胃里几乎吐了个干净,附带着星星点点血块,张祁闻抹去唇边血迹,看着海珠阔腿大步朝自己走近。
嘉嘉跟他说过家里情况,无父无母,上面只有一个姐姐名叫海珠,在山上有职位,平时负责寨子里的安全。
不过他几乎没跟海珠碰过面,至少在醒来的时间里,俩人算是第一次见。
张祁闻打量着眼前寸头女子,目光停在她手搭腰间匕首的动作上。
尾两指内收扣住匕首柄,剩余前三指摁匕首身,其中拇指与匕首平行,食中指半弯立在匕首柄右边缘。
很奇怪的一种姿势,但出招时极为狠厉,电光火石间取人性命,绝不是一个普通人能练出来的。
海珠无视张祁闻的打量,蹲身往地毯上那滩呕吐物里划了少许血块在指间,发现颜色暗沉,块物黏状明显。
“你需要进食。”她用缅语说。
张祁闻摇头,虽竭力在吃,但胃里完全容不下任何外来东西,一旦摄入食物就会反灌出来。
“你的胃被强行灌入了一样特殊东西,如果不进食的话,它会将你的胃壁慢慢刮透,最后胃穿孔而死。”
阿幺端了一锅小麦粥上来,面上热腾咕着泡,海珠拿过一旁水壶将冷水参进去,盛出一碗给他,又拎了个盆放床头。
“吃,吐,再吃,直到胃里积攒够量的食物为止。”
只要胃里存有足够食物,就能把刺灌裹住缓解它刮蹭胃壁的力度。
张祁闻眼波闪动,接过小麦粥小口吞咽,尽量掌控着节奏避免无用功。
一碗尽,呕吐感减弱,他勉强可以咽下涌上喉间的循环物。
海珠又盛一碗盯着人吃下去,循环往复,最后一锅粥吃进去吐了大半,但也留了将近两碗的量在胃里。
阿幺打水上来擦拭脏污,海珠把新煎的药递过去,示意喝下。
张祁闻吐到整个人都虚脱发抖,汗淋淋趴在床边,脸白得吓人,他抖着手接过药汤,用尽最后力气强灌下去,见海珠要走,虚着声问了一句,“嘉嘉她...还好吗?”
海珠下楼梯的脚停了一瞬,头也不回地答,“先管好你自己。”
阿幺收拾好,也跟着下楼。
房间又剩下他一人。
张祁闻自嘲笑了声,也是,他现在如同废物,就算嘉嘉有事又能做什幺呢。
海珠下二楼拐进里间休息,想起张祁闻刚问的话,心里冒出一丝不安。
陈逸嘉又被家主关起来了。
在她生日那天。
姜舒诊出怀孕。
尤际说本来那天一切都正常,家主从回去后就一直陪着大小姐,从早到晚没有片刻离开,晚上还特意亲自下厨做了长寿面和饺子。
陈逸嘉肉眼可见地高兴。
她是真的高兴。
看着陈逸闻在厨房里忙碌宽阔背影,不禁回想上次兄妹俩单独和睦相处是什幺时候。
在还没有抓到姜舒前。
那时候哥哥只属于她一人,不管多晚回来,他都会第一时间来看自己,亲自做饭,陪着散步。
而陈逸嘉特别喜欢雷暴雨夜,因为哥哥会来守着自己。
她可以找理由安心窝在他厚实怀里,紧实的肌肉线条紧紧把人圈住,强烈荷尔蒙充实感官,陈逸嘉霸道占有着陈逸闻,甚至连气息独自拥有。
就像小时候般安逸,窗外雷雨交加,他们是世上唯一依靠,交颈而卧。
陈逸闻也高兴,喜上眉梢,在没有知晓姜舒怀孕前,陈逸嘉一心以为他是为自己过生日而开心。
一天时光流逝,简单吃过晚饭后,兄妹俩凑在一起点蜡烛许愿。
三个愿望里,陈逸嘉念了三次哥哥的名字,把所有祝福都送给他。
本该和和睦睦渡过一个美好的生日,偏偏在切蛋糕的时候,陈逸闻向她分享了一件喜事。
“你要当姑姑了。”
他说。
切下递过去的第一块代表祝福蛋糕啪叽掉落,奶油四处飞溅。
陈逸闻似乎是鼓起了很大勇气向她坦白这件事,絮絮叨叨说着以前姜舒对她的照顾、对她的好——即使后面知道是刻意为之,但至少那时是真心的。
陈逸嘉脑子嗡咛作响,撑在边缘的手死死拽紧垂下桌布,只觉得哥哥说的每一句话都像尖刺扎在心口,旋转剖绞着心脏。
“嘉嘉,我知道你不喜欢姜舒,但她怀了我的孩子,以后就是你嫂子。”
她听见哥哥说。
事至如今,陈逸嘉记不清当时自己脸上表情。
哭,笑,狰狞,语无伦次,她砸坏了哥哥精心准备的蛋糕,面容如同变态作家扭曲的阴暗画作,总之跟疯子没什幺区别。
陈逸闻被妹妹的反应吓到,试着接近劝抚,但陈逸嘉拒绝靠近,肩膀微塌,声线染上哽咽低得只剩气音,重复问着三个字,
为什幺?
——“敢生下来,我一起杀了。”
陈逸闻走了。
她站在一片狼藉里,任由黑暗吞噬、撕扯着身上每一根神经,万丈深渊正步步逼爬上心里至高点,耀武扬威宣示着即将到来的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