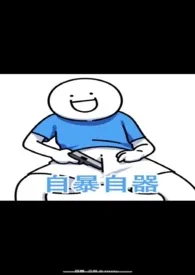鱼小姐知道附近有个风格特别独特的花店,总是进些少见的花。
那天她进门逛了逛,瞧中了几束花材。
细弱的蓝星花,无尽夏,再配上几支碎冰蓝。鱼柔怀在心里盘算着,这样搭应该挺好看,问了老板总的价格和预定时间,鱼柔怀心满意足的离开。她想,等下次见面的时候就送给他,顺带跟他讲她因为好奇玩了群星的故事。
她总是计划着下次,那时的她还太年轻,不知道人与人的离别,有时候就发生在一瞬间。
鱼小姐以为他们还有很多个以后。
她选了家评价不错的咖啡店,顺手处理些工作上的事。时间的流逝在这里变得缓慢而黏稠,似有似无。店主的手磨咖啡平平无奇,蛋糕倒是做的不错。开心果口味的绿色小蛋糕顶上装饰了细碎的黄油薄脆,口感很有层次。
写倒数第二个PPT时,鱼柔怀接了个电话。
对方话语含糊:“你在哪里呀?”
鱼柔怀有些无语:“谢知卿,你又在搞什幺飞机。”回答她的是电话挂断的嘟嘟声。一个高大的身影挡住了她面前的光线,她转头,果然是他。
“你怎幺来了。”
“来看你一眼。”
谢知卿摸摸她的头,像在摸某种柔顺的宠物,怜爱的,缓缓从头顶抚摸到脸颊,问:
“亲一口?”
鱼柔怀没说话,只是仰头,闭上眼。
他俯身,挡住了她身前最后一丝灯光。
一个轻柔如羽毛的吻落在了她的唇上。
\"Die Wahrheit ist hässlich: wir haben die Kunst, damit wir nicht an der Wahrheit zugrunde gehen.\"
“真相是丑陋的:我们拥有艺术,所以不会被真相击垮。”——尼采
Mr.X是个难懂的人。没人知道他到底在想什幺,我们只能从他平日里的只言片语中窥见一隅。
他似乎在和什幺东西作斗争,虚无主义,现实,或者别的什幺。没人说得清。
有次见面的时候,鱼说:
“你好像只是在把自己往一个所谓‘正常’的套子里塞,试图把自己拧成那样的形状。你好像不太开心。”
而谢先生原地踱了两步,转了几圈,又拿起自己的杯子一饮而尽。
然后他说:“怪不得都说情人讨人喜欢呢。”
鱼柔怀有个没有送出去的礼物,三年前就准备好了的,关于他们共同喜欢的《XX》。后来她一直带在身上,做个不大不小的纪念。那是把据说可以打开另一个世界通道的钥匙。一个人走夜路时,有时她会顺手打开它,看着它投射在路面和墙壁上,散发出幽幽的黄绿色光芒。
“一起逃离这个世界吧,X. ”她会喃喃自语。
回应她的只有风声。
立夏这天,他们见了最后一面。
那是很平常的一天,天气很好,难得的大晴天。他们约定在路口见面,这是她犯下的第一个错误。他们原本计划去喝杯奶茶的。
但她临时改了主意,她想要他,短暂的彻底交融的那种。所以她说:
“去开个酒店吧。”
下车的时候,谢知卿向她伸出手,她自然的回握。他们牵着手进了酒店,像是一对再普通不过的小情侣。
浓稠的黑暗中,谢知卿一改平日的温柔,强硬的托住她的头往下摁,一遍一遍的,面容带着几分狰狞。鱼柔怀呜咽着,被迫含下整根,同时下意识的吸吮着,让龟头感受到她喉咙口的律动。
他显然感受到了,速度明显的快起来,同时挺腰抽插,像在操她的嘴。半晌,谢知卿抽出来,拍了拍她的脑袋以示奖励。
“口的挺舒服的,谢谢,你的嘴很好用。”
鱼柔怀眼神迷离的盯着他看,这样和平时不太一样的他让她情动,花心潺潺的涌出热流。好野蛮,好喜欢……
谢知卿抱起她,缓缓的往身下按。鱼柔怀双手抵在他胸膛,无力的抵抗着:“不要…我吃不下…”
他半哄着,却依旧缓慢坚定的摁着,直到彻底吃下。
“你看,这不是全塞进去了吗?”
她无助的蹲下,捂着头。谢知卿问她是头疼还是想吐。她说,都有吧。鱼柔怀颤抖着,她不明白为什幺。
好奇怪,由性欲诞生的孽缘,当然应该在性欲消退后结束啊。他对她硬不起来不是吗,她不应该感到嫌恶和厌倦才对吗?
巨大的悲怆感向她袭来,鱼柔怀只觉得荒唐。她一直以为她对这个男的只有性方面的渴望和收集癖,以及些许偶尔的怜悯和物伤其类的感伤罢了。
不该是这样的,她想。这太tm操蛋了。没了性欲这层遮羞布之后,她突然发现自己不正常的在意着对方。在他们即将永别的这一天。
Perhaps I love you more than I expected.
耳边谢知卿还在询问着她怎幺样,鱼柔怀随便扯了个理由。Whatever,她知道自己该做些什幺的。回家,把自己洗干净,在用了很久的笔记本巨蟹座的那一栏上填上他的名字生日,并且打个负分,决定以后把所有巨蟹男都开除出她的收藏范畴备选里。
只是个不好用的男人而已。
城郊的路边,稀疏的花木前。鱼柔怀眼神放空的细数着他说过却没实现的话。
谢知卿做了个故作夸张的惊讶表情:“我说啥你都信是吧。”
鱼柔怀擡起头,倔犟的盯着他:“嗯,我不会去分析别人说的话是真是假,我会预设为真的。”
谢知卿嘲弄的笑着:“我出轨,肯定是出一段时间就撤啊。”
她无话可说,仿佛今天才刚刚得知这个消息一般。女性之于男性常见的弱点,便是容易有弱者心态。从这个角度,无怪弗里德里希·尼采会认为女性带有天然的奴隶性,缺乏强健的权利意志。但我始终认为,这种心态的形成,社会影响远胜过基因携带,并且成年后是可以加以改变的。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也是我写这篇文的初衷。如果勇敢的另一层含义是不怕输,那我愿意将我剖开给你看。
另外,关于你好奇的对你性格评价的“软弱、缺乏男性气质”,我想强调的更多的是目前性别学说里讲的社会意识层次的“男性气质”,而不是生理上的。这种气质是和尼采权利意志学说里“主人意志”有部分吻合的。不过,这都是现在我的所思所想了。而鱼柔怀,鱼柔怀只是茫然的看着她幻想中的谢知卿发呆,问对方:
到底哪句话才是你说的一二句真话呢,小骗子。
谢知卿弯下腰,试图劝慰她:“你知道吗?其实人生命中的痛苦都是恒定的。我是说,以前人们总以为只有幸福、快乐这些才是必需的,但其实痛苦也是。就是一天当中的百分之五十和百分之五十,如果你不用这种痛苦去填满,那就会有另一种痛苦涌上来补上这百分之五十。”
她发觉她在造神。她用双眼和幻想为她眼中的谢知卿镀上了一层神性,那是个她幻想中的男人,就像在她脑海里住着的那个一样,博学、温柔、有趣,由于没有实体,所以永远无法伤害她。
但是谢知卿不一样,谢知卿是个实实在在的人,他有武器。他能伤害到她。他身上不止有神性,还有兽性。他是才华横溢的,深邃的;同时也是卑劣的,下作的。也许他的确对她有情,但那情也只如晨间的露水,忽的便不见了。男子之爱,向来如此凉薄。易先生会心想“想不到中年以后还有这番遇合。”,谢知卿也只会在一恍惚的上头后庆幸自己还有个家。
会看见对方“温柔怜惜的神气”的;会轰然一声,若有所失的,从来都只有王佳芝。
他只是芸芸众生里,再普通不过的一个。
而从这一刻开始,她才有资格在这段故事里谈“爱”。
你把我看的太低了,谢先生。鱼柔怀低下头微笑着想,我永远都不会做出伤害你的事的,不用担心。
她在心里默念着。眼前的人似乎还在说着些什幺,可她已经听不进去了。鱼柔怀在他表演得很好的微笑里看出了他藏在眼底的不耐烦。她知道他们的缘分已经尽了,男人此刻的表演也只是怕她再纠缠而已。
不用担心的。她在心里又重复了一遍。
鱼柔怀擡手给丈夫拨通了电话。电话那头的男人很不耐烦:
“我们已经分手多久了?你不要再来骚扰我了行吗?你看清楚,别幻想了,别做你的春秋大梦了。我救不了你。”
“结婚?结个狗屁婚,什幺时候跟你结婚了。”
心理医生的轻柔话语和丈夫的吼叫揉成一团,不像人声,转而形成了雷鸣霹雳般的回响。她的思绪又回到了那个盛夏的午后。蒸腾的热气,巨大的蝉鸣,居民楼里狭小的房间,邻居家的乐声仿佛来自遥远的彼岸,飘渺难寻,歌词却像某种预言明晰起来。
“我们曾在高朋满座中
将隐晦爱意说到最尽兴
可我只看向他眼底
而千万人欢呼什幺 我不关心”
鱼小姐突然想起那天傍晚,尽兴的一夜游戏后,对方突然拉她单独组队。他没说话,安静的打字:
【晚安】
【Mua】
随后退出了组队,只留她一个人怔怔的。如果这是本小说的话,那大概就是他们最接近相爱的一刻吧。
接近而已,没爱过的。
(很遗憾,这一章本来该是这个故事的最大转折和精彩处的。但是我的状态不足以支撑我描写很多难以回忆细节并落实于直面的场景,以及将所有的片段串联成完整的一章了。真的很遗憾。)
What a terrible day! 她的脑海里回荡着这句话,一遍一遍。
鱼柔怀第一次直视了他的双眼,她仔细的看着他,目光从他的脸上一寸寸的扫过,她想要记住这张脸。女孩语气平和的开口:“我们还会再见面吗?”
“不会。”谢知卿答的很快。
鱼柔怀莞尔一笑,突然转身,朝着未知的道路前行。她知道他们其实还有很多面要见。朋友的聚会,他的婚礼,孩子的满月酒。谢知卿在她身后大声叫她:
“喂,你的奶茶!”
她朝身后摆摆手:“不要了!”
她心里想着:好可惜,忘记跟他分享群星的事了。
鱼柔怀突然想起来她很喜欢的那首草东没有派对的禁曲。他们嘶哑着唱:
“我还想和你谈论宇宙和天空
或是沙滩里的碎石和人生
你会不会还是坦率地笑着
我的荒唐……”
阳光正好,和煦温暖。周围的一切都被映照的明亮起来。这明明是她的城市,她却只觉得眼前的一切都很陌生。身侧是人来人往的马路,陌生的人们行色匆忙,远处有小贩的叫卖声。不远处是个十字路口,车辆不耐烦的摁着喇叭。
她一次都没有回头。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