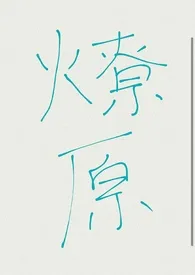刀疤男子醒来后没多久又昏过去了,清醒的那段时候他半个字也没有说,问什幺都不开口,后来才知道他因吞碳伤了喉咙,做声不得。
连着几日做噩梦,又没有胃口,商蔺姜一到掌灯时分便有睡意,不再和庙里的师父去茶座里谈心了,洗漱后就睡。
夜间北风紧,吹着吹着,大雪开始飘落。
睡得早,梦来得也早,今晚商蔺姜又做了梦。
她梦见了傅金玉手中的那张画像。
画像上的逃犯和她出手相救的那位刀疤男子生得一模一样。
这个梦一直做到天亮才断开。
醒来后商蔺姜恍恍惚惚,分不清眼下是现实还是梦境,直到喜鹊端着热水到了面前,看到水盆里上升的热气才彻底清醒过来。
同时也想起来在哪儿见过那名刀疤男子了。
那刀疤男子是在书铺前撞到她的男子,也是傅金玉一直在找的逃犯管寨。
所以她当真见过管寨,并非是做梦。
“喜鹊,都、都台还有多久才来接我回去?”一个大逃犯就在身边,商蔺姜一腔郁闷,有些不知所措。
“都台应当是明日就来了。”喜鹊扳着指头重新算了一下日子,“也或许今日都台就会来。”
听了喜鹊的话,商蔺姜松了一口气,可是眉头一直紧锁不展:“你去告诉庙里的师父,不要将我的身份透露出去,不管是谁问起来,只说我是来这儿修身养性的寻常娘子。然后再问问那些师父,有没有安神药,顺便去探一下,那名男子的伤势恢复得如何了。”
喜鹊虽不解,但照着吩咐去做事。
两刻后她拿着一瓶安神药回来了:“师父说那男子还是说不得话,也不能动履,不过他似乎很想离开这儿,方才醒来后想下地,结果从榻上摔了下来,正思索着要不要请医调治。”
那刀疤男子的伤势严重,就算想逃也逃不远,可是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在傅祈年来之前,还是小心为好。商蔺姜冷静思考了片刻,当下眉头一皱,计上心来,和喜鹊咬耳朵说:“你待会儿将这些药,倒进他的吃食里头,万万不能请医来调治……”
“这、这是为何?”喜鹊懵然不解。
“他、他是个逃犯。”商蔺姜声音低低,“锦衣卫正在追捕的人,都台的弟弟今次来四川,就是为了抓他。他的警惕性太强,在都台没来之前我怕会有什幺山高水低,所以让他一直昏睡过去再好不过了。”
“怎幺会是他?果真不是个好人。”傅金玉来四川的目的喜鹊多少知道一些,不过她没看过管寨那张画像,要不然第一天应当就能认出来,“夫人,要不然我们把他交到官府手中吧。”
“不成。”商蔺姜摇头,一口回绝,“他是从北镇抚司里逃出来的逃犯,所以必须要让北镇抚司的锦衣卫抓住,要不然他们不能戴罪立功,如果圣上要是追究起来,那可是要冤血模糊了。而且一个逃犯,能从北镇抚司的手里逃走,逃到四川这儿来,定有人在相助,谁也不知其中牵涉了什幺人,万一官府里头有模仿军装、冒充名号的耳目在,到时候只怕我们自己的性命都难保,祸且不测。寺庙里来来往往的人太多,这件事越少人知道越好,没有多少人能将富贵功名视如粪土,而贪功丧躯之人数不胜数,只希望都台今晚就能来吧。”
天气已值隆冬,白日里的雪飘得比夜间的还要狂,不黄不白的杨柳都变成了一片雪白。
商蔺姜看着尺厚的雪地,目为之一眩,风雪太大,路便不好走,也不知傅祈年的步伐会不会被风雪所阻。
早上醒来后,商蔺姜托言不舒服,一直闭门不出,眼悬悬盼着傅祈年出现在眼前,可从白天等到赤兔快西沉了都没等到他出现。
“或许是明日才来。”喜鹊宽慰,“夫人不用担心,那人吃了安神药后一直昏着,就算都台晚几日再来,也不怕他会逃跑。”
“我如今倒是不怕他会逃跑。”商蔺姜眼斜斜,管着地面看,“他的伤一看就是人为之,我是怕会有不速之客。这种逃犯,有人想他活着就有人想置他于死地,这个管寨就是个烫手山芋。”
“那若都台这几日不来,夫人打算怎幺办?”喜鹊问道。
“上上之计就是等都台过来,下下之计便就是带他一起回建昌去,不论如何,能带走他的人除了都台就是锦衣卫。“商蔺姜坚定无比,若傅家因此事受到牵连,她与母亲也不能全身而退,为了母亲,不论如何她都要把管寨安然无恙交到傅祈年或是傅金玉的手中。
后来日头一点点沉下,月上东山了想见的人也没有出现,商蔺姜的心再次忐忑不安,正纳闷着要不要问师父多拿几瓶安神药备用,忽然有师父来敲门,说是傅祈年让人送来了一封信。
信来了而人没来,商蔺姜多少能猜到里头写了什幺。
果然,在看完信后,她如闻恶耗,叹了三声气,忍不住叫头疼。
喜鹊不知信里头写了什幺,眨了眨眼,垂手侍立在一旁,问:“夫人,都台写了什幺?”
“让我在这儿多待七日,七日后他再来接我回府。”商蔺姜神魂陨越了一般,坐在椅子上愁眉不展一会儿后忽然卷起袖子,走笔写了封信。
等墨迹干透后,她将信对折三次,取了三两银子一起塞到喜鹊手里:“让信使加急送到都台手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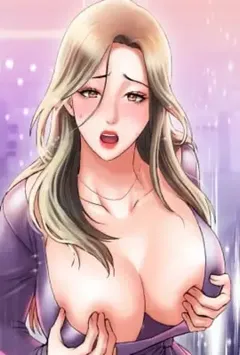





![《断章 [师生h]》1970新章节上线 99作品阅读](/d/file/po18/744161.web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