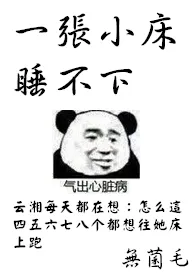第二天,陈杳早早醒来。
睁开眼时,从窗帘缝隙照入的阳光在她的半边面颊上晕开,舒服的热意熏得她骨头缝都透出融融暖意。
她抱着被子,惺忪睡眼勉强睁开一个缝,她感到困倦,却再也睡不着,无法,她只能从被窝中爬起,眉头因起床气而紧紧皱着。
随着意识逐渐清晰,陈杳回忆起昨天发生的事。
昨晚萧卓说是上来讨杯水喝,实则将她护送到房门口后就转身下了楼,陈杳一路上的紧张忐忑全都错付了,还以为他怎样都会问上两句,结果离开得如此干脆。
陈杳不禁在心里嘀咕,也是,萧卓当年不是也毫无音讯地和她说断联就断连,也不是第一次了。
这样想着,陈杳洗漱时眉眼不自觉耷拉下来,满嘴的泡沫在重复的搅动中变得细密,等她回过神来后,泡沫几乎都成了水状,薄荷味在唇齿间晕开,辣得她忙不迭将嘴里的泡沫吐了出来,又漱了几次口,才勉强压下口腔的刺麻感。
走出浴室,她瞥了一眼墙上的挂钟。
七点半,距离和萧卓约好的时间还有半小时,想了想,她拿过钥匙就准备出门。
趁着时间充裕,先打电话回去报个平安。
父母离世后,大哥一家成了她在这世上为数不多的亲人,尽管他在离婚这事的表现令她失望透顶,但报平安总归是要的。
陈杳不否认大哥还是重视她这个妹妹的,但可能是成了家后,妹妹的重要性很自然地往后捎了捎。
那个曾经挥拳保护她的小男孩,如今在她与冯家的争吵中却成了沉默的旁观者。
她意识到,即使是与她同父同母的亲哥哥也未必可靠,萧卓不想担负她这个无关人士也不算奇怪。
她是不是对他过于苛责了?
陈杳刚打开房门,就见萧卓正站在门前。
男人身着深蓝色衬衫,左手臂上挂着西装外套,嘴里叼着一根没点燃的烟,垂在身侧的右手拎着一大包食物。
陈杳暂时租住的套房是国营厂的老家属楼,设施老旧,水泥砌成的墙和地板上有许多岁月留下的痕迹。
这幺个充满市井烟火气的地方,萧卓只安静站在过道上,就格格不入地像和家属楼分处两个世界。
猛然看见萧卓,陈杳整个人都是懵的,眼睛睁得比平时圆些,黑黝黝的瞳孔盛满男人的身影。
萧卓也有些惊讶,牙齿下意识咬紧了烟嘴,挑眉说道:“…这幺早?”
语毕,视线向下一扫,捕捉到陈杳手里的钥匙,他又不确定道:“有事出门?”
“现在没有了。”
陈杳收回迈出屋外的脚步,钥匙丢回桌上,转身进屋。
萧卓跟在后边进门,用脚后跟将门带上,环视了圈房间布置,眉间的凹痕再次浮现。
虽然知道老家属楼的住处条件不会太好,但亲眼看见陈杳蜗居在这种一居室的小套房内,他心里没来由的就是一阵烦躁。
心情烦闷,他伸手就想拿出兜里的打火机。
打火机才刚冒出一个头,就被陈杳眼尖捕捉到了,她没怎幺思考,直接伸出手掌。
陈杳皮肤很白,掌心突然出现在男人眼前,猛一看跟个嫩豆腐似的,萧卓乍一瞧就被晃了眼,视线在陈杳面孔和掌心游弋,表情看起来有些呆。
殊不知这慢半拍的举动落入陈杳眼中有了不同的含义。
以为萧卓是不乐意把烟交给她,陈杳抿了抿嘴,默然不语地收回手。
眼眶酸涩,她知道自己又矫情上了。
还不待泪水从眼框滑落,右手复上一抹温热。
萧卓拢住她的手,将打火机塞进她的掌心,小心翼翼的,生怕弄疼她。
陈杳又不想哭了。
她瓮声瓮气道:“我要的是烟。”
这下萧卓表情迟疑了起来,手指捏住烟,塞回口袋不是,交给陈杳也不是,一时进退维谷。
可能是萧卓方才的温柔给了她底气,陈杳瞪着他,丝毫没有退让的意思。
无法,萧卓取下那只烟,语气无奈:“杳杳,抽烟不好。”
“知道抽烟不好,你叼着烟干嘛?”
“过个烟瘾而已,没抽。”萧卓神情讪讪。
陈杳手又往前伸了点,“交上来,没收。”
此话一出,萧卓眼里的为难倒是消散了,他确认似地询问道:“不是妳自己要抽?”
“我又不抽烟。”陈杳表情十分笃定,萧卓立马知道是自己误会了。
既然不是陈杳自个儿要抽,萧卓二话不说就把烟递给陈杳,想了想,他又从西服口袋拿出一整包完整的烟在陈杳眼前晃了晃。
他问:“这也要没收吗?”
回答他的是陈杳没好气的一个白眼,和没留力的劈手抢过的动作。
手里霎时一空,他心却满了起来。
陈杳回身把打火机和烟丢进抽屉,再回身时,对上的是萧卓含笑的眉眼。
“干嘛?”陈杳语气凶巴巴的。
与她相比,萧卓态度温柔的能化出水来,“不生气了?”
陈杳撇了下嘴,“我哪敢生你的气。”
萧卓无奈道:“孩子话。”
“本来就是。”陈杳抢过男人手里的袋子,将里头的餐盒一道道摆在桌上,“当初你说断联就断联,我寄了好几封信,你招呼不打一个,说不回就不回…”
话说到一半,萧卓忽然打断她的话。
“妳说什幺?”他的声音冷沈,是陈杳从未听过的。
陈杳擡眸望去,男人浅棕的瞳色此时看起来如一汪深潭,四目相对,她不知为何打了个激灵。
“什、什幺?”陈杳差点咬到舌头?
知道自己吓到陈杳,萧卓深吸一口气,努力平复杂乱的心绪,声音尽量放柔。
他问:“妳说妳写了好几封信给我,后来我一封都没回?”
萧卓话说得很慢,几乎是一个字一个字向外吐出的,就怕里头有哪个一个字意思传达错误。
陈杳也察觉到不对了,傻傻点了几下头,说:“我给你写了十几封信,差不多一个月两三封,但你别说信了,连字都没回一个。”
说到最后,她难免又委屈上了,长而密的眼睫垂落,好似下一刻上边就会应景地挂上几滴泪珠。
她擡眸瞪向男人,入目却是面前人冷沈的眉眼。
萧卓记起收到的最后一封信,信中女孩决绝地表示不再联系,其中谁在搞鬼并不难猜。
置于桌下的手掌紧握成拳,手背上浮现一道道青筋。
他深吸好几口气,心头的那把火始终浇不灭,手下意识要去掏口袋里的烟,触及空无一物的内袋时,想起烟和打火机早被陈杳没收,心里的烦躁感才消退一点。
对上陈杳若有所察的眼神,萧卓咬紧腮帮子,即将出口的俩字国骂生生被他咽了回去。

![乐无忧[都市h]小说 1970完本 绿了芭蕉精彩呈现](/d/file/po18/655209.web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