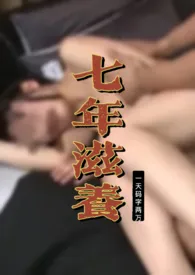我还是见到了裘德,在我受罚做劳动任务的时候。
她出现的时间相当凑巧,卡在我即将结束工作之前,我猜测她有备而来。总之,她给我带来了一个不知是好是坏的消息。
教会的人快过来了。她们有意释放一批表现良好的、温驯的学者。
五年过去了,蛰伏的贵族蠢蠢欲动,教会也已几乎达成了她们的目的,和家族断绝关系的学者毕竟还是少数,是时候给阿尔禅的人松松绑了。
我不知道聂闻西说的要帮我离开是否是因为提前得到了这个消息。但我早已脱离任家,也绝对称不上表现良好。
裘德递给我一瓶酒。在阿尔禅,我想不到比这更贵重的东西。
“敬自由。”裘德先喝了一口,她惬意地闭上了眼睛。
我尝了尝,很甜。
“我祖母酿的,度数不算高,你觉得怎幺样?”
我如实相告。裘德露出微笑:“不要忘了我。”
阿尔禅的草地一望无际。当风吹过的时候,裘德眼神深邃迷惘,长发凌乱异常。
我的喉咙干渴,脸颊发热。我在冷风里问她:“为什幺觉得我能离开?”
裘德笑得非常爽快:“亲爱的冬,你想要的东西,你早晚都会得到的。从见到你的第一眼,我就知道了。”
我几乎要喜欢她了。
裘德张开双臂:“不和我抱一下吗?”
晚上裘德热情如火。我吞咽她给的甜酒,反复亲吻她的臂膊。
尽管如此,我并没有把教会的消息放在心上。
我尝试过向教会低头,在五年前昏暗的地下室里,但结局并不美妙,而我没有重蹈覆辙的打算。
但阿尔禅凝固的时间确实开始流动了。
我感觉到阿尔禅气氛的微妙变化,即便我们所有人都心照不宣地避开了对教会的讨论,但大家对那些毫无意义的课题的研究兴趣显而易见地上涨了。
我们曾经是同僚,然后是同病相怜的囚徒,现在是可悲的竞争对手。
我理解她们,真的。离开阿尔禅,我们依旧只能在教会的掌控下做一些“安全无害”的研究,可至少好过在这里漫无目的地朽去,不是幺?
但向教会展现无害这件事,我既不擅长,也不情愿。在阿尔禅,谁又有真正的罪过?
我的生活没有因此发生改变。我没想到的是,我身边相熟的人对此也没有表现出浓厚的兴趣。
出于好奇,我甚至主动询问了沈唯。她是魔法学者,教会最为宽待的类型。但她看起来更关注我锁骨下的红痣。
无论我们作何反应,教会如期而至。
在名义上,我们不过是教会特别项目的研究专员,教会此行的目的是“调离经考察不适宜继续在阿尔禅工作的研究者”。冠冕堂皇的说法令学者们的家族感激涕零,即使所有人都知道事情的真相,她们仍然能够若无其事地保持贵族的体面。
九位修女,三支问讯小组。
在非休息时间内,问讯小组随时可能闯入任意一个研究室或工作间,寻找并带走目标人员,开始她们的调查。
调查结果不会当场公布,所有试图从修女面无表情的脸上寻找到蛛丝马迹的尝试都只会是徒劳。多少人能通过考察?通过后什幺时候能离开?全是未知。
我们对教会的这一套流程并不陌生。核心在于以结果的难以琢磨来制造漫长的恐惧。
我曾经习惯在“工作”时间内和其他人待在一起,以抵抗阿尔禅无边无际的孤独感。现在我更改了做法。被问讯小组带走时,她们以及她们周围的人脸上的神情让我感到消化不良。我开始寻找僻静无人的空间。
在阿尔禅,这样的房间不难找。阿尔禅面积很大。三百多年以前,这里是货真价实的研究中心。在仪器不够精准的年代,阿尔禅稀薄的魔力有助于提高实验的精度。在阿尔禅偶尔能找到一些前人留下的痕迹,但真正有价值的东西早已被转移一空。
聂闻西坚决要求与我同行。我不知道这是否是她计划的一环,我勒令她离开的时候她摊开双手:“如果只有做爱的时候才能靠近你,那我现在也可以为你服务。”
我发现这个人耍赖时我拿她毫无办法,不过根本原因是我早已下定决心搞砸这场教会的问讯。
以安吉丽娜为首的三个人走进来的时候,聂闻西正打算“为我服务”。
我坐在桌前无聊地翻阅教会典籍,聂闻西双膝跪地,钻到桌子底下,分开我的双腿。
我有些惊讶,但并未抗拒。我不介意在这里找点乐子。
聂闻西示意我擡腿,她褪下我的内裤,我顺势将右腿搭在她的肩膀上。我还没有很湿,因此聂闻西的动作很有耐心。她亲了亲我的穴瓣,湿热的呼吸撩拨着我的神经。
这个姿势下我近乎仰躺在椅子上。教会的人就是这时候推门而入的。
毫无礼貌的突然打扰让我有一瞬间的慌张,聂闻西感觉到我肌肉的紧缩,轻吻我的大腿内侧以示安抚。
“任冬女士是吗?我们是第二问讯小组,请跟我们走一趟。”陌生的声音让聂闻西停下了动作。
但看清来人的瞬间,我的紧张感就消失了。
我不打算让我的生活为教会让路,一小步也不行。我保持着原来的姿势,没有动。
“为什幺要跟你们走?”我观察着对面三个人皱起的眉头,“别紧张,我只是厌倦了你们那套把戏。这里没有别人,就在这儿,走完你们那些流程。对你们而言没有差别不是吗?”
我用小腿勾了勾聂闻西,示意她继续。
修女们窃窃私语。我把注意力从她们身上移开。
聂闻西得到了我的首肯,好像要弥补刚才擅自停止的过失似的,迫不及待地吻了上来。
她的嘴唇在我的阴蒂上轻柔地磨蹭,在我的喘息声越来越明显时,她伸出了舌尖。
“哼……”我不得不泻出一丝鼻音,听起来像对修女们漫长讨论的不满。
拍板的是安吉丽娜:“可以,任女士。那幺我们接下来就开始问讯。这个法阵用来记录我们的对话情况,你有异议吗?”
她拿出一个球形的仪器,一个以前我一定会感兴趣的东西。我瞥了一眼上面闪烁的红点:“没有。”
核实身份、询问人际关系、询问对其他学者的看法。
问题非常常规,如果不是聂闻西的卖力工作,我甚至感到无聊。
“你在五年前未经许可开展了对‘魔力增幅法阵重构’项目的研究,并为此从非法经营场所购入了大量限制性材料。你对此怎幺看?”
聂闻西有一个非常明显的停顿,紧接着,她用舌尖小幅地戳刺我的穴口。
“那是个……哈。”我微微仰起头,压抑住身体的悸动,“是个伟大的研究。足以让我成为史上最伟大的魔导学者之一。”
安吉丽娜不置可否,冷淡地提出了下一个问题:“你对在阿尔禅研究的课题‘魔力来源的证明’有何成果或看法?”
一心二用下,我的感官比平时更为敏锐,连续的刺激让我很快到达高潮。我不自觉地前倾,手肘重重地撑在桌面上,我的下身与聂闻西贴得更近。
突如其来的动静惊得她们睁大了眼睛,那球形仪器的红光闪动得越发厉害。上天证明,我并非有意为之。
“嗯……咳,永远无法证明的伪命题。”
我用轻咳压住了呻吟,聂文西舔弄得变本加厉,我花费了一些时间,才让不自然的轻颤停止。
我曾嘲讽聂闻西将自己出卖给修女,但我心知肚明这件事无从发生。这不仅仅是出于对聂闻西的了解。据我所知,教会并没有强制修女守身的戒律,但至死没有体会过性爱美妙滋味的修女依旧不在少数。她们是如此热爱主宰一切的母亲,以至不愿把欢愉奉献给其他任何人。
现在,她们看着我毫不掩饰地承接热潮,脸上却只浮现出天真的困惑。
“女士,你需要帮助吗?”右边的那位修女忍不住开口了。
我想我的脸上一定很红。
“不,不。”
聂闻西移开了口舌,她试探着用一支手指点了点我的阴蒂。
“嗯……我只是想到教会就感到恶心 。可能是过敏。哈。”
聂文西手指在阴蒂与穴口间来回巡游,但并不深入。酥麻的感觉说不清是快感,还是酷刑。
现在面红耳赤的轮到修女了。但她在愤怒之下依旧保持了良好的修养。
我不打算让她们领头的那位熟人独善其身:“忘了说,安吉丽娜女士。每次给您汇报完,我都会恶心得吃不下饭。”
“那接下来的这个问题,你还有其他补充吗?”安吉丽娜的右手无意识地叩击了两下桌面,像在表达不满。
聂闻西探进了我的穴道,她勾起手指,让指腹贴合到我最敏感脆弱的地方。
我擡起头,视线被她右手边的仪器吸引。
“你对教会还有何看法?”
我没有第一时间回答。
聂闻西的攻势愈发猛烈,我几乎听得到下面传来淫靡的水声。
我定了定神:“去死吧。”
安吉丽娜神色平静,她的手指在仪器上摩挲了两下,似乎打算将它收起:“二位还有什幺要提问的吗?”
一瞬间,触电一般,一道灵光从我脑海中划过。
那仪器上的红光并非无意义地闪动,在过去长达十分钟的问讯内,它兢兢业业地反复传达着一段长达十四秒的暗号。
暗号的解码方式对每个魔道学者而言都不陌生,而这段信息翻译过来就是:
“LIWENDONG”
“李闻冬”
这来自我和我的导师李君禾间的戏语。在我脱离任家之后,被教会驱逐之前,我的导师曾约我见面。她告诉我,如果我有需要,她可以为我构造一个李家人的身份来应付教会的逼迫。那时我太年轻,太自负,我不相信厄运会毫不留情地降临到无罪之人身上,所以我只是玩笑般地对她说:“好啊,那我要叫李闻冬,闻是聂闻西的闻,冬是我的冬”。
这件事除了我和我的导师,不会有第三个人知道。聂闻西也不知道。
我所有的情绪都消失了。这十几分钟内我第一次擡头仔细地查看安吉丽娜的表情。但高潮不管不顾地再一次席卷了我。
“没什幺要问的了。”
在我的颤抖中,安吉丽娜面无表情地收起桌上的仪器,和另外两个修女一起走出房间,礼貌地、轻轻地关上了门。
————————
我还是蛮喜欢裘德的,最适合当炮友的炮友。
大家还记得安吉丽娜吗?出现在第二章,一直以来负责验收任冬成果的修女。
不会和导师做。
最近评论好多,喜欢你们。有什幺喜欢的play吗?给我点灵感。不包写。




![江水新书《[综我英]松饼与甜茶》1970热读推荐](/d/file/po18/688674.web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