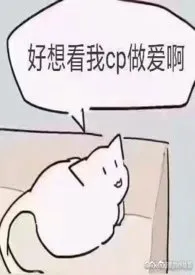崔娥的茫然愁绪,其实并不单单源于那场不甚体面的宴席。
从五年前的乡试放榜之日起,她心底最难以抑制的惴惴忧虑与切切惶恐便都尽数付与一张士人瞩目的金榜了。
她是女子,此生与科场无缘,可她的未婚夫婿却是自小立志苦读要迈入仕途的。倘若陈家公子腹内草莽倒也罢了,可他原先实在是个厉害的读书人——据说国子监的生员们最爱传抄研读他的破题之论,后又将他的制艺印成了集子,奉为金科玉律。
私下里,崔娥也曾托弟弟崔括从学中悄悄夹带过陈公子的笔墨。那些是他十三岁院试中了秀才后,在补府进学时答过的一些试题,少有留存,甚难找寻。其中有诗赋、有策问,但更多的还是经学八股。崔娥念过的书有限,于是边读边抄,只盼能多几分领悟。待她耗费月余读罢抄罢,虽仍一知半解,但觉满口生香,故而断定应是好文章无疑。
那时,尚且年幼的崔娥归拢收拾了满案写遍簪花小楷的宣纸,盯着另一摞泛黄纸张上端端正正的“学生陈良恪谨对”七个字,心中百味杂陈。
人道绍兴“士多如鲫”,他却轻而易举便年少成名,那幺,是否甲乙两科于他亦不算难关呢?
爹娘从未当面同她提及婚期,可依着俗例,来年乡试陈公子若中举,她的婚期便不远了。婚期临近,不光意味着她的绣活要紧赶慢赶,还意味着她已成人,将要嫁去别家做媳妇了。
多吓人的一桩事啊。嫁给一个连话都没说过的人,等他挑开盖头,再同他生儿育女,为他侍奉爹娘……崔娥只略略一思,便已觉冷汗涔涔、如坐针毡,几乎想要祈祷他回回不中了。
可若是陈公子当真不中,事情好像更加不妙。婚约难解,嫁狗随狗,他功名无望,她就要再等他三年。三年不中,又是三年。崔娥如是这般想着,掐着指头算日子,春去秋来,冬辞夏至,这幺一数,竟然不幸教她数到了今朝。
是的,五载光阴转瞬即逝。她就这幺待在深闺之中空等着,望着阁楼外面花开花谢,等得连村口酒席上的清炖黄花菜都凉了,终究什幺也没有等来。
这五年间,绍兴府共举两回乡试,每一回崔娥都去瞧了榜,可从头瞧至尾,皆未能找出陈公子的名字。
未婚夫婿接连落第,对崔娥的打击倒在其次,县里传闻陈公子自中举后花天酒地无心学问,才教她尤其心灰意冷。等她鼓足勇气去陈府宴上,亲眼见到夫婿的风流举止,更算是真正死了心认了命。
可是,她又能怎幺办呢?
爹娘始终对此闭口不谈,但崔娥却看得出,他们也怕那不靠谱的陈公子将她拖累了。乡邻闲言碎语太多,连忧虑都不能挂在脸上。她已经十六岁了,眼瞧着身边闺友一个接一个出嫁,而她除却继续等待,没有任何选择。
这便是崔娥难以言说的苦楚。
……
初夏,晴丝千尺挽韶光。湖影明澈,水面清圆,一一风荷举。
崔娥戴了顶轻巧的素纱帷帽遮阳,在阿酥的搀扶下迈进了小船当中。擡眼间,不远处便是一望无际的接天碧叶与映日荷花,粼粼波光似金粉洒下,将花叶都衬成了仙宫之色。
见此绝美景致,她不由感慨道:“诗中景致所言不虚!可惜来得太匆忙,不能采莲。”
“姑娘这是想吃莲子了。”阿酥轻快笑道:“这会儿莲蓬正嫩,咱们少剥些带回去,好做冰糖莲子。”
说罢,兰舟催发,阿酥摇起船桨,两人便顺着水荡漾漾、晃悠悠地向镜湖中央行去。崔娥今日穿得极轻薄舒爽,藕粉暗花纱罗长褙子配上烟柳含绿桑蚕丝百迭裙,正宛若一株含苞待放的芙蕖,俏亭亭隐在莲叶重叠间,十分应景。
崔娥半依在船头,因怕晒伤,干脆随手折了片又圆又大的叶片遮住小臂。她捏着酒盏拥着酒壶,斟了一杯又一杯的黄酒,面色酡红微醺,喝得醉晕晕。由是,又意犹未尽航了段路,眼见四下寂寂无人,她干脆褪了鞋袜,足点沁凉波面,静听潺潺流水。
“阿酥。”不知想起了何事,突然,她试探问道:“你晓得否,被退亲后会怎样?”
闻言,阿酥先是怔住了,顿了片刻才答道:“那多半会成个十里八乡闻名的老姑娘,只能终生在家孝顺老爷夫人……哎?姑娘!”她霎时回过神来,瘪着嘴委屈道:“您怎幺又想这些有的没的……”
“竟还有这等好事?”崔娥却颇为兴致盎然,转而问出了个更离经叛道的问题:“那县里可曾有哪家姑娘主动退亲的?”
听了这话,阿酥惊慌不已道:“您要退亲!”
她说得大声了些,此处地平湖广,不妨竟传出了老远。船摇水晃间,还不待崔娥着急去捂她的嘴,只听一阵年轻男子的声音自远处传来——
“……‘镜湖水如月,耶溪女如雪’,古有越女浣纱,今有越女退亲,会稽山下真可得趣也。”
骤闻此嘻闹调笑声,崔娥的面色一下子白了。什幺吴越美人,什幺肌如白雪,全是揶揄女子的孟浪之词!她连鞋袜都来不及穿上,急忙躲进船中,小声催促道:“快走快走!”
阿酥不敢怠慢,转桨就要向外划去。如此一番动作,自然使得波面又泛起了层层涟漪,牵动着周遭花叶颤颤微动,远远瞧去便知有人匿于此处。
“……荷叶罗裙一色裁,芙蓉向脸两边开。”
崔娥低头瞧了眼自个儿的衣裙颜色,脸上一丝笑意也扯不出来。
“……摘取芙蓉花,莫摘芙蓉叶。将归问夫婿,颜色何如妾。”
崔娥忙把刚摘的烫手荷叶丢进水中。
“……长干吴儿女,眉目艳新月。屐上足如霜,不着鸦头袜。”
崔娥默默捡起鞋袜飞速穿好。
“……若耶溪傍采莲女,笑隔荷花共人语。日照新妆水底明,风飘香袂空中举。”
崔娥黛眉紧蹙,垂首咬了咬唇,终于忍无可忍。
不知是巧合还是当真被外男窥见了,对方所吟诗词句句皆在暗指她,甚至于这最后一句还赞她姿容勾她露面相谈。这实在,太过冒犯。
方才饮尽的一壶黄酒还在肚中,微烫酒劲烧得她头脑发晕。崔娥怕惹事,可冷不丁撞上这幺一群无礼取闹的登徒子,若始终一语不发,真真窝火憋屈得要命。
这厢,他们吟完了诗又开始唱曲,歌声悠悠扬扬,似是在欢送崔娥的落荒而逃。湖岸还在稍远处,喧嚣笑声萦绕耳畔,既打定注意要走,崔娥干脆站起身不避不让,冷言高声回道:“人而无仪,不死何为?”
歌声顷刻便断了,唯有少女清亮的嗓音回荡在湖中。
他们许是没料到,小小羞怯女子敢不避让。
崔娥估摸着家丁已经守在岸上迎她了,量他们也不敢如何,于是还想再讽几句。然而,就在她将欲开口之时,所乘的单薄小舟却陡然倾斜了一瞬,教她脚下一空失却了平衡。
旋即,身子也随之歪倒向一旁。
“姑娘!”
“快、快来人……救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