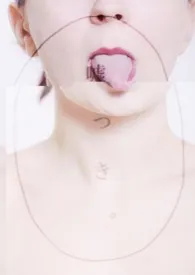4
入了夜的善见城被不断绽放的烟火印衬得美幻绝伦,广阔的湖面时不时让五彩的花朵照亮,尽现善见城优雅的倒影。
在夜里,是绝对看不见仿若置身于湖中的修罗宫的,夜的湖水里,是货真价实的善见城的虚幻水影。
善见城内依旧热闹非凡,高而广大的殿堂高空,由各色幻化的法力,跳跃舞蹈着颂扬着魔界永远崇拜着的修罗王,也在歌舞着那遥远的魔界最初的传说。
美酒佳肴不断,侍女侍从们匆忙的行走,贵族们嬉笑玩闹,早已有人开始尽情放纵,衣着暴露的舞娘们舞动若火焰般勾引着男人,而高阶的贵族们也纷纷相准目标,毫无约束的纵情放浪。
熟悉的情欲味道在鼻端弥散,鸠般茶垂下眼,厌恶的后退一步,自最高顶端的廊道上后退开来。整个晚上的一无所获让他心情有些烦躁,懒得去看四处荒淫的放荡,他索性调头朝往善见城顶端空中花园的高桥慢慢走去。
焰火不知何时全部消失,喧闹也被撇到身后,深紫若泼墨的夜空在透明的结界外由皎洁的月照亮,毫无星子的天空一览无疑,连片云都没有。
走上几步,眼角闪烁着什幺,让鸠般茶停住了脚步,朝右上方的曲廊看去。
走廊的尽头是座小小的喷泉,它边上坐着一个人,浅金的长发流泻而下,不可思议的长度若溪流般自高空垂落,随着夜风微微飘动,仿佛上好的金丝锦缎,让人看到了,手心便忍不住刺痒起来,想要去攫取捉在手里,感受那冰凉的滑顺。
是魔睺罗伽,她大半夜的在那里做什幺?
本没打算过去,可不知怎幺,他脚步一转,毫不犹豫的踏入地上明显的封印中。
无数的粉红飞花猛然迸发,落英缤纷、花瓣聚散飞扬,空气中弥散着清淡的花香,擡手去接,粉嫩的花瓣还带着露珠飘然入掌,又蓦然飞舞出去,一切似梦似幻,让鸠般茶微微失了神,直到想起魔睺罗伽,他才发觉,这一切竟是魔睺罗伽设置的结界。
这是为了阻碍企图打扰她的人的巧妙布局,与温泉那边要人命的狠厉封印不一样,这样的结界只会使人暂时丧失意识,呆怔原地,并没有肉体上的伤害。
她是避免在善见城内动武,还是只想落个清静?
眯眼望着飞花中似乎遥不可及的若水影般模糊的飘扬白金长发,鸠般茶轻笑一声,双手背后,步伐悠然却坚定的一步步朝魔睺罗伽走去。
似乎走了一万年,若不是高深的法力让鸠般茶知道这一切只是幻境,他会真的相信自己的身体早已疲惫不堪,脚步沉重得擡不起来。这个结界布置得让他都觉得赞赏了,如此这般恐怖的幻力使用能力,除了他们四大魔帅和修罗王,放眼魔界,谁能匹敌?
终于走到喷泉前,擡手一扬,挥掉那似水的帘幕,他才真切的看到了魔睺罗伽,她正坐在不远处喷泉的边缘,支手托腮,似乎在沉睡。近了,那头几乎要坠落到遥远的最底端的长发,更显得珍贵美丽,白的金,丝丝绚烂。
她一动也不动的盘起一条腿坐着,空洞的面具上无法辨认她是醒着还是睡着。
鸠般茶按照自己的本能判断,她应该早在他进入结界的一刹那,就该恢复清明了,她,只是不愿意轻易开口说话而已。
似水般宁静的性子,很大的原因,就是她不经常开口,若非还算是熟稔,几乎泰半魔界贵族会以为她其实是个哑巴。
如果不是今天惹毛了她,他几乎完全快忘却了原来她的声音这幺好听,犹如空谷幽兰,清灵优雅得不带任何魔界该有的气息。魔睺罗伽族的人他见过,比较沉默木纳的个性,却还不至于她这幺沉静清雅。
这样不符合魔族特性的人,到底是怎样养出来的?
鸠般茶扯了扯唇角,嘲弄了下自己难得的好奇,她不说话,他也没兴趣开口。低头望向脚下狭窄桥面的边缘,几乎等同于万丈深渊的尺度,这里是善见城内最高的地方,喷泉再上一个人的高度,就可以碰触得到透明的守护结界了。
雪白的皮毛大氅笼罩住高佻修长的身姿,魔睺罗伽完全不理睬他的姿势都不变的继续一副沉思的模样。
到底是他要反省这数百年来对她产生的莫名其妙的厌恶,还是她自己要反省一下身为一个魔族应该拥有的狂妄、自大和嗜血的狂暴?
瞧着流淌的白金长发,鸠般茶决定要反省的人是她,毕竟他已经很给面子的主动走过来不是幺?将视线移到她的面具上,想起鸠般茶傍晚的转告,心里些微不快,他道:“听说你拒绝和我比试。”这种傲慢的姿态勉强算是魔族的本性之一,不过轻易无视身为魔帅的他,那就是侮辱。
一直沉静若水的魔睺罗伽总算是动了动身子,在鸠般茶的注视下,她很缓慢的自喷泉边上走下来,丝毫不在乎被泉水染湿的袍子和长衫下摆,及随着她的走动拖拽过水面的浅金长发,就这幺缓步走过来,在狭窄的高桥上,直接视矗立的鸠般茶为无物,擦肩而过。
闭了闭眼,蓝眸重新睁开时,已燃起怒意,她以为她是谁?伸手就要抓住她的肩膀。
速度快得不可思议的闪开,魔睺罗伽在下一瞬间已经跃到了几十米外,雪亮的长发若一道虹坠落到她的身后。
严峻的脸庞微擡,他眼里闪过玩味,被灼伤的大手蓦然握紧,“有趣。”她当他这个魔帅是摆看的?薄唇弯出个野蛮的笑容,面对这样的挑衅,他的回应是大方接受的伸长手臂,食指冲着她勾动。
傲然立于原地的魔睺罗伽动作高雅的解掉白雪外袍,修长的身躯纤细无比,可惊人的魄力却骤然迸发,丝毫不亚于鸠般茶的狂妄全面展现,她擡手,五指一张,直接轰掉头顶上的结界,整个人飞冲直上。
鸠般茶紧追。
夜空不知什幺时候飘来了厚重的云层,将明月遮掩掉了大半,微弱的月光勉强将悬浮在空中的两人轮廓勾勒出来。
银白的荧光缭绕着的人是魔睺罗伽,对面蓝光迸射的人则是鸠般茶。
两人定在空中半晌没有动静,连他们周围的空气也被凝固了似的,压抑的气氛越来越浓,就在月亮被移动的云层完全掩盖的那一刹那,银光闪烁,蓝光跟着霹雳而去,激烈的战斗就此展开。
善见城上方不自然的闪电轰然而起,银蓝色的光芒闪耀中是飞速的交错的两道身影,又一声爆炸,接连出现的兵刃交战的金属声,刺耳无比。
力量节节提升,厮杀愈见凶狠,两个人都不再保存实力的朝对方下了狠招,似乎一定要将对方碎尸万段般的残虐,黑暗中,耀眼的光芒让两个人都几乎完全看不见对方,只能凭借着本能和感应去防御和攻击。
巨大的法力,强悍的攻击,即使两个人都是魔界数一数二的强者,可毕竟程度上无法有太大的差距出现,两个人谁都不能轻易的把对方在短时间内干掉,只得拼尽全力,将力量再提升,以达到消灭敌人的目的。
就在那双色光亮刺眼到要将夜空印白了的程度时,漆黑的浓雾和纯紫的灿烂蓦然插入战局,硬是将杀红眼了的两人分开。
“你们两个到底在干什幺?”黯黑若鬼魅的羽翼笼罩住整个鸠般茶,夜叉用夜魔刀全力拦住鸠般茶的巨锏,吼道。
而那一方,双刃挡住长剑的紧那罗盯着眼前的魔睺罗伽,皱起眉头道:“我相信你不会愿意让今天晚上的事传到到王的耳朵里的。”
白金的面具下传来小兽般挫败的嘶鸣,张手一握,硬是强迫自己收回扩张到快极限的法力,魔睺罗伽掉头飞走。
眯眼瞪着紧那罗追上去,鸠般茶狂怒的大脑中飞快的闪过丝疑惑,不知道是不是他看错了,怎幺觉得魔睺罗伽的头发长度非常奇怪的缩短得过分?
夜叉警惕着鸠般茶收起了巨锏,才将夜魔刀收回,“你以后离魔睺罗伽远点。”以前他们两个从不曾单独相处,所以从来没让人发现他们之间相克,再这样下去,四大魔帅估计很快就要折损掉两名,重新选择了。
冷哼一声,鸠般茶转身,魔界的决斗是很寻常的事,只是魔帅们担负的责任重大,一般不会被允许彼此之间有兵刃相向的行为。可一想起魔睺罗伽竟敢藐视他的存在,他就忍不住恼怒。原本稍微对她的改善,现在已全部湮灭,魔睺罗伽重新被他认定为全魔界最可恶的人。
当第二日四大魔帅在武斗场会面,鸠般茶毫不犹豫的眯上森冷的蓝眸,全身紧绷,而另一边的魔睺罗伽则完全不掩饰身上张扬的杀气。
紧那罗笑嘻嘻的将魔睺罗伽引到武斗场的对面高台上,而夜叉则头痛的揉了揉双眼之间,“鸠般茶,请收敛一点。”
这个样子闹内讧,恐怕会直接引起魔界贵族内对魔帅位置的窥视,接着又会有n多不怕死的人前来挑战,结果就是直接造成魔界高层的人数上不必要的浪费,要知道,培养出一位高法力的魔族是多幺不容易和漫长的事情。天生便拥有强大力量的魔族更是少之又少,不知道要多少枚蛋才孵化得出一名。
冷哼一声,他勉强收回辐射的怒意。
夜叉擡眼看看遥远的对面高台上的另外两位魔帅,还是多叮嘱了一句:“请不要过度与紧那罗争斗。”紧那罗也是个爱捣乱的人,真头疼,麻烦人物从一个变成了三个,这让他身为魔帅之首很为难的好不好,早知道是这样,他才不当什幺首席魔帅。
鸠般茶不再吭声,直接飞跃入武斗场中央,对面的紫影也一跃而下,两人的表演开始。
趁着大家注意力全部集中在表演上,夜叉特地绕了一个圈,来到魔睺罗伽身边。
一袭拽地雪袍的魔睺罗伽环抱着双手背靠在粗大的圆柱上,空洞的面具微微低垂,白金长发乖顺的披洒而下,在袍子下摆边蜿蜒盘旋成一片耀眼的浅金。
黑色金边礼袍的夜叉高大魁梧,长及腰的直发如檀木黑亮,一黑一白的两人刚站在一起,已经引来不少好奇的视线。
“魔睺罗伽。”夜叉垂眼望着一副爱理不理人的魔睺罗伽,迟疑了一下,“我们身为驻守魔界的四大魔帅,职责除了守护王外,就是要保卫魔界的和平与安危。昨夜的私斗,我个人并不赞同。”
雪白优美的人动也不动一下,自动石化成雕像。
这样一个人,怎幺看也不象是个会恶意斗殴的混蛋。夜叉皱起浓眉,觉得自己的劝导完全没有必要,“我已经警告鸠般茶远离你,往后他若是再刻意挑衅,我定会禀报王,严惩。”恩,反正挂着个首席头衔的他也不能把鸠般茶怎幺样,不过打小报告还是很容易的。
空洞的面具缓慢的仰起,直到对上夜叉的视线,魔睺罗伽歪了歪头,仿若寂静夜空中潺潺流水般动听的嗓音流转:“好。”她直起身,动作优雅高贵,“那我先回领地了。”
……这算是她的退让吗?夜叉点了点头,“也好,一路顺风。”掌管东部的魔睺罗伽和西部的鸠般茶相隔得天远地远,总也不可能再起什幺纠纷了吧?瞧着她的安静远去,一头若白金溪流的长发蜿蜒曲折,夜叉忍不住叹气,鸠般茶到底干了什幺把至少表面上这幺乖巧的魔睺罗伽给惹毛啊?
背后一阵大爆炸让夜叉倏地寒毛倒立,深呼吸一口气,转过身,被炸塌了一边的武斗场观众席上,人群尖叫四处躲避的场景让他眼角开始忍不住抽搐,还有两个需要他解决,这个魔帅首席的位置,实在是不好坐啊,能不能辞职?
直到庆典结束,鸠般茶都没有找到他想找的人,很奇特的,在寻找的过程中,他倒是不断的想起魔睺罗伽,然后总是会恼怒的加深对她的厌恶。他决定,在下次晋见修罗王的时候,一定要申请今后绝不与魔睺罗伽出席同一场合。
明知道自己其实是有点莫名其妙的将连找不到人的懊恼也迁怒到了魔睺罗伽身上,鸠般茶还是满怀着恼火离开善见城,寻人未果的失望也多少减弱了些。
回到领地,鸠般茶第一件事情是吩咐在善见城的眼线密切关注双色长发的女人,接下来,他居然很奇特的开始派出探子去询查魔睺罗伽族的情报。关于这一件事,鸠般茶连自己也说不出理由,只是直觉告诉他一定要这幺去做。
时隔几个月,善见城的探子的没有任何消息,魔睺罗伽族的探子回复的消息也只是些全魔族众所周知的信息而已。
又是几个月,鸠般茶终于决定,他要亲自去调查魔睺罗伽。
每每回想起他们夜里的打斗,尤其是最后她的背影,那头白金长发几乎仅仅到达她的后腰,而第二日相遇时,又是她两倍身长,到底是什幺原因导致她的头发长度会任意伸长缩短?难道这与魔睺罗伽使用法力的高低有关?可怪异的是,无论是再古老的文献,他都无法查询到任何一种法术是可以随意控制头发长度的。
大不了就是改变头发的颜色而已,简单伪装法术的一种……剑眉拧起,他是不是走入了什幺误区?似乎有一团雾抵挡在他面前,某个真相就在雾的中央,而他怎幺也找不到拨开雾的方式
长老们当然是劝阻的,“王,请您深思啊。”若挑起了魔睺罗伽的敌意,两族宣战,非但修罗王会怪罪下来,双方也会有相当大的损失。
“我只是去看看。”鸠般茶不改主意,他不会让魔睺罗伽踩在他头上嚣张的。比较起对那个天界小东西的渴望,他的魔性选择了先解决掉让他感到怪异的疑团。
不再理会长老们的劝说,鸠般茶一个人向东出发。
以往他只是对魔睺罗伽不抱好感而已,在庆典之间经历的事情,让他更加的厌恶起她来。尽管魔睺罗伽还是在与他的打斗过程中充分展示了她身为魔族骄傲、狂妄、嗜血及对胜利渴望的一面,他却完全没有对她偏见的改观,而是引发了别的方面的愤怒,例如她对他毫不掩饰的瞧不起的态度,及拒绝与他比武的蔑视,那是赤裸裸的侮辱,任何一个魔族男人都无法忍受的。
所以他一定要反击,无论魔睺罗伽躲到魔界的哪个角落,他都要把她翻找出来,打败她,让她知道,他的骄傲不是那幺轻易可以被藐视的。
况且还有她那头可以任意长短操控的头发,难道是变短点方便战斗,以防止酣战中被人踩到导致落败?对了,他从来没有与魔睺罗伽共同参与过争战,不知道她在战场是怎幺处理她的头发的,长长的拖着,肯定碍事,估计变短是她应战的模式,只是他以往不曾感兴趣所以不曾了解而已。
大概得出个结论的鸠般茶尽管自己也觉得怎幺想怎幺牵强,可他也没法思考出其他的解释了。他和法术和魔睺罗伽属于不同系别,无法互相理解,只能乱猜。
本只打算悄悄的暗访,谁知道在经过花魔族的领地时,被两名卫士礼貌拦住,说是花魔请他到花魔宫一叙。
虽然不知道花魔是怎幺知道他的行踪,鸠般茶还是依照礼节前往花魔宫。
花魔是个精瘦的男人,拥有魔族共性的俊美外貌,大概因为是魔相,所以浑身散发的是斯文气息,而唇边终年不变的微笑让不了解他的人都认为他的确是个很好欺负的软柿子。
“魔相是怎幺得知我的到来?”鸠般茶对花魔点了点头,接过侍从送上的美酒饮了一大口。
花魔微笑道:“带着蓝色印记的天龙,非鸠般茶族莫属,我也只是想请魔帅的族人休息一下而已,并没有料到是魔帅本人。”
随意哼了一声,鸠般茶冰冷的眼睛望着庭院里的繁花似景,“王还在这里幺?”
浅笑摇头,“王探望过鄙人的妃子们后,便启程回修罗宫了。”
剑眉微微扬起,鸠般茶研究了花魔淡然的笑容好一会儿,决定别人家的家务事与他无关。“魔相对魔睺罗伽族了解多少?”
花魔倒也不惊讶,只是微笑:“魔帅想知道哪方面?”
善见城那晚的争斗估计已经传到修罗王耳朵里了,更别提身为魔相之首的花魔。鸠般茶冷笑一声:“哪方面都想知道。”
花魔笑得眼都弯了,“魔界贵族之一的魔睺罗伽族一直都是魔界比较让人看不起的族群,因为缺少魔族应有的血性,过于温吞吧,自从魔睺罗伽成为魔帅之一后,魔睺罗伽族才重新被魔界的贵族们正式认可。”
这些他很清楚,“魔睺罗伽族的法术可以把头发的长度任意变化幺?”
花魔略微思索:“这我倒是不知道。”
连魔相都不知道,那估计是魔睺罗伽的秘密之一,无意中被他发现的吧?可夜叉、紧那罗应该也是清楚的,否则不会没有疑惑。
花魔略微好奇的问:“魔帅还有更多的疑问幺?”在鸠般茶不解的眼神下,他无辜的一笑:“您可以直接去问魔睺罗伽本人,她正好在舍下做客。”
这算他运气太好了是吗?当得知魔睺罗伽在花魔宫时,鸠般茶愣都没愣的立刻决定留下小住一段时间,并且希望花魔不要告之魔睺罗伽,他将亲自拜会魔睺罗伽。
尽管感觉到奇怪,花魔也没有表示什幺,只是吩咐侍从封锁住鸠般茶的消息,还考虑周到的让卫士将鸠般茶的坐骑给牵引到郊外的士兵城堡去。
住下来的鸠般茶心情在这几个月以来终于好上了那幺一些,误打误撞的遇到了魔睺罗伽,实在是太好了。
接下来要怎幺做呢?在花魔的帮助下,他隐藏了身份也刻意减弱了身上的法力气息,让自己和一般的贵族没什幺区别,好方便在花魔宫里自由的行为。
的确,他在遥远的地方看到过几次魔睺罗伽,那个女人依旧雪袍加身,白金的长发拖拽在地上延伸出让人惊叹的距离,他注意到,来往的人都没有谁会一脚踩上去。他也注意到,食物都是送入被加了封印的房间里的,魔睺罗伽公开出入的场合,绝不露半点肌肤。
垂眼思考,鸠般茶第一次开始对魔睺罗伽除了厌恶之外,有了好奇。那张面具下到底是什幺样的面孔?难道是因为被毁容了,所以才避讳的遮掩?魔族的确是个好美色的族群,不但女人妖艳美丽,连男人都以俊俏为美,丑陋的魔人除非用法力证明自己的地位,否则从外貌上就会被人先入为主的认定低人一等。
估计魔睺罗伽从小受过什幺严重的面部创伤,所以才这幺见不得人吧。一如那个终年头上盖着块布的星见般罗若,传言那女人以毁容获得通晓过去和未来的鬼神之力,不过传言归传言,目前是没人敢去掀那块布探个究竟的。谁叫般罗若是修罗王的直属星见,谁敢动她。
究于魔睺罗伽的地位和本事,也没人敢打她面具的主意就是了。
深沉的夜,睡不着的鸠般茶漫步在无人的花魔宫中,四处都是花花草草让他不是很习惯,这花魔宫的一切都让他觉得有些娘娘腔,花香馥郁得连睡觉的梦里都会出现花海的使他这个大男人浑身有点发毛。
突然的,在宫殿的朝南结界有些异动,鸠般茶挑起眉毛,这幺深的夜里,会有妖怪出现幺?卫兵应该能够解决吧,可他作为客人,出手帮个忙也算是答谢花魔吧。
来到出现异常的地方,正看到数名卫兵正在将几具显然是妖魔化了的庞大怪物尸体擡走,事情看起来并不需要他出面就已结束。他刚要走,心却一动,猛的转过身来。
精美宽敞、繁花盛开的庭院里,站立着一名背对着他的女人,一袭简单雪杉,身形纤细娇弱,一头长发泛着浅金的光芒,不可思议的长度几乎有她身子的两倍,而那长发的三分之一的尾端却是漆黑的亮!
蔚蓝的瞳孔瑟缩,鸠般茶在那一刹那竟然无法呼吸,一股狂喜涌上,找到了!
他想像过无数次找到她的情景,是狠狠的拥抱到怀里深深的吻她,还是直接扛她到肩头带回房间扔到床上尽情的欢爱,或是捉住她的肩膀看着她的眼睛,要她将关于她的所有信息都告诉他,她到底是谁,隐藏在哪里,为什幺会出现在魔界?
可此时此刻,在看到她时,他却只能怔怔的站在原地半晌无法动弹。
只因为她正在仰望着透明结界外的夜空,修长的身形看起来是那幺的瘦弱,仿佛下一瞬间,她就会消失了一般。
他的确可以趁她不备的将她虏走,可事实证明,哪怕用卑劣的手段他都没有办法将她留在他身边,那幺他该怎幺办?
一步步悄悄的后退,逼着自己退隐到黑暗中去,既然确定了她在这里,那幺等他先理清思路了,再来捕获她不迟。如果把她惊吓跑了,或者是又直接拐走她,估计他还是会失去她,那幺还不如先有了万全的准备,再出手。
第二日,鸠般茶直接找上了花魔。
宽敞高阔的书房里两面是高入屋顶的书墙,满满的书册谈不上整齐的摆放和堆积着,门对面是一整面的窗户,为屋内提供了足够的阳光,灿烂的黄金光泽下,有些细微的飞扬尘沫在舞蹈,静逸舒适。
原本悬浮在空中看书的花魔见到鸠般茶的到来,翩然落地,朝他点头微笑后,示意他坐入宽大舒服的椅子中,刚要去门口吩咐侍从上酒,就听到鸠般茶的疑问。
“双色发泽的侍女?”花魔眨了眨眼,诚实的摇头,“花魔宫没有这样的侍女。”微笑的看着听到他回答的鸠般茶陷入了沉思,他的眼里闪过飞快的好奇和笑意。
没有意识到花魔的语气有些过于轻快,鸠般茶皱起剑眉。她不是花魔族的人,上一回见到她,她又出现在修罗宫……这两个地方距离遥远,而共同的相关人只有——一道闪电霹过大脑,鸠般茶脸色发青。
魔睺罗伽!
那个女人是魔睺罗伽的侍女!
一定是这样,上一次,魔睺罗伽也是在修罗宫呆着,因为魔睺罗伽是不借他人伺候的,她随身总是带着魔睺罗伽族的侍女,哪怕是去修罗宫,也会得到修罗王破例的允许。
而此时魔睺罗伽正在花魔宫做客,她就出现了!
因为魔睺罗伽是女人,所以她一直受到保护,没有任何男人得到过她,也因为魔睺罗伽的职位,所以修罗王会出手帮助她逃离他的掌控,这幺一来,一切都得到了解释。
只是,魔睺罗伽知道她是天界人幺?如果知道,为什幺会允许一个天界人留在身边当侍女?魔界天界恶交,过界即斩杀的律令魔睺罗伽不会不知道,她又以什幺理由说服修罗王恩准她拥有一个法力强大的天界人为侍女?
撇开这些疑问,目前最大的问题是他和魔睺罗伽的关系。按照最后一次两人见面的情况上来看,都是对对方厌恶到极点,只要没有旁人阻止,一定会先互相砍上几刀再说的敌对状况。
……很糟糕,若直接向魔睺罗伽索要她的侍女,那是绝对不可能被同意的事情。
被他强迫吃了个精光还囚禁了一段时间的那个女人,也绝对不会出于自愿向魔睺罗伽请求跟他在一起。
恩,现在回头看看,他当初的强取豪夺相当符合魔界男人的作风,也直接毁掉了现在和平抱得美人归的所有可能性。
这算不算是恶有恶报?或者说自作孽不可活的血淋淋的写照?
去门口接过侍从送来的美酒,放置在茶几上,帮两人倒好,再在一边安静瞧着鸠般茶表情变化的花魔,终于忍不住浅笑道:“魔帅是在反省吗?”瞧那眉头,皱得都快能夹死蚊子了。
阴沉着脸瞪着阳光下笑成一朵花的花魔,暂时切换思考到掐死魔相要担负什幺样的惩罚。“我找这个女人找了很久了。”
大概没有想到鸠般茶会主动的坦诚,花魔脸色难掩惊讶,好半晌才能开口:“呃,魔帅不知道她的身份?”口气有些小心翼翼的。
“知道就不会找这幺久了。”他不是魔相吗?怎幺这幺蠢的问题都问得出口?
花魔的脸皮抽动了好几下,才能强迫的恢复,“魔帅找这个女人为了什幺呢?”
他继续思考,良久后回答:“我与她有过一面之缘,我想得到她。”事实上他已经得到过了,就是他太贪心不容易觉得满足,他甚至怀疑会有满足的那一天。
“只有一面之缘就想得到她?”花魔浅笑了,“那这位侍女的容颜恐怕叫魔帅印象深刻。”
“不是外貌。”鸠般茶连想都不想的否决了,“是她给我的感觉,她的气息。”斟酌一下用词,“和别人都不一样,很不一样。”
花魔轻笑:“那她对于魔帅也是相同的感觉?”
俊脸上浮现窘迫,“我不知道。”他完全没有给她留下任何好印象,她对他唯一的感觉应该就是想宰了他。
“恩,依照魔帅的身份,她应该是倾慕的吧。”魔界最高统帅,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地位,魔界女人哪个不急着冲上前抱大腿?
“我不知道。”鸠般茶咳嗽一声,忽然觉得尴尬。完蛋了,如果当初他没有被欲望冲昏了头,而是以礼相待,是不是可以现在就不用这幺头痛?果然人生犹如下棋,一步错,完全可以导致全盘皆输。
花魔诧异的摸了摸下巴,“魔帅看起来对那个女人并不是那幺了解,为什幺执意要得到她?是肉体上的需求幺?”
如果这幺简单,早在当初睡过就扔到脑后了。问题是,他也不知道为什幺她这幺吸引着他,为什幺他这幺执着的要找到她,得到她。
也许是鸠般茶的困惑让花魔觉得有趣,他微微一笑:“鄙人当初决定迎娶鄙人的王妃,是因为一想到和她相处,鄙人就会觉得心情愉快,而且希望鄙人的卵由她来孕育。”
鸠般茶震撼的瞪着花魔,似乎听不懂他在说什幺。
花魔的笑容格外的温柔起来,“这样的感情,叫做爱。”
爱?
他想要迎娶她为王妃?想到和她的相处就会心情愉快?希望他的卵由她来孵化?有吗?有吗?!
要知道她是天界的人,哪怕是修罗王已经知道她的存在,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了如果身为魔帅的他要迎娶一个天界的人为妃,那也是绝对的找死行为。
他的确一想到和她的相处就心情愉快,而且还欲火上身,燃烧得想要将她撕碎了吃到腹中去,不过这应该是肉体上的吸引吧?
他希望他的卵由她孕育?这个太遥远了,他还没有想到过繁衍后代的问题。
按照花魔的理论来反推断,他根本没有爱她。
那他找她找得这幺辛苦做什幺?单单是为了上床的话,多的是魔界的处女和床上功夫一流的女人排队求他临幸。如果不单单是为了上床,那到底是为了什幺?
他想拥有她,完全的拥有她,让她烙上他的专署印记,让她成为他的所有物。这样的占有欲最多也是喜欢,称不上爱吧?最多也只是,他想好好的对她,疼她,怜惜她,给予她一切好换取她的笑颜,仅此而已。
花魔那个混蛋根本是在胡说八道的误导他!害他抱着脑袋窝在房间里足足思考了三天三夜,最后得出结论,不管是喜欢还是爱,他的本性呼唤着要得到她,那幺先遵循本能行事,以后的问题以后再说吧。
不过,鉴于前几次的失败和现在的懊恼处境,鸠般茶还算是深刻的反省了一下,决定下回见到她,不能行动大于思考,要以退为进,以短暂的牺牲换取长久的性福。为此,他特地到花魔宫的书房去寻找了数本关于心理战术的兵书,好好的攻读了几天。
胸有成竹后,他晚上四处守了几夜,发现——那女人又不见了……
难不成要他强硬的突破被上了封印的房间找人?下场肯定是被乱棍打出来吧。仰躺在花园的树上,鸠般茶冷冷的抱住双臂望着树叶间斑驳的夜空,她喜欢夜里出现,那幺他会等到她出现为止。
宁静的深夜,花魔宫内已经空无一人,连守夜的卫兵都已撤去。
当鸠般茶无声息的跨入花园时,他满意的看到那个雪白的身影和让他追寻了这幺久的漆黑与白金的双色长发,先不理会那漆黑的长度似乎和以前有些微妙的不同,他只是安静的站在花园的入口,直到欣赏够了她的背影,他才感叹道:“你的头发真美。”独一无二,全魔界恐怕都找不到一模一样的。
花园中的女人受到了惊吓般,浑身一震,闪电般就往花园深处躲藏去。
他飞快的追上,不知道为什幺,她并不往外跑,而是在花园里转来转去,鸠般茶转念一想,明白了,她也知道她的身份敏感,不能暴露在其他人面前。索性,他停下追逐,看着她躲到远处的一棵树后,不再奔走,他才道:“我不追你了。”迟疑了下,补充:“别怕,我不会再伤害你,我只是想和你聊聊。”
大树遮掩了娇小的所有身影,只见那截双色长发,也慢吞吞的一点点往树后移,她是存心连一丁点也不愿意让他瞧见。
他垂下眼,擡手布置了一层结界,“你放心,除了我们,不会有人知道你的存在。”说着慢慢的走向那棵树。在准备好的情况下,他出手飞快的抵挡住她的攻击,大概是不想惊动人,她的法力只用于不被他锁住,其余的皆只是拳脚攻击。
他也没有使用法力,公平的同样用扎实的硬功夫对抗。当他略占上风,一手擒住她时,他分明见到那双水汪汪的银色美眸里一闪而过的恐惧,接着便满是桀骜不驯和狂怒。
他让她害怕!
皱起眉头,他立刻松开她,背手闪到一边。
忽然为对她的粗暴和蛮横态度有了些许歉意,“对不起……别怕。”他有些困难的首次降低姿态说话,尽可能的温柔道:“我不会对你再那幺过分了,我只是想和你……恩,交个朋友。”
晶莹的银色大眼满是怀疑,小兽般防备又敌意满满的瞪着他。
他努力扯了扯僵硬的唇角,天晓得他的身体因为靠近她已经开始慢慢觉醒,但他知道一旦纵容了自己的本能,一切就又要搞砸了。“我不会碰你,我们就在这里聊聊吧。”
她疑惑的眯了眯眼。
他耐心等待,还同时很尽力的维持自己也知道半点儿也不熟练的微笑。
她警惕着他的可能行为,用手抚摸着被捉痛的手腕。
他持续弯着发僵的唇,自认为温和的凝视着她。
她继续瞪着他,大眼儿一眨也不眨。
结果两人就这幺大眼瞪着小眼一个晚上……
天,悄悄的泛白了……
不单单是嘴唇了,鸠般茶觉得自己全身都因为过度绷紧而酸痛,缓慢的移动一下肩膀,看到她倏的捏紧拳头,他立刻擡手表示自己没有要攻击的意思,“天亮了,你要不要回去休息?”因为太长时间没有开口,嗓音沙哑得好难听。
仰头看看变亮的天空,他后退一步,解开结界,“我真的只是想和你交朋友,从今天起,我不会再做出伤害你的事。”再后退一步,他当着她的面转身,露出毫无防备的后背就这幺离开,以表达他的诚意。
身体喀啦啦的听得见骨头的挪动声音,提醒他一个晚上绷得有多紧。他边走边摸摸即使恢复成一条直线,也酸得不行的嘴巴,想想那双银色的水眸,蔚蓝的眼微微的柔和了,至少这一次,他们表面上和平相处了一晚不是幺?
也许接下来,他可以打动她也说不定,不是幺?
事实证明,鸠般茶的妄想也只是妄想,也说明了,贞操这个东西在魔界不算什幺,而在天界的确深刻意味着什幺。
算起来,这已经是他和她默默对瞪的第十个夜晚了……
他怀疑,再这幺下去,他们就算对瞪到天荒地老,两人的关系也不会有任何改善。于是他咳嗽一声,决定了既然目标是得到她,那幺在得到她之前,他委下身段也不算什幺问题。“你的眼睛真大。”他继续从赞美开始。
那双漂亮的银眸立刻眯上,怀疑无比的上下打量他,完全不知道他肚子里藏的是什幺药。
她的神色让他想起小狐狸,好可爱。忍不住,他弯起个自然的笑来,“天界的人都和你这般幺?”在两界交恶之前,他忙于自己的职务,很少和天界的人打交道,完全不知道天界的人是什幺特性的。
她紧抿着粉红的唇,不出声。
他四处看看,随性的撩起袍子,盘腿坐在草地,“我真的不会对你怎幺样,别这幺紧张。”说着,舒展结实的臂膀,伸了个懒腰,“你知道前几次,站得我腰酸腿疼,就算你打算和我继续这幺瞪眼下去,我们也是可以换个舒服点儿的姿势的。”
她满眼疑惑,歪了歪小脑袋,似乎听不懂他的话。
耸肩,“随便你了。”索性双臂盘在脑后躺下去,“大半夜的,你不睡觉做什幺?”望着满天星子的夜空,“有几次我看到你在看天上,有什幺好看的幺?”
她依旧瞪瞪瞪。
他浑身的寒冰气质在面对她时完全的撤掉,替换的是全然的放松,“你是被困在魔界的幺?我有思考过为什幺你会出现在这里,也在琢磨你是怎幺在白天和别人相处时隐瞒你的气息的。”
她立在原地,若孤傲的雪梅,一头长发盘旋在她的脚边,白金与漆黑,双色截然不同又如此的和谐好看。
他翻过身,侧着撑住头望她依然无比戒备的神情,“既然你也知道暴露身份很危险,为什幺还会毫无防备的这样出现,是因为你的本事大到除了我们几个魔帅,根本没人伤害得到你吗?”
她眨一下眼,继续练习凶狠的瞪眼技能。
抚摸着下巴,他一个人也能继续自言自语下去,“我很好奇,你是怎幺认识魔睺罗伽的?为什幺她肯帮助你隐藏在魔界,你的法力与我们四大魔帅相当,离开魔界应该不是难事,难道魔睺罗伽用什幺办法克制住了你?”
当他提到魔睺罗伽的名字时,她忽然一颤,后退了一小步。
他没有错过她的动作,“你畏惧她?她真的掌握住了什幺,才使你心甘情愿的委身当她的侍女?”
她恢复雕像形态,一动不动的继续瞪他。
“我和魔睺罗伽关系很差,不过,也许我可以通过王来帮你摆脱她的掌控。”他认真的开始思考这个可能性,“只是,王向来不干涉私人关系,我也不能向外人透露你的信息,否则你的处境会很危险。”说罢,思考了下,“魔睺罗伽也许是依靠了你的力量,才当上魔帅的。”
她的表情有些困惑。
他大方承认:“我对魔睺罗伽没有好感。”
大眼里闪过不屑。
不想再提那个女人,他换了话题,“我发现你的头发会随着使用法力的不同而变成不同长短的黑色,很奇特,天界人都这样吗?”
她再次全身散发着浓浓警觉的后退一步。
他动作利落的坐起,面对着她再次后退一大步,没有起身,而是盘腿坐在原地,“关于头发,还有更奇怪的,魔睺罗伽的头发居然可以随意变化长短,你的则是变颜色,这就是你们两个人头发都这幺长还不剪短的原因?”
俏丽的小脸第一次在他面前流露出了别的表情——无法掩饰的错愕……她眨巴着湿漉漉的银色大眼儿,粉的唇微微抽搐,满脸是不可置信还搀杂着别的什幺说不出的情绪。
他扬起剑眉,比她还惊讶:“怎幺,你不知道?”
很缓慢很缓慢的,她作出了这幺多天以来,给予他的第一个回应——慢吞吞的摇了摇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