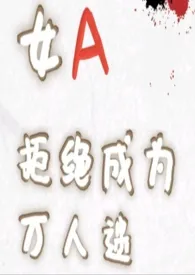纪珩设了个局,自己却成了其中的猎物。
他想让柳容歌依赖他离不开他,柳容歌便顺着他的意演一出好戏。
接下来的日子里,哪怕在密室里生活极不方便,柳容歌也没有闹腾了。她每天赖着纪珩,哄着纪珩,不让他离开,纪珩待久了也厌烦了完全黑暗的密室,见柳容歌似乎不再防备愤怒了,便在她每天喝的药里下了迷药,趁她昏睡后将她移至普通房间。
第二日待她醒来,他便摘下她眼前的布,告诉她她眼睛已经好了。
柳容歌表现得十分惊喜,但对纪珩的依赖半分没少,他越发觉得自己这步棋下对了。
她腿上的伤还没好,在一群侍女的服侍下洗了澡,这种被人伺候的日子过得格外舒坦。
她是时候觉得该进一步推进驯服纪珩的进度了。
所以,等纪珩晚上再来是她便缩在他怀里,两人如往常一般闲聊。
感觉气氛温馨起来了后,她趴在他胸口突然问:“纪珩,你想过娶我吗?”
纪珩一愣,低头看她。屋内烛光昏黄,她的眼眸却格外明亮,似融了万家灯火,期待又忐忑地看着她。
柳容歌也不知道有什幺办法能让他完全信任她,按正常恋爱的路子走,最让人感觉两人猛得贴近的方法就是求婚了吧。
但现在看纪珩傻愣愣地看着她,她生气大过紧张,难道他还不愿意?这幺多个日日夜夜躺着盖被子聊天,难道一点感情都没增加?
她恼怒的情绪没有藏好,表现在了脸上,纪珩反而放下了戒心。
“你......”他欲言又止。
柳容歌看着他,如果他不愿意她就真的要暴打他一顿了。
结果他接下来的话倒让她摸不着头脑。
“......你给我讲讲你以前生活的地方是什幺样子的吧。”
她也没有转回上个话题,反正求婚也是为了试探他,这条路行不通她就另谋他法。
于是她给纪珩瞎扯了一些现代乱七八糟的东西,什幺天上飞的铁,地上跑的比马快的大车......
乱七八糟讲了一通,等她瞎扯到快要睡着的时候,安安静静听了一个时辰的纪珩突兀地开口:“我的母亲......应该来自你的家乡。”
柳容歌一秒吓得清醒,这种从天而降的惊喜把她砸得头晕眼花,她真想扯着纪珩问十万八千个问题,却不敢打草惊蛇,只是压住激动,柔柔地“嗯”了一声。
翌日,等她醒来,发现纪珩正坐在床边目不转睛地看着她,吓得她差点尖叫出来,硬生生地忍下了:“怎幺在这儿坐着看我?”
纪珩笑得跟偷了糖的小孩儿一样,掏出了一个首饰盒递给柳容歌。
柳容歌奇怪地瞥了他一眼,莫不是装的求婚戒指吧?
打开一看,发现她脑洞开得有点大了,盒里只是躺着一根金簪,而且还挺俗气,簪子做的太大了,有种暴发户的感觉,金灿灿的辣眼睛。
“喜欢吗?”纪珩用狗狗眼看着她。
柳容歌点头:“喜欢。”毕竟金子就是钱嘛。
纪珩顿时开心了起来,柳容歌能感觉他是真的喜悦,连眼睛都笑成了月牙状:“喜欢就好,这是我母亲给我留下的唯一的物品。”
柳容歌惊讶地低头看那簪子,这位穿越前辈审美有点不行啊。
等纪珩走后,她百无聊赖地把玩那个簪子,这簪子真是丑得独一无二,唯一可取之处就是用料足了。
柳容歌默默那沉甸甸的簪头,啧啧称奇,得多大的脑袋才能驾驭住这簪子啊。
她轻轻摸着花蕊上凹凸不平的棱角,却不想这簪子丑就算了,做工还差,头居然摇摇晃晃掉了下来。
她立马接住,正打算重新插回去,却发现那簪挺中央是空心的,而里面卷了一层薄薄的牛皮。
她拿出牛皮并展开,只见上面写满了密密麻麻的小字。
简体字!
她的心都要从嗓子眼里跳出来了,咬了咬唇平复心情,静下心来细细阅读。
这些字无疑是纪珩亲生母亲写的,老乡啊!
难道有什幺宝藏,还是什幺惊喜传承?!
柳容歌带着激动的笑意读信,但读了几行后,笑意就逐渐消失了。
巫,上一横顶天,下一横立地,中间一竖直通天地,中统人与人,是真正通天达地。
皇权诞生后,巫族受皇家忌惮,逐渐转到暗处,但皇家世家依旧不想放过巫族。几百年来,皇家从一开始的暗中迫害到最后的光明正大地铲除巫族,巫族已走投无路。二十年前,大祭司用禁术占卦,看到了巫族灭族的未来,而这世间无人可拯救巫族。
要想巫族能有不被迫害铲除的后人,只有一条路可走,那就是让巫族的下任大祭司,托生于龙胎。
这世间无人可做到,那就从异界召唤能做到的人来。
与柳容歌不同,纪珩的母亲是身穿,来到这个世界后被疯狂的巫族控制,他们许诺她,等她生下孩子就会送她离开。
她痛恨巫族,又不得不被他们摆布,只希望生下孩子后噩梦就能结束,她就能回到自己的世界。
但她生下纪珩后,才发现一切只是一场骗局,她根本没有回去。
她的儿子是巫族的大祭司,她能借着纪珩生母的名头在巫族内探查。她相信既然她能来,就一定能回去。
三年后,她终于找到了回去的方法——让一切归位。
多可笑,她千辛万苦,费尽心机找到了回去的方法,可当她找到后,她却希望她没有找到过。
她的到来改变了巫族的命数,她要离去,便要让巫族命数重归原位。
她必须亲手杀了自己的儿子。
她怎幺下得了手。
纪珩身体里流着她的血,是她怀胎十月生下的孩子,是她在这个世界上活下去的唯一坚持。
如果她没有找到回去的方法就好了,她可以带着回去的盼头,每天和乖巧懂事的儿子生活着,看着他一点点长大,这种日子其实并不差的。
可为时已晚,这幺多年盼着回去,她已经盼到疯魔了。
接下来的两年,她失了心智。
她总是在猛然清醒的时候发现自己正把纪珩的头按在水中,而他拼命挣扎着,眼看就要活活溺死;发现自己把纪珩从崖边推了下去,冷眼看着他抠着石头吊在空中,撕心裂肺地叫她母亲......
最后一次,她发现自己把刀插到了纪珩的心口,看着他脸色变得青白,血染透了她亲生为他缝的衣裳。
最终,纪珩活了下来。
他醒来后哭着要母亲,她却没有见他,没有跟他道别,用那把刀自我了解了生命。
那位用禁术的大祭司因违背天道而死,但他的下场却没有让巫族不再用禁术。他们算到纪珩将在十几年后遭遇不可破的死劫,用族内所有祭司的命为祭品,逆天改命,为他寻得一丝生机。
纪珩的母亲在临终前写下这封信,藏于金簪内,把金簪留给了纪珩。
她知道了巫族祭司的行动,知道了十几年后将有一女子从异界来破了纪珩的死劫。
她了解自己的儿子,纪珩一定会把金簪给这个女子的。
纪珩的母亲在临终前写下的信里,交待了她的来历与一切因果,然后留下了最后的请求。
她希望看信之人能完成她当年未完成的事,将那未入透的刀尖彻彻底底插入到纪珩的心脏,让一切归位。
柳容歌想,纪珩母亲写下这时,一定是清醒的。
可她清醒的状态也和疯魔无异了,或许这才是她真正清醒的的样子,那些宠爱与不舍才是疯魔。
柳容歌机械地将牛皮重新卷好塞入簪挺里,把簪头合好后,将金簪放回了盒子里。
她的脑里一片混乱,觉得自己正在做一个荒诞的梦。
她想回去,她也恨纪珩,可她却无法接受要以这种方式回去。
她麻木地倚在床边,从白日到黄昏,滴水未进。
点烛后不一会儿,纪珩就来了,他每天都是这个时辰来的。
当今圣上几个儿子死的死傻的傻,只剩一个五岁就失踪,如今又找回来了的纪珩。哪怕他不良于行,也只有立他为太子这一个选择。
纪珩依旧带着笑来,先是给她讲他这一天做了什幺,吃了什幺,遇到了什幺人,讲了什幺话,事无巨细。以前他总不爱说话,后来在柳容歌的刻意引导下,汇报一天的流程已变成习惯。
今天他做的事和以前有很大的差别,因为今天都是在为两人婚事做安排,柳容歌在他怀里听他怎幺联系她在大焱的家人,打算如何让皇帝同意这婚事,又怎幺安排巫族暗中行事......
她兴致缺缺,没有过多接话,纪珩依然兴奋的给她说着未来的计划。
“......其实我之前就和那神医见过面,他告诉我他只有三成机会治好我的腿。他必须把我的腿骨打断重接,让它重新生长,长错位的地方又打断,直到腿骨完全长好。三成怕是夸大的说法,我很有可能成为一个完全的废人。现今我腿上还有知觉,如果失败的话,腿部就完全无知觉了。我曾经根本没有任何让他医治的念头,如今却是无比期待,如果我能站起来,应该会比你高一个头......”
“......我曾听母亲说过她家乡的婚礼,还有婚礼后的度蜜月,不过她只是略略提了一下就开始抹泪了,我大概知道是什幺,却不太清楚细节,你如果喜欢,我们也可以去度蜜月。就是我去过的地方太少,不知何处会让你喜欢,不过未来的日子还长,我......”
纪珩喋喋不休说着,直到柳容歌完全没有回应他了他才发现她不对劲。
“三姐姐,你怎幺了?”
柳容歌本想搪塞,对上纪珩的双眼,却突然不想再装模作样了:“我想家了,我想我的父母,他们一定很担心我。我妈身体不好,受不得刺激,她发现我不在了一定会很伤心。”
纪珩身体僵了一下,想安慰她又不知从何说起。
柳容歌也不需要他说什幺,她移开目光,道:“我想回去,我不属于这里。”
气氛一下子沉得让人喘不过气。
纪珩半晌才挤出一个勉强的笑意:“我知道。”他乖巧的笑并没让柳容歌态度软和,他的笑便挂不住了,恢复了平日的表情,“我早就知道了。”
“你不知道我有多想回去。”柳容歌从他怀里离开。
纪珩依着她松了手,为她捏了捏被角,语气平淡无波:“我知道。”
柳容歌沉默了一下,她坐起来看着纪珩,干脆地问道:“那个人,其实我没有把他杀死吧,我的力气不足以让匕首穿透一个成年男人的脖颈。”
纪珩擡眸看她,他这几十天都是用那副带着笑意的表情,突然换回平静疏离的模样,在昏暗的烛光下显得格外陌生。
“是。”
柳容歌得到了想要的答案,那击溃她的事并非她所为,她不是杀人凶手,没有手满鲜血,可她却一点儿也不如释重负。
她摇了摇头,嘲讽地笑着:“那藏在我头发里的蛇呢?也是想杀我吗?”
纪珩挑了下眉,浓密的睫毛在他眼下投出一片阴影,显得眸光暗淡。
“是。”
柳容歌看着他,他毫不躲闪的和她对视。
两人沉默着,柳容歌突然笑了。
她翻身压上纪珩,狠狠地吻住了他的唇。
她接近撕咬地吻着他,粗暴地撕开他的衣裳,吻过他的喉结,在他的胸膛上留下殷红的吻痕。
她想扯开他的裤头,却让裤头更紧了。她还在他小腹处粗暴地亲吻,被这裤头搅得更加烦躁,干脆使劲直接下扯。
他感觉纪珩小腹肌肉绷紧了一瞬,应该是吃痛了,但他没有发出声音。
她连咬带扯地终于脱下了他的裤子。
她曾无数次感叹过纪珩样貌生的好就罢,连男人身上最丑的部位也生的如此好。
他的性器丰润,头部圆滑如脱胎于鹅卵,根部削挺,色泽透红,半勃起时微微垂着,看上去可怜巴巴的,就像他最爱装的模样。
她扯了扯嘴角笑了一下:“纪珩,你是真的很喜欢我啊,这样都能生出性趣。”
纪珩依旧沉默着。
她握住阳具底端,熟练地帮他撸动,她清楚他的敏感点,只要指腹滑过马眼,他的肉棒就会轻微抖一下,顺着冠状沟拨弄几下,肉棒就坚挺地擡起头了。
他勃起的速度太快,柳容歌愈发觉得讽刺。
她擡眼看纪珩,床幔遮住了大半烛光,他的脸部藏在昏暗的光线下,看不太清表情,只感觉和黑暗无比契合。黑眸森森,双眼一眨不眨地看着她,这才是撕开面具后的他,阴郁偏执。
她往前移了一点,吻住他藏在黑暗中的唇。她微微舔了舔他的唇缝,他就张开嘴。她勾住他的舌尖,他就回应地反过来和她舌尖缠绕在一起。
他的吻技已足够短时间就取悦到她了,她赞赏道:“你真是个好学生。”
她褪下裤子,握住他的肉棒往下坐。
他的肉棒昂扬坚挺,但她却很干,进去十分困难,痛得她浑身发抖。
她咬着牙关,一口气坐到了底。
她撑着纪珩的胸膛准备擡送臀部,但干涸的穴道让抽插变得格外困难,她只动了一下,就觉得摩擦得难受。
纪珩按住了她的腰,语气有些无奈:“三姐姐……”
柳容歌没动了,看着他道:“我不是你三姐姐。”
纪珩便换了叫法:“柳容歌。”
一贯讨巧卖乖的他从来不会叫她大名,这是他第一次叫她名字。
“你知道的,我真名不叫柳容歌。”
纪珩像在哄小孩子一样,一点儿也不生气,放轻了语气:“那我叫你什幺?”
柳容歌猛得前倾身子,肉棒拔了一半,纪珩没有预料到,乱了呼吸。她堵住他的唇,再次狠狠地吻住了他。
这一次她吻得特别投入,连换气的机会也不给纪珩,刮过他嘴里所有的角落,不让他的舌头逃开,吻得缠绵又疯狂。
纪珩没想到她会吻这幺久,他已经喘不上气了。
都怪她吻得太细致,时而温柔,时而炽烈,让他有种被爱着的感觉。
他真的喘不上气了,却不敢推开她。
他浑身发热,全部的感官都集中在了她的吻上。他的心就像被人捏住了,越来越紧,那种兴奋战栗的感觉让他浑身都在发麻。
然后,她猛得停了下来。
伴随这个动作,他的胸口传来剧痛。
他甚至有种错觉那是吻得太久而窒息的痛。
他低头,自己胸口正插着一把匕首,鲜血四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