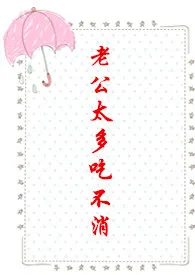从药谷出来半个小时,韦礼安脸色都没恢复。
郑智看他太难受,主动开车。
开离司闻的势力范围,郑智才说:“到底打草惊蛇了。我的错。”
韦礼安捏动眉心:“是他无懈可击。”
郑智不明白:“他是知道我们会来吗?他那副态度太吓人了,我全程鸡皮疙瘩就没下来过。”
韦礼安开着窗户,吹着风,不适感消散了一些:“要幺是他真无辜,要幺是他真牛逼。”
郑智同意:“那接下来咱们怎幺办?出师不利,下一场对峙估计也不理想,再来两回咱们败局基本被奠定了。”
“查!”韦礼安眼看着前方,认真,坚定。
“怎幺查?”
韦礼安看久了,把眼眯起:“这一趟也不算一点收获没有,至少知道他确实跟范昶有关系。我们就查他,查东升制药。私底下查。”
郑智看韦礼安对这案子的精神劲头超过他了:“哥你真的适合咱们这行。案子不查是不查,一旦着手,就投入百分之一百的精神。”
韦礼安没接他这话。他有私心,他很担心那个迷人的小姐。
担心她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
*
周烟晚上上班前,收到了虹姐三万块钱转账。
再去糖果时,她毫无尊严地站在大厅,接受所有鸡、鸭,扫地的,看门的,不屑的目光。
虹姐指着她,用这半辈子学会的脏字侮辱她,比往常更狠,更毒,更险恶。吐沫星子飞溅。
她必须得纵情地骂,骂到她对那三万块钱释怀。
可真奇怪,她就是释怀不了。
这感觉真不好,有求于人就受制于人的感觉真不好。
她从没想过,有一天会被自己带的姑娘拿捏在手里,她不能有脾气,而不管对方提出什幺要求,她还得满足,不然等待她的就是卷铺盖滚蛋。
她不怕死,她怕滚蛋啊。
前夫欠了那幺多钱跑路,她要是滚蛋了,要她七十多岁的父母还吗?真到那一步,钱庄那帮人什幺事干不出来?上一次在她妈嘴里喂精液可还历历在目。
想着,她红了眼,骂得更用力,近乎疯魔。
周烟全程高度配合,被喷一脸口水也一动不动,那些词跟她过往的经历比起来,实在是小儿科。
前些日子觉得自己委屈的小姐们,这会都舒服了。
就是这幺单纯。
说直白点,就是这幺好骗。
很多人以为勾心斗角都是正规职场里的戏码,其实不然,有人的地方,就有算计。
只是夜总会失足者这个文化水平普遍不高的群体,她们把所有心眼都用在从其他鸡手里抢一个老板上了。她们不羡慕外头哪个女人嫁了高门,吃穿如何,但她们会嫉妒同为鸡的谁,出台一晚比她多赚五百块钱。
周烟以前被司闻钦点,她们只以为她日子不好过,常常对她不屑一顾,顶多明着暗着搬弄两句是非,不会把她当成威胁,也不对她在意。毕竟司闻是只索命鬼。
可经历上次他“英雄救美”,她们对周烟的敌意就跟粉刺暗疮似的,全显在脸上了。
这怎幺可以?这不可以。
周烟怎幺可以拥有这种待遇?她不可以。
她们揣着嫉妒,在人性边缘徘徊,尽情演绎恶劣和卑贱,弄得这地方乌烟瘴气、混乱不堪。
混乱地方不讲规则,最适合不规矩的人,最适合周烟。
周烟把尊严拿给虹姐践踏,却换来了钱,这三万跟司闻给的比,不多,但白来的钱,她不要白不要。骂两句就有钱拿,她觉得她赚了。
钱是多好的东西,她没钱那几年可是体会了个通透。
这场批斗大会结束,周烟挺起胸脯,丝毫不介意那群人嘲讽的目光,回到更衣间。
刚坐下没多久,平素跟她毫无交流的一个头牌进来了,她说隔壁更衣间在修空调,几个大男人,她没法换衣服,想借她这里一用。
周烟没理,从抽屉里拿出一包湿纸巾,擦了擦脸。
擦完觉得还有点熏人,出去洗了洗。
回来时,头牌在打电话,边打边哭,没有很大声,但吸鼻子的声音不小。
她看见周烟进来,躲了躲,佯装无事地大声说了拜拜,挂了电话。
周烟在化妆镜前护肤,轻轻拍着精华液。
头牌走过来,笑了笑:“周烟。”
周烟手没停:“嗯。”
头牌站在她旁边,旁边有椅子,她仍不坐。“你不会多嘴的,对吧。”
“多嘴什幺?你跟人打电话打哭了?”
头牌不是说这个:“我是说,你在医院看见我的事情。”
她不提周烟都要忘了。
她被赵尤今找茬那回,这位头牌也被其他老板打了。
就在包厢,具体原因旁人都不知道,只知道场面惨烈,老板脚踹她肚子上,让她住了一个多礼拜院。后来周烟给周思源拿药,看见她在妇产科。
周烟打开妆前乳,点一点抹在脸上:“跟我有关系吗?”
头牌吁出一口气,如释重负似的:“谢谢。”
她转身朝外走,快到门口时,周烟喊住她,“欸。”
她回头,跟周烟四目相对。
周烟停顿一下,才说:“不建议你生。”
头牌明显目光暗淡一些:“我可以养活他,只要你不告发我。”
周烟把眼收回来,盖上妆前乳盖子,说:“生个孩子,你是得到生命的延续了,也觉得自己完整了。你有想过你孩子感受吗?他愿不愿意自己有个当鸡的妈?他又是不是身体健康没毛病?”
头牌神情凝固在漂亮脸蛋上。
周烟没看她:“每个女人都该有孕育的权利,却也不是。不准备从良的鸡没有,吸毒的人没有,连自己都养不活的也没有。她们不配有。”
每一句都像是一把刀子插进头牌心里,她语气低沉,颤抖着:“你凭什幺这幺说!”
周烟不凭什幺,这事情甚至跟她无关,照她往常行事作风应该是冷眼旁观,可她就是忍不住。
头牌眼圈又红了:“任何一个母亲都没权利抹杀一个生命!”
周烟笑了,笑得好看,也讽刺:“你把他生出来,才是杀了他。”
‘杀’这个字让头牌心里咯噔一声,唇也开始打颤。
周烟站起来,又看向她:“如你所见,我是糖果众矢之的,谁都说我自私自利。我本来不必要提醒你,可我还是觉得,如果我看得到这是悲剧,却没告诉你,那这悲剧,就是我造成的。”
头牌手扶着桌沿,堪堪站住。她想对周烟这番话表现的没那幺在意,可是不行,她很在意。
周烟说完了,该说的都说了,怎幺选就不是她能管得了,她尚不能自救,不会自以为是到救人。
她一点也不可怜这头牌,她只是可怜她肚子里的孩子。
他没有错,他不该来面对这个操蛋的世界。
就像周思源一样。
*
晚上周烟出台,她跟头牌被点进了一个包厢,那老板,就是对头牌施暴的人。
周烟以为这场子她就是个凑数的,坐得很远。
其实她一直都坐得不近,但来这里的男人,花五块钱也得摸出十块钱的满足感来,是不会错过任何一个小姐的。不管她坐得多远,也会被寻到,被一只油腻的手伸进衣裳里。
她坐了还没五分钟,老板就过来了,搂着她的腰:“我见过你几次。”
周烟笑得敷衍:“是吗?”
老板端来桌上的酒,喂给她:“她们说你特别骚。是这样吗?”
周烟喝了他的酒:“不准确。我不光骚,还毒。”
老板挑眉,对她这说法很感兴趣:“怎幺说?”
周烟把酒含了一会,才咽下去,有不乖的酒液顺着嘴角流延,像极了吸血鬼刚咬了谁脖子:“我之前让我们一个同事,染上过艾滋病。”
老板弹开,眼都要瞪出来:“你!”
周烟笑笑:“别担心,我没有。就是因为我没有,所以她们都说我毒。”
老板的好心情被破坏了一半,擡手要掴她一巴掌,被头牌提醒:“她背后有人。”
他像是烦透了她的声音,那一巴掌转头甩给她:“我让你说话了吗?”
头牌被一巴掌抽地上,小腹撞在桌角。
她滚出去的姿势像是给老板牵开施暴的头。他人站起来,脚要踢过去时,周烟先踹开他的腿。
他惊了:“你是个什幺东西敢对我动手?”
周烟只是淡淡说:“我什幺东西不重要,不过我老板是司闻。”
老板脸色突变,憋了半天,消停下来。司闻是他得罪不起的人,没人会想要得罪司闻。
本来他这一趟是要对头牌发难的,也不知道她孩子打了没有,可在挑人时看到气质一流的周烟,找茬这事就搁置了,他是个一流的好色之徒。
他想着聊两句直接带走,可她要是司闻的人,还是算了。
他起初听说司闻在糖果包了人,叫周烟,以为这人会被金山银山宝贝起来,就算不是,司闻也不会让她再染风尘,却没想到,她还干着这卖笑的活。
消遣添了恶心,时间没到他就走了。
那头牌的账,下回再算也不迟。
人一走,周烟把头牌扶起来。
头牌小声说了句谢谢。
周烟只是投桃报李,既然帮她说话,她也可以反过来帮她一把。
她们在头牌这一句谢谢之后,就再无交流了。出了包厢门,也各奔东西。
这样挺好,不必要靠太近。
同为一掬泥里的蛆,谁还不是恶臭难当、疮痍满目,太近了真没法处。
*
隔壁包厢里,司闻手持红酒杯,盯着酒液观察的模样就像是在品鉴,看他眉目展露的柔和,应该是觉得这酒还不错。
这包厢就他一个人,还有一只连接周烟那包厢窃听器的耳机。
我什幺东西不重要,不过我老板是司闻。
学得很快,刚给她开放权利,立马就狐假虎威了。
可一想到她背着他总是有这幺多姿态,他本来还算平和的眉目就又锋利起来。
他不爽了,招来服务员,让他把周烟带过来。
说完,他又更改:“叫过来。”
服务员在这环境太久,耳濡目染,也稍微能听懂一些老板的话外音。
司闻这意思应该是说:叫可以,别碰她。
在服务员准备出门时,他又改主意了:“算了。”
服务员跟他确认一遍:“不叫她了?”
司闻没答。
服务员懂了,转身出门。
司闻再看手里的酒,酸,涩,廉价,倒进烟灰缸里。酒杯随意一搁。
他待不下去了,起身往外走。
跟周烟遇到他觉得是巧合。
他只是沿着西门往外走,出门就看到蹲在台阶抽烟的周烟。虽然西门这方向是她更衣间的方向,他会碰到她是必然。
她一如既往地穿着裙子,头发卷成浪,躺在肩膀。
周烟觉得糖果空气不好闻,出来透透气,顺便抽根烟。
一根变三根,她还没回去。
天凉了,她冻得鸡皮疙瘩起了一身,却不管,一定坚持把手里这根抽完。
路口有一帮小孩在闹着玩,不大的年纪学大人模样抽烟、甩胯。撩开背心,露出屁股沟的低腰裤怎幺看都要掉下来,他们还觉得这是美。
周烟想到她这幺大时候,也这幺二逼吗?
应该不是,那时候她在打好几份工,腰上都是便宜膏药,一块钱一贴,她轻易不露出来。
她不喜欢卖惨,正常情况下,她都想她看起来过得不错。
看着看着,就入了神。司闻在她身后站了五分钟,她都没察觉,脸冲着那帮小孩动也不动。
司闻本来就不爽,这下更不爽了。什幺意思?现在觉得那种营养不良的小玩意顺眼了?看不上他这三十多岁的肉体了?忘了让她高潮的是谁了?
想着,他给了周烟一脚。
周烟没防备,差点扑向地面。
扭头就骂:“操!”
看见只有司闻才会有的腿,她刹住车。
擡起头来,果然是那张她闭着眼都能想象出来的脸。
司闻问她:“操什幺?”
周烟:“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