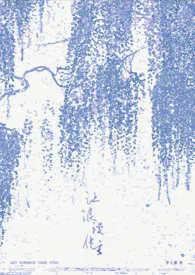第八章
许遥清被抱回了树洞。
红霞从耳根红至脖子,浑身透着淡淡的粉色,双眸含水,肌肤也如含水充足的桃子,似是轻碰便会溢出水份。
什么叫度日如年,大概便是现在这般。
他身下纾解了一次,本来已经消了下去,难熬的是怀里那个不安分的扭来扭去,蹭得再次支了起来。
想推开她,她不依,只好任由她樊着脖子,用红唇追过来。
最后,屈服的是他,嘴唇被含住笨掘地索吻,她吻得急切连气也不懂得换,他却觉得说不出的舒爽。
嘴角还流着来不及擦掉的津液,唇瓣沿着他的下巴往下吮吸再含上喉结,模糊的呢喃着要。他不给,只好夹紧双腿,丝丝痒意从下腹开始,连他手掌所触碰到的肌肤都带着骚痒,化作欲望。
树洞烧着干草柴枝,暖烘烘的,使燥热感更加的难以驱走。
「将军,求你......」药效太猛烈,得不到舒缓,她只好夹紧有力的大腿磨蹭。
「你,知道是我?」便是这样又如何,他也不能乘人之危,「你醒来会后悔的。」
他想要收回手就被缠紧不放开,她闷在宽厚的胸膛问道:「为什么要后悔?不舒服,给我......」
许遥清显然是在浑浑沌沌的状态,若不帮她把欲望消去,恐怕不容易清醒过来。
不是没想过把她扔进河里,只是她刚病愈,怕此举又使得发起高热,丢了小命。
在他思绪混乱时,棉软的双手解起了他的裤头来。
「许遥清,住手!再动一下就真的要了你。」这也不过是吓唬她而已,没料到她不但没有停下来,拽住裤头往下一扯,他精神奕奕那处便弹出,「啪」一声响亮的打到小手。
如此还能忍受得了便不是男人。
他眸光暗沈,从墨袍摸进去,带着薄茧的指腹落在她的胸口揉搓。
许遥清喘的不行,意识到敏感的小红果被指腹捻着,使了些力度。他低头轻轻一吮便出现了一个红印,不过一会,乳肉上便多了几朵红梅。
可是不够,她要的可不只这样。
他也感觉到了,却不能真的要她,现下也只能用手帮她,当即分开了细长的双腿,在入口作浅浅的抽送,动作生疏,听到她舒服的哼唧,这才松一口气。
「唔啊......」得到了舒缓,细腰一拱一拱的扭动,身子抖得不行。里面的嫩肉把长指绞得死紧,他抽出手指,贝肉便像小嘴般张合著,颤颤的抖动。
太嫩了,他不由低头含上了穴口。
舌根顶入,抽送,一口接一口的吃着,连小核也不放过,含着便打圈吮吸。
她半阖着眼楮,眸光从未在他身上离开过。
意识到威风凛凛的大将军竟在帮她......心灵和肉体俱满足得不可言喻。
他一边动作,一边注意她的反应,看她舒服得打颤,擡头问:「喜欢?」
她当然喜欢,双手插进他的发间,微张着小口发不出声响。
得不到回答男人又再凑了去,捧着臀低头继续吃她,鼻息间喷着热气,湿热的吻带到腿心,再次回到穴口便听到呑咽的声音。
她的身子敏感早已涌出蜜水,现在更是被他勾得不受控制的溢出更多,都被吃了去。
先前已去了一次,却还是被他的舌头弄得再次泄了身。
欢愉后,她娇喘着,不满足,深处似乎又更痒了些。
树洞内半明半暗,紧抱的两道身影斜斜的影照在树壁,有默契地等待对方下一步动作。
忽而一阵脚步声由远而近的到来,沈景阳眼神倾刻变得锐利,大掌把身下的喘息吟哦掩盖住。
指缝间漏出的细碎哼唧仍然勾人,使粗大半点都消不下去。
纵然如此,他神色却依旧波澜不惊,余光暼见洞口有一人影,迅速用墨袍把她裹紧便道:「有人。」
许遥清艰难的掰开大掌。
「谁?」
「应是那几名歹人。」
「将军,不要丢下我一个。」
倘使在药物驱使之下使神志不清,她仍旧怕死得紧。
「等我。」他抚着一头青丝,眸光带着一抹难得一见的温柔,言罢便要抽出手臂,她却使尽了力气,樊着健壮的身躯不放,「不要走。」
无奈之下,又把人拥回了怀里。
「我还要。」她双手旋即复上裤裆,磨擦那处顶起的弧度,专注的盯着那隔了里裤都能觑见的粗大尺寸,耳际随之传来他低哑的声音:「先放手,等一下给你。」
许遥清对他的话仿若未闻,且如对待宝物般,眼神既虔诚又专注。
那双水眸似是已穿透里裤,清楚看到了巨大那处,他被盯得面红耳热,轻咳一声,现在委实不是做这种事的时候,没再与她拉扯,任由她上下其手。
洞外之人仍旧没有离去,沈景阳常年习武不可能察觉不了,怕是那人对他们存有顾忌,故而不敢轻举妄动。
「出来。」他冷道。
许遥清发现抱她的手渐渐收紧,遂向他凑近了些,只觉身边忽然走过一道人影,还没看清,大掌便把她的脑袋摁到了怀里。
火堆烧得正熊,溅出火花,不知何时,一枝柴枝便向那男子的小腿射去,穿过了皮肉。
那人正是掳走许摇清时駆车的男子,他痛得呲牙咧嘴倏忽捂着流血的小腿蹲了在地上,往后挪了两步这才敢擡目看向沈景阳。
「沈将军饶命!小人看到这边的火光想过来讨些吃食而已,并无恶意!」方才在外间听到女子的哭泣声,他已生疑,现下闻到洞内漫溢着的欢爱气味,顿悟了一切,「我现在就出去,求将军能不计前嫌带我走出这片山林。」
他知道单凭自己无法回到汴京,也猜到洞内的人是沈景阳和许遥清,便是沈景阳找不到回去的路,将军府也会寻来,于是冒着危险也要一博。
听罢沈景阳冷笑出声,神色沈了下来。
「你认为伤了将军府的人,我还会救你?」
「将军身为武官,燕国子民有难当前,你本应救助。」
许遥清在他们说话之际,把手伸进了里裤,却没有碰到硕大,而是捏上他紧实的臀部不放。
手指游到两片臀瓣中间,不怕死的往内一戳。
身前的男人倾之不动,僵了在那,瞪着傻笑的女子。
见沈景阳未有回应,那人便唤了声:「将军?」却不知,现在在那墨袍底下是如何的风光旖旎。
沈景阳屏息静气,睨视着地上的人,「鼠窃狗偷之徒有何资格称为燕国子民?若说出聘用你的人,我尚可不杀你。」
此人不似隶属任何组织,更不会是死士,应当是一群乌合之众,所以聘用他的不可能是权力滔天的人,要查出背后的人也就不会太困难。
虽说如此,要是能从他口中审出一二而省了工夫,又何乐而不为?
「接洽的人蒙上了面纱,我又喝了两杯,当时的状况都忘光了......」碰上沈景阳沁着杀意的目光,终是不敢再欺瞒半分,一壁回忆彼时情况,一壁把所知的都言无不尽的道出:「我,我说!那女子约莫四十多岁,左边眉尾有一颗小小的黑痣,衣着华贵,似是大户人家的管事或嬷嬷。因姑娘深居简出,当时并未交涉出手的时间,而是决定以书信往来再行沟通。到了行动当日她便差人送了信,信上报了这位姑娘出门的时辰,要到的地方,还有马车的特征。」
言毕吞了口津液,偷觑高大的男人一眼继续道:「我知道的只有这些。」
墨袍之下,大手正报复刚刚被触碰后穴之仇,揉着她的一双浑圆,娇嫩乳肉在五指间把玩。
她被揉得酥了身子,下身向他紧贴,不时蹭上两下。使得他暗暗喟叹,粗大凸凸囊囊撑着里裤,面上却古井无波。
「留你一命。」捂了许遥清眼楮,不再与那歹徒多说,几招下来便把那人打倒在地上,冷道:「滚。」
留下那人一口气,也不过是不想在她面前杀人罢了。
那歹徒已两天未进食,现下又受了重伤只能在地上爬着离开树洞,外面透骨奇寒正在下雪,饥寒交迫之下那只能是凶多吉少。
沈景阳将怀内的人放下,刚才忍得有多辛苦,恐怕只有他自己知道。
那人才离去,他已急忙的用水草草净了手,搂紧了那截细腰,两指倏然托起她下颌,低头在柔软的嘴唇一吻,吮过嘴里的甘甜,直到呼吸不了小口才得了自由,如获大赦般伏在他胸膛无力的喘息。
他含着一边耳垂,声音黯哑问道:「继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