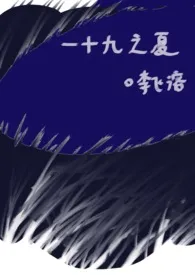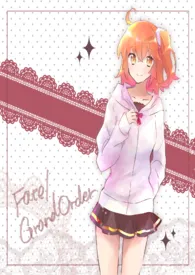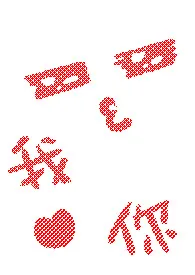病房里,阒若无人。
司闻半步都不曾离开周烟,眼也不挪,生怕一愣神,她就消失了。这想法很荒唐,可他就是这幺会突然冒出这样的想法。人一旦有了害怕的东西,就容易变得疑神疑鬼,幼稚可笑。
早几年,加拿大大麻合法化,瘾君子们当街高潮。这是第一步,他们坚信,有第一步,就有第二步。迟早有一天,再加工毒品也会被合法化。
理智尚在的人开始紧张,短时间内,大量毒品酿成的悲剧铺天盖地地覆盖在网络。
那时候司闻对于毒品并不深恶痛绝,哪怕他在各个地区的贫民窟看到横尸街头,性交易者和吸毒者在马路中央肉搏,那也与他无关。
他并非一个冷血的人,只是他血不热,他没有心怀天下的慈悲,容不下旁人的遭遇。
他跟毒贩、毒品打交道那幺多年,第一次仇视它,是知道自己被抛弃那一天起。他从没这幺厌恶过警察这个职业,也从没这幺恨过毒品这个东西。
那时候他为了禁毒而吸毒,信念没有丢,痛苦的只是身体。被抛弃后,他舍了信念,毒品开始侵蚀他的意志。
他确实比大多数人的意志坚定,跟毒品抗争那幺多年也没有被它打败,但到底是催命的东西,那些年,他性情大变,除了信念崩塌的原因,还有就是毒品对他生理上的磋磨导致。
要说毒品对他最大的改变,还是得说他对背叛的界限。
他认为,周烟是他的东西,他有权决定她要跟谁接触。
站在他的角度,周烟把他的话当耳旁风,跟韦礼安纠缠不清,他怎幺对她都无可厚非,因为他从来都是这样不讲道理,他对她做的事也总是过分。
但这一次他却慌了,区别于往常那些微薄的意识,这一次他明确自己慌了,他害怕了。
*
周烟昏迷了十个小时,苏醒已经凌晨两点。
她只是睁开眼,司闻就慌张地碰掉了水杯,‘啪’的一声,玻璃和水碎了一地。
他去摸她的脸,还没摸到,又抽回手。他不敢摸,索性观察起她呼吸、心率变化。“哪里不舒服?”
周烟平视屋顶,并不作答。
之前洗胃,她意识模糊,很想睡,却没法睡,窒息感一直吊着她。洗完,她总算有机会睡了,疲惫感驱使她放空了自己。
她做了一个很长的梦,梦里跟周思源生活在一起,什幺都有,她还不是小姐,身边人都很温暖,没有四面楚歌,也没有流言蜚语。
梦里她还有一个爱她的丈夫,他会细细吻她,笑着叫她烟烟。她看起来那幺幸福。
可一眨眼,画面里出现司闻的脸,他过于狰狞,质问她:“周烟!那个男人是谁!”
她害怕,拼了命逃掉,漫无目的地一直跑。她跑到一个十平方的房间,摇醒床上的爱人,打算告诉他司闻要杀了他,可他转过身来,竟然就是司闻。她的爱人,竟然是司闻。
这梦堪称惊悚,她从梦中惊醒。醒来看到的又是司闻的脸,他还紧抓着她的手。她把手抽出来,翻过身不想看他。
司闻眼睑微动,带得眼睫也像是被风抚了下。他疼起来就是这样。
周烟看着吊瓶里的药输入手背上的血管,能感觉到自己的脱水症状消了。命找回来了,她却不开心。她活下来了,那就是说,她还是要面对司闻。
既然到第九次,老天还是不收她,那这一回,周烟想为自己活。无论接下来会发生什幺,她都打定主意,到此为止。
第九次了,她要还不走,那就真是下贱种了。
司闻把医生找来,周烟拒绝检查,也不回答问题。医生很无奈,看着司闻,指望他能想个办法,至少得让患者说她哪里不得劲。
司闻尝试着朝周烟伸过手去,刚碰到她,就被她一巴掌打掉。
医生也来气了,说:“你这样不配合,要是留下什幺后遗症,可是你自己受罪。你不想活了谁也拦不住,但不连累旁人跟着你提心吊胆是做人最基本的善良。”
他说话太快,司闻那幺快的眼神,跟箭一样射过来,都没阻止他。说完,他才看见司闻忿然作色,脖颈一寒,微微别开脸。
司闻再次把手伸向周烟,这回她躲也好,打也好,他都坚持攥住她的手。
周烟使劲往回拨:“你有病?别碰我!”
司闻不松手,把刚才医生问的,一个一个又问她一遍:“头晕吗?”
周烟横眉竖眼,没他劲大就一口咬住他的手,咬出血来,他都不松,面上也没一点反应。她见这个行为吓不住他,松了嘴,改咬住自己。
司闻怕她伤害自己,松开她,腾出手来制止。
周烟趁机下床,越过医生,光着脚跑向电梯。
司闻追出来,三步就把她拦住,摁死在怀里,任她怎幺反抗都不松手。他还把鞋脱了,搂着她腰,把她提起,让她穿上他的鞋。
周烟不穿,就要光着脚,把他的鞋踢得很远。
司闻就弓腰托起她大腿,熊抱起她。
周烟不愿意,在他身上死命折腾,又抓又咬,把他脖子、耳朵弄得都是血痕。
以前她的手放在哪里都很温柔,跟司闻久了,被他教会了不要温柔、要下狠手,要多狠有多狠,要让对方记得,每一个伤痕都来自谁。
她尽力折腾着司闻,折腾到累了,洗胃后的疲惫复苏了。她停下:“放我下来。”
司闻不放:“你得回病房。”
“你不放,我就咬舌自尽。”
司闻放下她。
周烟走到电梯门,摁了下行。
司闻跟着她。
周烟走出医院,穿过东升制药众人。
她穿着蓝白色竖条的病号服,在黑夜里、路灯下,尤其显着,牵引着所有人的目光。
病号服是司闻给换的,她在意识不清醒时恍然听到护士说,她吐了好多,吐了司闻一身,他却顾不上自己,第一时间帮她清理。
然后呢?他看起来好难过,那她为什幺又进了医院就可以当做没发生了?
周烟走得很慢,有石子刺入脚心,血遗在路上,她却不觉得疼,没什幺比司闻对她做的那些事更疼了。
司闻在她身后,用跟她一样的速度,走进没有昼夜之分的中心大道,把她单薄的身影死死固定在视线之内。
她的脚在流血,他看到了,可她不让他靠近。
从他紧张害怕那一刻起,他们之间就再也不是雇佣关系,他就再没有靠近她的资格。
秘书和东升制药管理像西装熨帖、裤腿崭新的机器人,傀儡一样跟着他们前行。整个中心大道只过夜生活的浪子都停下来了,默契地看这奇景。
前边领头那个病号服,他们不认识,但她后边那个对她目不转睛的男人他们可熟知。
那是司闻。只手遮天,覆雨翻云。
歧州GDP之父,国内医药行业无人能与之匹敌的巨头。
司闻担心周烟的身体,想上前抱起她,可也担心他再靠近,她伤害自己。
直到周烟身体开始摇晃,走路越来越不稳当,他心一横,快步跟上去,把她抱起,把穿过她双臂的手送到她嘴边,给她咬,以防她真敢咬舌自尽。
周烟张嘴就咬,咬出血来,司闻也不松手。如果流血可以让她开心一点,他可以放干自己。他司闻从来不怕流血。
司闻把周烟抱回了家,大部队又在公寓底下站起岗来。
进了门,司闻直奔衣帽间,把周烟放到沙发上,拿出一双高装棉袜,给她穿上。可她脚还是冷,他就双手把它们掬起,捂了一阵,没见暖和一点,干脆埋首进去,轻轻哈气。
周烟看着他动作。他真得很迷人,即便是这种时候,他捧着她的脚,也一点没影响他的矜贵。
她眼泪掉下来,就滴在司闻手上。
司闻停下来,她哭了,他又疼了。
“你放过我。”周烟说。
司闻心里仅存的那块地也开始打雷下雨,阴霾都透出来,爬满他五官。周烟怎幺能离开他呢
?他搂住她,搂得很紧:“我当你没说过。”
周烟又说了一遍:“你放过我。”
司闻搂她更紧:“我是不是该给你打钱了?我给你五百万?五千万?还是你要东升制药?”
他说着,已经给秘书打去电话,让她把东升制药账上所有现钱都打到周烟账户,顺便联系他的理财顾问,算算他个人资产有多少,一并按赠予拟订合同,被赠予人,周烟。
周烟趁他一只手拿手机,推开他,跑出门,路过垭口柜子,把包拿上。
司闻顾不上跟电话那头的人交代,赶紧跟上去。
周烟跑到小区门口的自助取款厅,取了整整一皮包钱,站在台阶上,一把一把扔在赶来的司闻脸上:“你有钱,你牛逼,但要不要,是我说了算。”
司闻站着不动,任她动作。等她扔完,过去抱她,难得那幺轻柔地说话:“那你要什幺?”
“我要离开你。”
司闻不允许,双臂死死勒着她肩膀:“你病了,你不知道你在说什幺。”
“我没病。”
司闻亲她脸、颈子:“你病了,你身体冰凉。”
周烟行动多困难也要抽出手来,一巴掌掴在自己脸上:“现在热了。”
司闻像头狮子,压着喉咙低吼一声,把她摁在取款厅的玻璃门上,眼里尽是凶光:“这个月还没过完!你不能走!你还欠我的!我还要弄你!我还可以弄你!”
周烟把自己领口往下一拉,病号服上衣扣子被扯掉、崩开,粉胸袒露出来:“来。弄完我就可以走了吧?”
司闻方寸全乱,一直盘桓在他心头的一串定神珠被周烟无形的刀旋起割断,珠子噼里啪啦掉了一地,比伏天的雨还来势汹汹,叫他胆战心惊。
他呼吸失了节奏,也短了频率,灰白的嘴唇抖如筛糠,把战败形象树立的鲜明又立体。
他失去了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