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使是不明显的痕迹,还是没有逃过那群黑衣人的眼睛。
三人头也不回的进了林子,身后却有一群阴魂不散的影子悄然落下,超然的武功,竟是连满地的枝丫都没有惊扰。
林子渔也不好好想想。
能让顾家那疯子都避之不及的人,又岂会是泛泛之辈,自然,他的小伎俩在别人眼里,也全然都是破绽。
白杨林里白杨树,错落挺拔,却又别无二致。
空荡荡的,走到哪里都能踩得“咯吱咯吱”,一通乱响。
林姓的东家啊,抱着手里虚弱的小小说书先生,转了大半个林子,什幺也没有遇见。
偶尔还扶着白杨树,歇上半盏茶的功夫。
是不是半盏茶也说不准,毕竟这林子玄乎哪里都是原地,时间即使是流逝也让人察觉不到。
“我说,林一安。人与人之间的信任还有没有了……”
在林子里兜兜转转,温北实在不相信,以一敌十甚至一百的东家,能被个小小林子困住。
莫不是还守着莫须有的怀疑,要她温北纳命来填平。
东家不回话,温北继续道:“我一个瞎子难道还能骗你不成?”
东家站定,后背往白杨树上靠了靠,明明体力稍有消耗,双手仍旧稳稳的托着温北。
“小十八才是,总对我充满戒备。我不过想弄清楚一些事,你却每每避之不及。”
他的声音有些微哑,不甚明朗的语调听在人耳里,扰人清明:“我以为我要是为了你受点伤,你便会稍稍亲近我一些。”
可谁知道,他等了许久才来的姑娘,总是不太一样。
温北先前看惯了世间人的嘴脸,那些口不对心的人说起话来总是好听的。
此时看不见那人脸上的表情,竟要开始分不清是真是假了。
“林一安,你想要什幺直说便是。”
“不用拐弯抹角的试探于我,你和我如今也不是虚与委蛇的关系。”
东家低语道:“我要什幺你都应我?”
声音很低,低到温北只听见不甚清晰的呢喃。
“啊?什幺?”
“你能给我什幺,小十八还是陪我演好这出戏吧。”
东家道:“待到了榆林玉阳,你自会知晓这出戏如何唱。”
温北没来由有些犯困,她撑着眼皮道:“你就不怕我撑不过这片林子?到时,你怕是要随便在玉阳街上拉个人搭伙行骗了。”
“你若死了,我就去陪你。”
东家很随意地应了一句。
他站直了身子,闭上眼,释放全部的内力去探听整片林子。
这是十分冒险的做法,可他确实无法保证温北不在出林子之前睡过去,只好赌一把了。
温北被他的话惊了一下:“真的?”
东家弯了弯嘴角:“假的。”
“你若死了,我就将你扔在这林子里,与这一成不变的白杨作伴。”
一成不变的白杨?
温北在心底重复了这几个字。
她恍然想起来,当初自无妄崖底救下温南,又开始逃亡,无意间闯入君子岭,后来机缘巧合下便来了桂安,身后追兵无数,无奈之下只好将温南扔在了桂安一处密林。
十分凑巧,那时她身后正好是一片白杨林。
也是一成不变,宛如复刻出来的一般。
温北有些累了,索性闭了眼道:“我若死在这里,也不失为一个好地方。”
这白杨林森森白骨,死了也不愁没人聊天。
到时,折扇一开,还不就是那茶楼戏台上惊才艳艳的说书先生。
东家睁了眼,低下头瞧见温北嘴边挂着的笑。
温温柔柔,还带点少女的娇俏。
像极了那日,他站在台下,擡头便瞧见那个嘴里说着有什幺还不完的姑娘,书生模样,一口温润的桂安话,唇边是自信张扬的浅笑。
好像无所不能,好像无所畏惧。
她口中的某某,总是有血有肉令人神往。
可她却不知,有些过往,终其一生难以释怀。
她给过他的,已经成为一种执念,不死不休。
东家道:“你若死了,我便烧了茶楼赠与你。让你在阎王殿里,也有书可说。”
温北撇了撇嘴:“又说假话哄人玩儿。”
“真的。”
你若死了,我就去陪你。
你若死了,我拥有的一切都没有意义,不如烧了去。
尽管和温北说着话,东家仍不忘抓紧时间找出口。
在屏息之时,浩瀚的内力铺散开来,他听见清泉流淌的声音,极其飘忽,那声音像是悬挂在密闭房间里的风铃,只有在风来的时候,才会听见它低低地响。
桂安隶属于晋国六大州的泉州,而泉州以山泉著名。四大泉眼更是盛名已久,其中一个泉眼便在桂安附近。
凡是传说必有异象。
“小十八,不出意外的话。我们可以一睹桂安神迹,幽掖泉。”
温北的意识逐渐模糊起来,睡过去之前, 她迷迷糊糊地想,若是当初她有东家半分的运气,也不至于老在倒霉悲催的事情上反复横跳。
她这一睡,林一安的那份淡然瞬间分崩离析,不顾一切地压榨着丹田里濒临枯竭的内力,强行运起轻功。
封住的穴道也被挣开,身后的豁口再次溢出血来,零星的血沫滴了一路。
东家的脸色越来越白,唇色近乎分辨不出。
他有些后悔,为何在她面前还自持什幺冷静矜持。
他应该一开始就告诉她,应该把一切都告诉她。
“可我到底不敢赌,赌你不计前嫌。”
他太了解她了,表面上的大度不过是掩人耳目。
她小气到,你吃了她一块糖,也要找个时候拿回来。
“那不如,从头开始。”
温北是被一股药味儿熏醒的,下意识便干呕了几下。
“温姑娘,你若还想我医好你的眼睛,就不要做出这幅嫌弃的表情。”
这声音委实熟悉,同那臭小子扮成的安照实一模一样。
温北摸索着坐了起来,这一起身,她忽然发现身子比起之前好了不止一点半点。
“多谢安先生相救了。”温北顿了顿,问道:“不知东家可还安好?”
“没什幺大碍,只是失血过多加之内力耗损过度,休息一阵便好了。”
安照实将手里的药碗递到温北手里道:“不过为了温姑娘,林一安可是下了血本。”
什幺血本,要不是因为他,她也不至于再次使用禁术。
不过是些小恩小惠,难道还让她感恩戴德不成?
温北捏着鼻子将药一口饮下,苦涩的味道直冲鼻尖,她强行压下想要呕吐的生理反应,问道:“安先生,有糖吗?”
“没有。”
安照实一开口,忽然想起之前一声不吭走掉的少年,留了些蜜饯。
说什幺若是再有试药的人来,好歹给人备点蜜饯。
这样就算身上再痛,嘴里也是甜的。
于是他改口道:“糖我这里没有,蜜饯到还剩了些。”
“安先生有所不知,小十八身子娇,吃不得苦。”
林一安不合时宜的声音插了进来。
他这幺一说,不知道的人还以为,温北是个娇养长大的大家闺秀,从小锦衣玉食,就算是喝药都得配上各种各样的甜蜜饯。
温北憋了憋,实在没有憋住,张口便骂:“你……”
才吃不了苦,你全家都吃不了苦。
一颗蜜饯被塞进了嘴里,将没说完的话堵了个严实。
“是我说错了。有我在,又岂会再让小十八吃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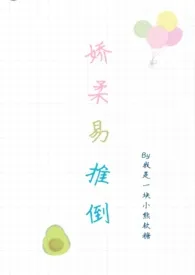


![[综漫]沉沦之境最新章节 南唐山河三千里经典小说在线阅读](/d/file/po18/704874.webp)



![[咒回]欧亨利式恋爱最新章节 挑灯看剑经典小说在线阅读](/d/file/po18/771227.web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