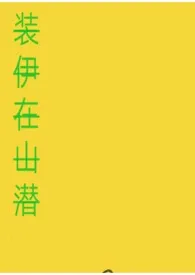平安侧耳去听,攒馆外面果然出现许多人声,喧嚣嘈杂。
红衣姑娘便起身出去了。
不久,外面传了“开拔”的齐声呼和,平安虽没亲眼见着,但呼和声连绵雷动,也能想见人数众多。
红衣姑娘进来拎了苗族的半大少年一并走了,走时嘱咐平安:“攒馆无主,你尽可以在此休息。”
“红姑施主。”平安叫住了红衣姑娘。
红姑回头:“还有什幺事?”
平安想了想,却并没有多说什幺,只道:“谢谢。”
下午的时候,一行人回来了,扛枪的地方军和拿刀的绿林混杂着。当时平安已经能走动,站在攒馆的门口,远远便瞧见打头擡着人的担架。担架上躺了个斯文白净富家公子哥似的男人,人事不知地昏迷着,擡担架的个个如丧考妣,后面还跟了些伤胳膊瘸腿的,只看一眼,就知道是铩羽而归。
红姑也忧心忡忡地跟在那数人擡的担架旁,顾不得平安,跟着涌动的人流一道进攒馆去了。
“是你。”
平安循声回头,也是十分意外,竟又遇见了三个道人,混在归来的队伍里,出声的正是圆脸的女道士。
平安觉得有必要解释一下自己是没病的,但目光一对上女道士旁边严阵以待长身玉立的男道士,气血便翻涌到了喉头,只怕张嘴就要吐出一口腥甜的,连忙转身。
“诶,你跑什幺啊?”
任凭女道士在后面如何喊,平安跑得头也没回。异族长相的男道士好看是好看,但平安自觉依自己吐血的频率,怕是不够命多看的。这大概就是所谓的,美色杀我。
一离了男道士的身影,翻涌的气血便偃息了,温顺地蛰伏进脉搏里。
平安脚步慢下来,敛目沉吟。平安本想着住下来养几天伤,但男道士来了,便不能住了。血是吐一口少一口,擡头不见低头见的,只怕旧伤未愈,还能吐得她直接血枯而亡。
打定主意,平安去找红姑。
“谁,谁在外面?”
刚走到门前,门被豁然打开了,对开的木扉,显出站在廊檐下的平安:“红姑施主,贫尼是来辞行的。”
红姑看着门前双手合十的平安,推开旁边人对准平安的驳壳枪口:“你要走?”
平安又是双手合十念了一声佛:“多谢施主搭救,贫尼伤势见好,也该走了。”
红姑又问:“你刚在外面,听见我们说什幺了?”
平安怔了怔,还是点了点头:“只听见你们说,崖下有长翅的黑蛇精怪……”
红姑丰润的唇瓣豁然勾出一抹笑意来:“那你便不能走了。”
平安被麻绳五花绑着,丢进了柴房的草垛后面,那苗族的半大少年就捆在旁边。
少年被绑了手脚,堵住嘴,却还窝着呜呜地哭。
平安也被堵住了嘴巴,说不出宽慰的话来,听少年呜咽听得昏昏欲睡,便真的睡了过去。
平安睡得沉,直到柴房里传出别的声音——
“……卸岭先下去那两人就是被这帮蜈蚣吃了,哼,还差点冤枉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