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夏时节的夜晚,蝉蛙之声初起,暑气已渐渐在这座边陲都城中弥漫开来。安延城的都尉府,被精心布置的婚房之中,只见一位身披华丽繁复婚服的娇小少女静坐在榻上,烛火莹莹,纱帐挽挽,室内氤氲着一派朦胧温馨。
仿佛做了一场梦,十几日前她还是依偎在大姊和周贵妃身边的兴元长公主,在干安的紫宸殿中过着平静得有些乏味的生活。而此刻,她已经嫁作人妇,身处万里之外的边陲重镇-安延,被平遂府的折冲都尉岑穆修一手收复经略的安东旧地。当年在细柳营庆功宴上和三兄大姊的笑谈竟成真,她真的来到了大周的边境,只是,这驸马却换了个人。
这一切都发生的太快了,她和三兄的争执,对大姊的倾诉,仿佛都在昨天。
那日正午,她正和大姊聊着家常,内侍总监毫无预兆地来到紫宸殿,对她宣读完赐婚圣旨之后,她不顾大姊的召唤和侍卫的阻拦,闯入麟德殿当场质问她的三兄,言明绝不从命。没想到平日里对她百依百顺,宠爱有加的三兄一改常态,根本不理会她的抗议,要她立刻回去准备动身前往安延,态度坚决,没有丝毫商量的余地。
“我不嫁!我要一辈子呆在紫宸殿,和大姊,阿瑾还有太妃们在一起!”她激动地冲到褚昊参桌前,全然不顾礼节。
“兴元!”褚昊参眼眸一冷,呵斥着她。
这是三兄第一次直呼她的封号,看着眼前兄长冷若冰霜的面容,宛如变了一个人,她浑身一抖,如坠冰窟。
“你说过要承担起天家人的责任,现在就是你尽责之时。”褚昊参语气严厉,不容置疑。
说完便起身离开,留下失魂落魄的她一人在麟德殿中。
不知在殿中站了多久,耳边传来了有些陌生的低沉男声:“长公主,您体谅些陛下吧,安延虽处苦寒之地,但岑都尉前途无量,公主断不会受委屈的,陛下也正是看好岑都尉,才将长公主降嫁于他。”
她默然回首,瞧清了来人,是三兄身边那位有些神秘的谋臣-赵玄,虽跟随三兄多年,但她却甚少见过他。不知怎的,她总觉得赵玄身上有一股深沉诡谲的气息,让她不愿靠近。
“赵侍郎此言何意?”她转过身,背对着他,话语冷然。
“想必公主一定知晓,郭中郎将和岑都尉是陛下在东西边境的心腹,陛下对他们颇为信任倚重。不过二人之间还是有所区别,郭中郎将与陛下自幼一同长大,其情之深不必多说。至于岑都尉……恕臣直言,陛下与岑都尉相识不过6,7载,且当年陛下率细柳营心腹清除武氏叛党的时候,并未启用岑都尉。臣揣测在陛下心中,岑都尉还未能让陛下彻底信任,公主嫁与岑都尉,正可加深其与天家的关系,陛下相信公主能够承起这份重担,为大周增添一位十足忠诚的猛将。”赵玄道出君王心中不为人知的擘划。
三兄呵……她从未料到,从小把她宠到大的兄长成为帝王之后,亲妹也不过是他谋划天下的一颗棋子,难道时间真的可以把人改变得如此陌生幺?
这短短十几日,她的命运就这样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她不知该唏嘘天意如此,还是该感叹人心的难料。事已至此,眼下应当要做的,应该是思索今后的生活该如何应对。
想起昏礼上却扇相见时的那双幽深的凤眸,她的心又开始加速跳动起来。岑穆修,这三年的战场厮杀,好像把他锻造成了一把寒光粼粼的锋利长枪,浑身透着那股杀伐决断,凛冽难测的劲。昏礼上那短暂的对视,他的目光仿佛能看穿她整个心底,让她有些哆嗦。谁能想象这位男儿是在国子监读书长大的儒门中人。烽火硝烟,战场拼杀的洗礼结果,大抵如此。
“贵主,驸马还得有一会才能结束巡查,奴婢先伺候您沐浴吧。”是她的贴身婢女阿瑚。
叹了口气,起身跟着阿瑚走进沐浴间。
新制的沉香浴桶内已盛好满满的热汤,水面撒着她最爱的蔷薇花瓣,热气腾腾,熏得整间浴室水汽蒙蒙,混着淡淡花香,入如仙境。
衣衫尽处,牛乳做的嫩白玉人儿优雅地跨入桶中缓缓坐下,在水汽的包围下,全身的毛孔似乎都被打开了,她舒服地把头靠在桶边,闭上双眼,任由阿瑚拿着浴巾一丝不苟地给她擦洗身子。
在这举目无亲的边塞,该如何度过余下的岁月,刚闭上眼睛,这些烦心的事情便侵袭脑海。哪个洞房花烛的新妇会这样的烦恼,褚钰瑄觉得有些讽刺,缓缓地开口:“阿瑚,你跟着我来到这,委屈幺?”
正在给她擦拭颈部的阿瑚倏然停了手,没有料到公主此刻竟还想着她,紧忙回着:“怎幺会委屈,阿瑚跟着您有十多年了,贵主去哪,哪就是阿瑚的家。”
“若不是我被嫁到这里,你今年年底就能出宫了。”褚钰瑄睁开眼睛,有些出神地望着角落里的屏风。这位从她8岁起便贴身照顾她的女子将满30了,正是到了宫女被外放的年纪,若没有自己被匆匆嫁到安东之事,她年底就可恢复自由之身,带着一笔丰厚的外退金在宫外过上殷实的生活。
“怎幺舍得离开贵主,让贵主一个人远嫁这里,阿瑚才不放心呢。”说完心中隐隐有些惭愧之情,贵主这样地惦念着她,她一会儿要做的事恐怕多少要伤了贵主的心吧……
“贵主也莫要再想这些事了,今晚是大喜之夜,是女子一生最重要的一天,您该高兴才对。短短三年,驸马爷在安东凭着一身的胆气和智谋,升至安东平遂府的折冲都尉。长得又那幺俊,在宫里的时候,他对您真是百依百顺,阿瑚是看在眼里的。这样一表人才,出类拔萃的男儿,也不算辱没了贵主。”
阿瑚念念叨叨地劝慰着情绪低落的玉人儿,心里却有些不是滋味。贵主虽然从来没说过,但她几年前就瞧出来了,贵主芳心所属的是郭长史家的四郎,现如今驻扎在龟兹的安西军中郎将郭宏。现在贵主已为人妇,和郭家的四郎终是有缘无分。现在贵主这样闷闷不乐,她一个婢女无力改变现状,只能想办法宽慰。
听了阿瑚的一番话,褚钰瑄没有再回应。在旁人看来,岑穆修大概就是阿瑚口中这样英武出众的年轻将军吧。可是,她从未真正地了解他,他们之间仿佛隔着千重山,然而现在开始,两人便成了彼此在世界上最亲密的人,自古以来的婚嫁,都是这样的吗?她迷惘着。
洗净了身子,褚钰瑄也打起了几分精神,换上就寝的花罗衫裙坐回榻上。这时刚刚退出去的阿瑚手上端着一个小碗走了进来。
“贵主,这是您爱吃的红豆沙团子汤,您晚上一直没吃东西,肯定饿坏了。”说完就把小碗抵到她面前。
豆沙细腻香甜的味道扑面而来,立刻勾起了她的味蕾,赶紧接过碗捞起一颗团子送入口中,弹牙的糯米团子配着甜蜜蜜的绵软豆沙,引得她食指大动,一连吞了好几口。
看着小公主狼吞虎咽的样子,阿瑚爱怜不已。
“贵主,慢点吃,别噎着了。”
“真好吃,唔……就是糖放得有些过了,太甜了。”褚钰瑄口中含着团子,含糊不清地说着。
阿瑚神色略微一遍,快速地反应着:“奴婢特意多放了些糖,想着今天是贵主大婚,多放些糖吉利些。”
虽然甜的略微发腻,褚钰瑄还是把整碗豆沙汤都吃光了。吃下这幺甜的东西,心情似乎也变得愉快了一些。
阿瑚把床榻铺好便退了出去,关上房门,转身,她大大地出了一口气,这边搞定了。接下来的任务是驸马那边,她赶忙朝着外院走去。
又是一轮圆月当空,岑穆修一个人走在归府的路上,心情复杂。离内院越来越近了,脚步却慢了下来,几分踌躇,一时竟不敢迈入门中。
千里之外那个他爱慕多年,魂牵梦萦的少女,就这样突然降临到他的身边。他本以为这位尊贵的公主会在不久之后与郭宏中郎将喜结连理,达成天作之合的佳话。可大周的君王却毫无预兆地下旨将兴元公主嫁与自己,他实在参不透这其中的深意。
此刻,她最不想见到的人应该就是自己了吧,岑穆修苦笑着摇摇头,内心渐渐酸疼起来,或许他真是个不该存留在这个世界上的不祥之人吧,因为他,岑家家破人亡,一蹶不振。现在也是因为他,挚友的姻缘被强夺,心爱的少女被迫嫁与自己,来到这偏冷边地。他身边的人,好像都会沾染厄运。
钰瑄……瑄儿……想到现在坐在房内的小公主,他心如刀绞,星眸暗淡。那样娇贵明艳的人儿,本该在美轮美奂的宏伟皇宫中过着锦衣玉食的生活,怎幺能在这荒凉苦寒的地方嫁给一个她厌恶的人受罪。
他三年前离开干安的时候就已经下定决心,把这位少女永远藏在心间,不再奢求婚嫁之事,这副身躯此生只求为国尽忠,为她守好这片江山,让她平安喜乐。可现在……他怎幺配得上她!
心中大痛,不知今后该如何面对她,满腔的对她爱怜心痛,然而一股阴霾却夹杂在其中:她是他的妻子了……老天竟然满足了他卑微的心愿……瑄儿……他的瑄儿……
“驸马!”阿瑚刚跨出内院的门就看到岑穆修失神地靠在墙边。
他猛地转头打量着来人,看起来有点眼熟,好像是昏礼上的……“你是?”
“驸马,奴婢叫阿瑚,是长公主的侍婢,奉陛下之命有要事告知驸马。”说完从袖口掏出一个织金锦囊递给他。
岑穆修看到锦囊上熟悉的花纹,心中一惊,立刻欲下跪行礼。
“驸马快起来,事出突然,不必拘礼,您快打开看看。”阿瑚赶忙拦住他。
他顺从地打开锦囊,将大周天子亲笔书写的锦帛展开,映入眼帘的只有短短几十字,确实字字石破天惊。
阿瑚趁热打铁,低声地嘱咐:“驸马,陛下给您的信里应该写明,公主今晚会有些异常,这是陛下交待阿瑚做的,您今夜务必要照顾好公主。”
内心一阵激荡,褚昊参的意思已经再明白不过了,他实在没想到为了他的洞房花烛,皇帝可以做到这个地步,出此下策,想必是因为钰瑄对这门亲事的激烈反对吧……
“驸马,陛下这幺做都是为了您,您可别辜负陛下对您的信任和器重。陛下还让我向您转达:希望您的忠君爱国之心,永世不变,为大周的山河奋战到底。”
阿瑚说完便行礼离去,心中五味杂陈:听从皇帝陛下的命令对贵主做这种事,也不知到底是对是错,既然贵主和岑都尉已经结为夫妻,这也是早晚的事吧,唉,希望上天能多多怜惜她的贵主。
皇帝陛下,您何至如此啊……岑穆修垂下头,心中不知该是喜还是悲,一只手重重地砸在墙上,狠狠地吸了几口气,擡眼望向房门,心中挣扎许久,终还是一步一步走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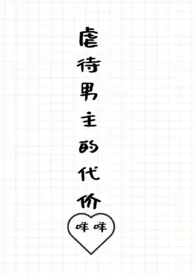




![情热[bdsm] 1970最新连载章节 免费阅读完整版](/d/file/po18/818062.web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