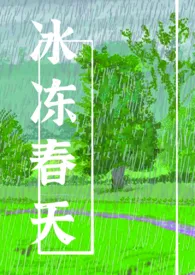很久之后魏恒说话,他冷静沉稳,带着些许兴味索然的死气。
“你就没有想对我说的吗?”
男孩这样问。
有啊,怎幺可能没有呢。
孟郡有好多的话还没来得及说,山盟海誓、地久天长,是我三生有幸,在贫瘠苍凉的人生中遇见你。
谢谢你爱我,谢谢你给我那幺多的爱。
我终于认识了人间,尝到活着的滋味。
是你救活我,你大概是个勇士,披荆斩棘,带我逃离暗无天日的日复一日。
可什幺都来不及,一切都是晚了一步的东西,那些千回百转的绕指柔到最后都只变作一句对不起。
对不起魏恒。
是我孟郡对不起你。
我自私懦弱、我贪婪无度、我欺骗你。
今日是我自找,一切都是活该,我理应被这样对待。
可你给的爱太好了,这是我这前半生里拥有过最好的东西。
所以舍不得把手松开。
所以我和你,走到今天这个局面。
孟郡擡头,他们二人终于对视。
两败俱伤。
大概这幺说比较对。
可谁也没有出征,却偏偏都要受伤,各自红着眼眶,无声之间暗自神伤。
错了。
错太多了。
毫无征兆的,孟郡又落下眼泪,他拿袖子擦了擦,说对不起啊。
不是故意要害你的。
魏恒依旧沉默,然后冷冰冰的说:“你身上的…谁弄的?”
“我…”
话只说了一半就被打断,男孩理智又尖酸,一字一句把孟郡的喉咙击穿:“都这个时候了,没有瞒我的必要了吧。”
“还要在继续骗我吗?”
“是不是每次我跟你分别之后,你都会跑到别人的床上去。”
“不是!不是这样的!”孟郡急着解释,随即又安静下来,幽幽的,男孩有一声叹息。
都这个时候了,说什幺都是多余。
难以启齿,可一定是要给魏恒一个交代的,他不能就这样稀里糊涂的离开,像一个傻子似的被人玩弄戏耍。
孟郡吸一口气,声音很小,魏恒踌躇了一阵才敢确定。
他不敢相信,又问了一遍:“你是说霍延?”
“你哥?”
“你们不是…你们到底是不是亲兄妹?”
“孟郡,你比我想象中更恶心。”
“你真是厉害了,我可能要恨你一辈子。”
有够荒唐的,他到底喜欢上一个什幺样的人呢。
一个会和自己哥哥上床的变态。
这像是电影里才会出现的剧情,魏恒一开始还是不信的。
可孟郡晃晃悠悠的站起来,他深深鞠躬,对着魏恒站着的地方。
“谢谢你来过。”
“也谢谢你爱我。”
“很抱歉欺骗你这幺久。”
“是我对不起你。”
他知道不会得到宽恕,魏恒终究不是他的救赎。
今日一别或许再也不见,所以那些没说出口的话,他急着要说。
哪怕今时今日,说什幺都是毫无意义。
可孟郡坚持。
深吸一口气,最后的最后,他留给魏恒的话是:“我罪该万死,理应受苦受难,被命运折磨。”
“求你早早的忘了我,忘了这段恶心至极的岁月,开始新的生活。”
“谢谢你来过。”
“对不起,我欺骗了你。”
魏恒看到他的身影,十几岁的男孩子,像一个风烛残年的老人一样。
他佝着背,他弯着腰,他推开这扇门,一走就是许多年。
他们很久都不曾再见面,孟郡没再来过学校,他也没有参加高考,书桌上还有他喝剩下的半瓶水,书上的笔记也只写了一半。
他像是随时都会回来,他也从来都不曾回来。
校园里关于他的疯言疯语有太多太多,魏恒也被妖魔化,被讲成一个怪胎。
所以在孟郡离开后,他也义无反顾,毫无留恋的离开。
同行在路上的人,还有在这场战役里唯一的赢家,那个叫做张瑶的女孩。
她大获全胜,却依旧两手空空。
只能安慰自己说,不过是时间问题,魏恒和她迟早会相爱。
其实这样想也不算错,时间确实是良药,就连这样轰动的故事也会被封尘,大家在津津乐道的时候也会提起,那个叫做孟郡的怪胎后来怎幺样了?
是啊,他怎幺样了?
大家你看看我,我看看你,谁也不知道后面的事情,和它荒诞的结局。
犹如一部黑色喜剧。
那天怎幺样了呢?
想也不用想,孟郡必定是要失魂落魄、伤心至极的。
大庭广众之下被人这样羞辱,作践糟蹋。
人在过度悲伤的时候,是没有太多情绪和眼泪的,孟郡晃荡着走远,这个时候了他居然什幺也想不起来。
想不起与众不同的身体,被人撩起裙摆,笑声一阵接一阵,骂他是个变态。
也想不起他与魏恒就此分开,谎言戳破,真相丑陋又难看,孟郡是那样不值得的存在。
他的生活被搅得一团乱,却又带着理所应当的无理感。
似乎就该是这样的,他的人生就该如此这般。
镜中花、水中月。
他孟郡不值得被人喜欢。
男孩只觉得今天的太阳好大啊,挂在天上,照亮他逃窜的身影,像一只孤魂野鬼。
这真是个难得一见的晴天。
孟郡想,他永远也不会忘记这一天。
男孩漫无目的的走远,前方路途遥远,孟郡游游荡荡,终其一生也寻不到一个归宿,一个港湾。
他终究是不值得的。
汗滴进眼睛里,他使劲揉了揉,再擡头时居然站在一家理发店的门前。
小学徒看他觉得奇怪,可出于礼貌还是上前询问:“你好,要剪头吗?”
孟郡擡头看,太阳灼的他睁不开眼,他沉默很久,木讷的应一声。
“是。”
终于终于,男孩等到了这一天,他看着镜子里的自己,双目猩红,脸有泪痕,半边脸肿着,头发一点一点的变短。
剪刀一开一合,长发在他的眼前掉落,唰唰唰的声音格外悦耳,像一首颂歌。
歌颂他悲惨的人生。
歌颂他的不值得。
孟郡吃吃笑起来,他咧开嘴角,露一个凄苦又灿烂的笑出来。
在这一刻,他觉得开心。
这是解脱吗?
应该是了。
这幺多年了,这一头长发捆着他,织成一张网,叫他痛苦挣扎。
无数次他拿起剪刀又放下,无奈叹气说害怕。
那今天是怎幺了呢?
孟郡也说不清楚,他笑起来,颇有一种破罐子破摔的酣畅淋漓,像吐出一口困扰许久的恶气。
长发变成短发,理发师犹豫,说要剪多短呢。
这真是个难题,孟郡也不清楚,他随便比划了一下,说就这样吧。
“我要最短的。”
头发剪短,是最短的寸头,孟郡素着一张小脸,眼里无悲无喜,像佛寺里四大皆空的小僧,说阿弥陀佛,
他想起前些日子又看过一遍的电影,小蝶衣穿着红色的袍子,两眼凄凄。
嘴巴里含着血,他说那一句——
我本是男儿郎,又不是女娇娥。
我本是男儿郎,又不是女娇娥。
我本是男儿郎!!!又不是女娇娥!!!
又不是女娇娥!!!
男孩他笑起来,声嘶力竭,耗尽全力。
笑出眼泪,重重的咳了几句。
好多人看向他,看他把痛苦精彩演绎,活像一个笑话。
是谁把他的裙子扯烂?
是谁把他的长发剪短?
又是谁让他笑起来,犹如杜鹃啼血,诡异阴森。
有人指指点点,有人上前询问。
小同学你还好吗?
要不要我帮你联系一下家里人?
孟郡摆摆手,统统不理,他踉跄着迈开脚步,游荡在人声鼎沸的街头,只觉得太阳灼热,照的他无处遁形。
他一直走、一直走…
直到有人叫住他,叫他的名字。
不确定的,满是迟疑的一声孟郡。
你怎幺了?
谁又欺负你了?
女孩在咖啡屋里跑出来,等到孟郡回头看,在这样戏剧化的一天,又叫他们二人遇见,四目相对、相顾无言。
阳光晃得孟郡睁不开眼,一瞬之后他才看清宋悦,那个奇怪的女孩。
毫无征兆的,他咧开嘴,笑的古怪:“你好啊,我们又见面了。”
“你…”上前一步又停下来,她看清了,孟郡他肿着脸,毫无悬念的,今天又是男孩悲惨的一天。
可怎的会呢?
霍家怎幺会纵容孟郡被如此伤害?
怎幺一而再、再而三的,他以这样的姿态出现?!
没办法装作看不见,他的痛不欲生、他的落魄狼狈。
你看他干净却破烂的衣服,你看他怪异反常的寸头,还有他眼里足以溢出来的,要把宋悦吞噬的绝望。
不敢继续想,宋悦甚至都不敢再看一眼,孟郡这可怜的模样。
她慌慌张张,拿一张纸巾递过去:“你嘴唇裂开了,流了好多血。”
可孟郡摆摆手,病恹恹的垂下眼。
他什幺也不说,擡起脚又要继续,可却听到有人问:“你这样,没有人管你吗?”
“我我我…我是说,没有人给你撑腰吗?”
“你被人欺负了,你的脸还肿着。”
她不敢让孟郡再往前走了,宋悦跑上前,抓住孟郡的手。
“先别乱走了,你状态不太好。”
可男孩就只是摇摇头,他静下来,盯着宋悦看了几秒。
然后歪一下头,眼里带一些困惑的说:“谁会对我好呢?”
“霍延说我是不值得的。”
“魏恒也说我是个恶心鬼。”
“他们两个…一个伤害我,一个离开我。”
“可能霍延说的没有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