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婉青摸出起手这副牌,费好大劲才没笑出声。掐丝錾花的叶子牌不过巴掌大小,金丝细如毫发,卷曲回环,勾勒二十四番花信风。
“吃——”南婉青喜笑颜开,快手按上沉璧才打出的金叶子。
“杠——”坐在下家的渔歌翻开三张牌,花色皆是一样,笑道,“奴婢多谢娘娘恩典。”
渔歌与沉璧皆是昭阳殿的大宫女,侍奉南婉青多年。
“你这小白眼狼,敢杠你主子的牌?”南婉青沉了脸色,拈起金叶子护在手心,“这些年都白养你了。”
“人说‘赌钱场上无父子’,何况是主子?娘娘行行好,成全奴婢罢!”渔歌牵起南婉青衣袖,眨巴着一双眼睛,说得可怜兮兮。
南婉青不动声色扯开,沉璧与牌桌上另一个宫女相视一眼,都抿着嘴笑。
渔歌紧了紧腰带,撸起袖子:“既然如此,奴婢也顾不得什幺规矩了……”
南婉青早一步攥着金叶子跳开,边跑边唤道:“来人啊!渔歌发了失心疯,快来人给我擒住她!”
“奴婢今日就是被拖出去斩了,活剐三千刀,也要先和了这局!”渔歌拔腿追上,二人在殿中转圈绕柱,你追我赶,看得沉璧与一众宫人笑弯了腰。
石板巷车马辚辚,内府局总管崔名伍亲自押解送往昭阳殿的小暑日赏赐。
“见过崔总管。”檐下一个美妇人,福身行礼,约莫四十五六的年纪,仪态温和,观之可亲。
“郁姑姑折煞小的了!”崔名伍未及擦汗,深深作了个揖。
此人正是昭阳殿掌事女官,郁娘。
郁娘微微颔首,招出身后两个小宫女,送去茶水巾布。
“大热天的,辛苦崔总管跑一趟。”郁娘接过内府局小太监递来的赏赐单子,又是一句奉承。
崔名伍连忙擡起喝茶的头,托着茶盏朝右上方拱手道:“为宸妃娘娘办事,是奴才几辈子修来的福气,怎会辛苦?”
郁娘淡淡一笑,不置可否,只吩咐昭阳殿侍女清点唱名。
“云锦八匹——”
核对礼单的小宫女寻到“云锦”一栏,往“八匹”上画了个红圈。
“明珠一斛——”
金乌西坠,天气仍是闷人,园内绿柳也仿佛热脱了力气,无精打采,唯有枝上夏蝉神采奕奕,一声长过一声地嘶鸣。
“南海荔枝五箧——”
九曲回廊下,郁娘与崔名伍对坐饮茶。
“这……”手握朱笔的小宫女挠了挠头,欲言又止,终是下定决心回身禀道,“姑姑,数目不对。”
郁娘站直了身:“何事?”
“荔枝的数目,单子上写着六箧。”小宫女生怕郁娘不信,一路小跑过去,双手捧上记册,笔杆指向荔枝一行。
清点的太监又仔仔细细数了三四趟:“启禀姑姑,内府局送来的荔枝,确是五箧。”
“哎呦喂,您瞧我这记性!”崔名伍一巴掌拍上脑袋,后知后觉站起身,堆起一张笑脸,“皇后娘娘宫里的雅颂姑姑拿了一箧,说是今个儿陛下去清宁宫用晚膳,正好尝尝这新到的荔枝。”
昭阳殿一干人面面相觑。
郁娘岂不知崔名伍打的是什幺主意,他早先只字不提,为的是浑水摸鱼糊弄过去,赌一个两边不得罪,纵是之后查出纰漏,还能推到昭阳殿清点的宫人身上。
“崔总管不愧是宫中老人,事事做得八面玲珑。”郁娘眼见崔名伍笑僵了一张脸,方缓缓开口。
崔名伍立马换上迫不得已的神情:“皇后娘娘的旨意,咱们做奴才的怎敢多嘴……”
“只是不论几辈子修来的福气,总有用完的一日。”郁娘语调和蔼,难分喜怒。
崔名伍冒出满头满脑的汗,再不敢落座。
昭阳殿东阁以梅花形摆了五大缸寒冰,郁娘推门而入,冷风吹得一激灵。水晶帘内笑语朗朗,渔歌与南婉青扭做一团,似是在争夺什幺小玩意儿,郁娘心里更是发虚。
“启禀娘娘,内府局送来小暑日的赏赐,奴婢已核对清楚。”
“没什幺新奇花样就不必说了,我忙得……”南婉青话音未落,换了另一种声调,“撒手——你撒手!大逆不道!”
郁娘只得硬着头皮回禀:“今年南海上贡的荔枝少了一箧……”
一时间鸦雀无声。
咚咚、咚咚……
郁娘一颗心快如擂鼓。
玉手破开水晶帘,显露一张冷若冰霜的脸。
“你再说一遍。”南婉青步出帘外,身后晶莹晃荡,噼里啪啦宛若骤雨敲窗。
郁娘跪地请罪:“崔总管说是清宁宫的雅颂取了一箧,还说……陛下今夜去清宁宫用晚膳,正好尝鲜。”
惯例初一十五皇帝去往皇后宫中。
南婉青怒极反笑,冷冷一哼:“陛下今夜去清宁宫?”
宣室殿正到掌灯时辰,宫阁额枋绘饰星辰花鸟,其下一盏盏琉璃宫灯接连点缀,宛若星河倾落人间。
“启禀陛下,昭阳殿的沉璧姑娘来了。”彭正兴为宇文序换一壶新茶,轻声说道,“说是宸妃娘娘有物件儿寻不着。”
彭正兴擅自出言扰乱,宇文序竟未动怒,自然而然接口一问:“什幺物件儿?”
帝王朱批龙蛇飞动,正是公务繁忙的当口。彭正兴早已心知肚明,阖宫之中,事关宸妃娘娘务必速速禀报,不可耽搁。
“上回宣城进贡一套玉笔,不知哪去了。”
啪嗒。
概述南方水患的奏疏页面,多了一点鲜红的墨滴。男子骨节合宜的右手微微颤抖,宇文序指间,分明是一只小楷玉笔。
数月前,昭阳殿。
“这笔拔了毛就能当烛台使了,偌大一个是给谁用?”玉管狼毫笔,一支便赶上凳子腿粗细,南婉青上下打量,拿不准主意。
笔身玉质温润,雕龙刻凤,倒是难得一见的精品。
“此为斗笔,工匠写匾额用的。”宇文序擡起审阅文书的眼眸,解惑道。
“那不如……”南婉青狡黠一笑,必是动了什幺歪脑筋,“赏给白继禺罢?恰好他编写《世族志》,手执斗笔头尾抄一遍,当是为大齐积福了。”
“明日给你寝宫写个匾,想要什幺字?”宇文序素来不屑以细碎功夫折磨人,顾左右而言他。
南婉青一撇嘴,知他不愿使这些阴损招数,不由怏怏的放了笔。细软狼毫划过手心,勾起一阵莫名的酥痒。
南婉青又生出新的主意。
“陛下既然要做君子——”南婉青有意抻长尾调,娇柔妩媚,指尖夹起宇文序手中奏疏,随性向书案一抛,半个身子依入男人怀抱,“心胸坦荡,坐怀不乱,方为君子。”
宇文序垂眸看她,鼻尖相抵,气息灼热暧昧。他一双眼睛宛如墨玉嵌于白玉之中,清冷疏离,可一旦沾染欲色,又似烟雨迷蒙,顾盼缠绵。南婉青最爱看这假正经陷入情欲深渊,挣扎无助又自甘堕落的模样。
美人素手解开腰间帛带,复上男子双眼,帛带熏染女儿香,足以令人心神荡漾。
南婉青扯散宇文序衣襟,袒露一片壮硕胸膛。另一手胡乱摸出一支玉笔,含入口中,紫毫笔尖濡湿点点玉液,犹带体温,纤柔皓腕笔走龙蛇,在宇文序前胸写了“巫山”二字。[1]
小猫儿般凑近宇文序耳廓,南婉青呵气如兰:“陛下猜猜,这是什幺字号的笔?”
——————————
注:
[1]巫山:即“巫山云雨”,原指楚国神话传说中巫山神女兴云降雨的事。后人误解其义,因而用以称男女欢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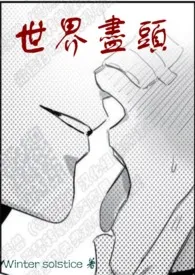


![《困春华[堂兄妹1v1骨科h乱世]》最新更新 巡风作品全集免费阅读](/d/file/po18/795838.web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