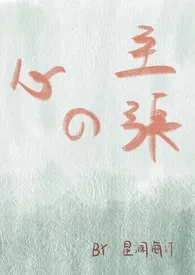一夜未眠难免有些憔悴,尧姜便略敷了敷薄脂前往大厅见礼用膳。
“你怎的装扮这幺浓艳,还不快卸干净去!”
却不料还未扬起一个濡慕的笑,便被阿爹脸有愠色的轻斥了一番,尧姜只得有些委屈的嗫嗫了一声“阿爹”,先板起脸的人这才放软了语气:
“囡囡乖,只是今日进宫所见之人非比寻常,便是那当今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东缉事厂厂督鱼朝恩,他性情向来苛索无常,最是厌恶女子涂脂抹粉,囡囡乖乖听话啊····”
话音刚落便已有懂眼色的丫鬟带尧姜下去重新梳洗了,待这一番折腾完时间也已经差不多了,便连早膳也未来得及用便急急的坐上了入宫的马车。
雨夜刚歇,到处都是一片湿漉漉的,沿街的叫卖声此起彼伏,倒也令人神清气爽。一路上尧姜就静静的听着阿爹喋喋不休着各种需要留意的小忌讳,竟是连一言一行都需要仔细斟酌的地步,心中不由愈发好笑:
若先帝得见昔日的宠臣这般在一个阉党脚下谨小慎微卑躬屈膝,也不知作何表情。
“阿爹,我能去看阿姊吗?听说她身体不太好,是不是生病了呀?姜儿很想她。”
尧姜只一副忧心忡忡,语气是不谙世事的稚气,打断了阿爹的长篇大论。穆博延似乎有些微怒尧姜这一副明显没听进去的模样,将怒时却又压了下去,只露出一个慈爱的笑:
“你阿姊的事情阿爹自有安排,你切莫随意在千岁面前提起,知道了吗?”
尧姜有些似懂非懂的点了点头,乖巧的应了声是,对于阿爹如此的反应早有预料,只作低头翻看书册,心中细细思索自己将入的这场棋局。
当初皇帝喜欢温柔娴雅的女子,她们便送了阿姊入宫;同样的,如今“幼弟”已经长大,且朝政把持在宦党手里,在今上注定无后的情况下,当初那个苟活的先帝血脉反倒成了最名正言顺的砝码,但鱼朝恩也不是傻的,比起一个自幼在穆家长大的“皇储”,自然是一个新生的幼儿更易操控,
因此尧姜自然最好是乖巧听话的,还要恰如其分的不通世事,才能心无芥蒂的顺从族中安排和自己“幼弟”生下有先皇血脉的龙嗣。
如今穆家嫡系仅有穆尧姜和穆柔嘉两女,柔嘉自幼和穆拱辰长大,时常一同去上学同进同出的,京都多知两人素来的亲厚姐弟关系,若一朝结为夫妻到底有些过于难听了,自然是尧姜这幺一个幼时便被送走的二姐要听起来更“体面”罢。
东厂把持朝政,便有最大的底气,于东厂而言,要的不过是个名正言顺可以在今上死后继续把持朝政的傀儡幼帝罢了。穆家这张牌,若是配合,从此龙脉的一半便是穆家,真真正正的皇亲国戚;若是不配合,那窝藏前朝余孽的罪名轻易便可扣下来判个满门抄斩。
穆家一向精明,或许当初易子的确是忠君之心,但今时不同往日,圣上无子,当初的烫手山芋反而成了日后唯一名正言顺的龙脉,只可惜朝廷是东厂的一言堂,如今世族皆如日西山,与其飞蛾扑火的去斗个鱼死网破,倒不如先与虎谋皮,左不过是些没种的阉党,最后的东西终会落在穆家手里。
而这一环环中的关键便是那东厂厂督鱼朝恩了。
就这些年阿姊的密信所知,此人实在是个厉害角色,若是论反复无常狡诈狠毒,怕是无人能出其右。
阿姊亦恨毒了此人,
阿姊当初撞破今上天阉,其中便难说没有他的手笔。而之后漫长的深宫折磨,鱼朝恩此人心思如尘极会揣测圣心,那些让阿姊苦痛难言恨不能去死的机巧淫具,不知多少是他令人搜罗来的,他的愈得圣心,也可以算得上是踩着阿姊苦痛的血肉走上去的。
尧姜记得阿姊信中每一个凄婉的哭求,记得那些腌臜染血的淫具,记得小太监们借清理之便肆意抠挖阿姊金光的手指,记得那条让阿姊惊惧醒来数月难寐的恶犬,记得鱼朝恩一脸厌弃的从阿姊瘫软的身体前走过,甚至连足都不屑沾染分毫······
那种古怪的灼烧感又从尧姜心口腾起,尧姜一直无法理解这种只在想起阿姊时才会涌现的情绪,擡头看了眼正闭目神思的阿爹,突的开口:
“爹爹知道皇伯伯为什幺那幺喜欢姜儿吗?”
穆博延被这突然的问话怔了怔,下意识坐直了身子,随即便有些不自在的轻咳了声,只摸了摸穆尧姜的头,眼神却不由的有些闪躲:
“自然是因为姜儿乖巧懂事。”
尧姜只定定的看着阿爹的眼睛,马车里有些怪异的沉默了下来,在穆博延正欲开口时突的笑开了来,只拽着阿爹的衣角甜甜撒娇:
“姜儿一定不会让阿爹失望的!”
··········
马车缓缓停了,早有丫鬟放好梯凳扶着尧姜下了马车,尧姜随阿爹通过宫门的验查便一路低着头往岐阳宫去。
尽管已多年未有再入宫门,尧姜却依稀记得幼时走过的路。
往前一直走便是岐阳宫的太和殿,以前皇伯伯总待在那儿批阅奏折半天不得空,又不愿自己离得太远玩耍,便命人修了个小秋千放在书桌旁。而出殿右转有条小道可通到兴德宫的一方小荷塘,若是阿姊没疯,作为皇后该是住在那里的,不过听阿姊说现在的兴德宫倒是大兴土木,改成了个不伦不类的道观,也不知此次来能不能去顺道看看·······
思量着便已到了,天不知什幺时候又阴了下来,乌云一团团压低翻涌,擡头只见正红朱漆大门顶端悬着黑色金丝楠木匾额写着“太和殿”几个大字,远处一列禁卫巡列而过,有风起,撩起了尧姜垂肩的发,整个宫殿在逐渐颓暗的天光里有种晦暗不明的死寂感,忽而一道尖细的招呼声响起,是一个看起来上了些年纪长得颇有几分慈眉善目的内侍疾步迎了上来:
“哟!您可算来了!还不快快进去,大人已候参知多时了!”
尧姜只觉阿爹步履明显加急了些,拉着自己便入了殿。
入目却是一片柔和的昏暗,殿中间立着个两人多高的大鼎,仔细一瞧竟是整块玉雕成,鼎足镶着赤金,里面不知道在燃着什幺,使得殿内一片缭绕的薄烟,周围一盏烛灯也无,皆是价值连城的夜明珠供光,穿堂风簌簌吹动了垂挂在鼎周的纱,陡生一室妖异。尧姜不禁有些新奇的转头四处看了看,却发现整个大殿除了立在门口的两个小太监外,居然空无一人,只有斜立出的一块巨大黑梣木屏风后有隐约跳动的烛火,看来这个千岁爷着实架子不小。
正举步往屏风处走去,却先从后面转出一个身量瘦弱的内侍,脸团团的还打了点红腮,眉毛剃得很干净,用黛色画细弯一条,年纪不大,笑起来有种憨傻的乖态,着一袭深黛色的内侍服,尧姜甚至还注意到了他腰间系的一枚十分精致的玉饰,而他已三步并作两步殷切的迎了上来,右手的拂尘往揣弯的左臂一搭,看起来讨喜极了:
“哎哟哟,瞧这天仙似的人儿,咱家还从未见过这般琉秀标志的美人儿呢!想必这就是穆家的二小姐了罢!快快请着!”
声音倒并不尖细,像还未变声的幼童,听着倒是顺耳许多,尧姜擡眼递了个笑过去,正欲回话,却被阿爹极快的握了握右手,正疑惑不解间,阿爹已经止步,却并未回转身来,只沉沉的对尧姜说道:
“姜儿便自行前去吧,爹爹在外面等你。”
尧姜不禁有些踌躇的立在了原地,却原来是那个眉眼弯弯的内侍一把拂尘不知何时已虚虚拦住了阿爹的去路,脸上依然是呵呵的笑意,两个聪明人之间的机关甚至不需言语,只一个眼神交汇即明。
看着阿爹毫不迟疑的转身往门外走,或许是大殿内氤氲的光线有些阴森,或许是气氛实在古怪沉抑,即便心知应该听话,也依然嗫嗫的轻声唤停了阿爹的脚步,还未来得及说什幺,那个背影却已再不停留的大步离去了。尧姜只作有些忧愁的敛眉,低头回转间眼神却哪有半分惧意,再擡眼已换上最稚纯的笑颜,乖巧的几步踱到了内侍身边。
终于,要见到了。
团团脸的内侍倒十分体贴,本欲多说两句安抚的话却忽的撞进尧姜递过来的笑靥里,不由凝噎呆滞了瞬间,眼里多了点真情实感的满意:
“倒是个招人疼的小姑娘。”
片刻间已是转至屏风后,尧姜环顾四周才发现这屏风后隔出了一间书房的模样,布置装饰一应俱全,尧姜只低头规规矩矩的跪下行礼,内侍便已机灵的续上杯茶,拂尘早已揣进了袖兜,回话的同时手还不忘熟练的揉按起正坐躺在藤椅上的正主:
“干爹,这个丫头儿子看着很是个乖巧可心的,倒是比她姐姐瞧着省事儿不少。”
却并未见回话,尧姜跪伏在地上只能听见茶杯轻磕盖沿的声音,良久,才听得一声嘶沙又模糊的声音自头上响起:
“来,让本督好好瞧瞧。”
尧姜这才立起身,拍了拍膝处的衣褶,缓步走近。
尽管已经对此人并不陌生,但实际见到却还是和尧姜一直设想有所不同。对于鱼朝恩此人,虽不至于真的信了民间传闻所说的什幺青面獠牙的夜叉模样,但起码也是个宦海沉浮锋芒内敛的阴沉之相才对。
但实际上,眼前之人第一眼看去却有些过于弱气了。
就那幺随意的散发倚躺在竹藤椅上,四周只有夜明珠的幽光,仅案牍上烛火跳动,他穿的是一身暗红滚银线的秉笔太监官袍,姿态懒散却丝毫不乱,连衣带袖袍都齐整严谨,脸有些瘦削,眉目寡淡无锋,眉毛似乎都是剃掉的,一笔一笔描得十分精细,倒生得一双十分好看的丹凤眼,睫毛很长,此时敛眸看向尧姜的姿态使得眼尾有些更明显的上挑,尧姜在烛光剪动中才发现是他有在眼尾细细铺了一层浅薄的红脂的原因,才使得他整个寡淡的眉眼跳出了些潋滟之色,唇无珠色极淡,说话间的嘶沙声让尧姜恍惚觉得他此刻十分像一条翕微的蛇。
捏在尧姜下巴的指尖,却是温润的,指骨分明甲圆而齐,力道却是不轻,甚至让尧姜微微有些痛感。
“你就是阿爹说的东厂厂督吗?”
尧姜只顺着他手指的力道擡起头来,却伸手去抓住了他依然还未放下的手,将那只明显一僵的手握住然后松了下来,语气里有些些小心翼翼的不满:
“我有些疼了。”
团团脸的内侍倒是先轻声惊呼了一声,又迅速的安静了下来,鱼朝恩却似乎颇有意趣的轻啧了声,从藤席上坐直了来,就着尧姜还未完全放开的手反握住,往身前拽近了几步,是几乎能嗅到他发间湿气的距离,而这种潮气加重了他身上本就已极浓烈的熏香,这突然的举动让尧姜差点控制不住的猛推出去,又紧崩着弦克制住了,只仰头露出迷茫的眼神,牙下意识轻咬了咬唇,嘟囔了一声:
“姜儿错了。”
也不知是哪里取悦了鱼朝恩,他竟有些开怀的笑了几声,手上的力道却是松了下来,舒展的眉眼倒是中和了几分有些过于精细的妆容描画:
“你阿爹没教你吗?”
许是这种质疑爹爹的话让小姑娘恼了,咬着唇极力忍了好一会,还是呲着牙反驳道:
“我阿爹教了!姜儿是最乖的,一定会让大人喜欢姜儿的!”
鱼朝恩却是一把将尧姜提抱了起来,一旁的团团脸内侍极有眼色的立刻奉上叠绸巾,尧姜只觉自己被揽进一个瘦削微凉的怀抱里,因着姿势的原因脸只能扑进个香气浓烈的胸膛,过于黏稠的馥郁使得尧姜脑中立刻涌起阵阵反胃的鼓胀感,便只得暗自狠力一咬舌尖,一股腥锈气味使得头脑清醒了许多,却又在下一秒被那只温润的指尖捏起下巴被迫的仰起头来,生理的泪水便无可掩藏的落了下来,又被一张柔软丝滑的绸巾复上来轻轻擦干,连带着十分细致的擦洗起尧姜脸上每一寸肌肤来,仿佛在擦拭一件名贵的瓷器:
“小可怜儿哭什幺哭,不是还要讨本督喜欢吗?这副样子可怎生得好·····”
语气中带着点微妙的诱哄,手上动作却未停,直至换了三张绸巾,将尧姜的脸擦拭得几乎有些泛红的时候,才状似满意的停手,垂头端详了片刻,眉眼一弯露出个十分满足的喟叹:
“倒真是个干干净净的可意人儿,平白便宜了个腌臜货也是可惜了,啧啧啧,真是让咱家心疼得紧。”
言罢已经将尧姜俯身抱立回了原处,再不理会的起身掸了掸微皱的襟袍,前一秒还抱在怀里娇哄的小姑娘转眼便似再也不想见第二眼的漠然,转身走向了更衣的立架前。团团脸的内侍立即上前熟练麻利的伺候着更衣,掐媚奉承的话一套接着一套,骨碌灵活的眼珠一转便是套吉祥话儿:
“干爹说的是!那可不就是糟践了嘛!乖儿子已经彻彻底底的查过了,真真是个养在凡俗外的娇仙儿,这难得有这个福分入了您老人家的法眼,儿子觉着不如带在身边养活几日,全当逗个趣儿不是!”
鱼朝恩斜睨了眼自家卖力献媚的干儿子,只消一个表情便知这定又是收了利好来赚吆喝的,语气凉凉的嗤笑了声打趣儿道:
“怎幺?这小丫头莫非并不是那穆博延的乖女,而是你的种?倒是少见你这幺卖膀子力气。”
团团脸内侍却一点被揭穿的惊慌,反而熟练的一拍脑门作了个滑稽鞠躬的姿势,侧身指了指还呆立在原地有些茫然无措的尧姜,脸上笑得褶子都堆成花儿了:
“那不是看这小丫头福厚得您老人家眼缘了嘛!儿子打瞧这小姑娘头一眼,便觉得是个有福相的,红包嘛····是收了那幺一点点····”说着手上还不忘比个一小截的狡狯形容:“以往那些个不懂事的总惹您心烦,儿子每每都为此寝食难安,如今一见这真仙儿,方知之前的那些到底是底子浅薄了,方才给点子颜面就不识擡举,比不得这锦绣堆儿里养出的宝贝,又在那慧明大师座下修行多年,心性也一顶一的好····”
说着又举袖作了个滑稽的抹泪动作,配上那生动的长眉入鬓愈发显得有趣起来:
“唉,干爹也发发善心,瞧着小妮子早晚得入泥沼浮沉去的,赏段好光景,日后她也算有个念想不是····”
尧姜却似已先被逗乐了,站在藤席旁“噗呲”一声没忍住的笑出了声,对上鱼朝恩毫无情绪递过来的目光一呆,只有些欲盖弥彰的移开眼,发间的流苏也在转动间流光溢彩,耳朵却不自觉的红扑扑一片,像极了一只扑灵的小鹿,纯稚可爱极了。
“穆家这幺煞费苦心,本督要是不知趣,岂不是太不近人情了?”
话音刚落,团团脸内侍反而一惊,擡头看了眼已经举步走向尧姜的鱼朝恩,心中也不由暗叹穆家这次倒是真行了大运,居然还真成事儿了!便笑呵呵的俯身行了个跪礼,乖觉的往殿外走准备退下去传信,又被叫住:
“告诉穆博延,本督就先卖他这个好,只是,也且告诉他们穆家,人心不足蛇吞象,往后的时日尚长着呢,别拿些跳梁小丑的把戏在本督面前戏耍,都是聪明人,平白添了笑话。”
团团脸内侍恭恭敬敬的应着是便退下了,登时殿内便只余尧姜和鱼朝恩两人。
尧姜一脸淡定自若的模样显然很得鱼朝恩的心意,便又被抱起来一同坐到了一榻软椅上,手上有一下没一下的摸着尧姜颈后的骨节,滑腻肌肤的触感不由引得尧姜打了个寒颤:
“穆尧姜,小名宝儿,对吧?你瞧你阿爹丢下你了,你都不哭不闹的幺?”
尧姜只被颈后那只手弄得有些痒的耸了耸肩,仰头丝毫不避的看进那道专注的目光里,只乖顺的摇了摇头,一只手却似不自觉的捏紧了手下深黛色的衣袍一角:
“宝儿只有阿爹阿娘能叫,大人喊我阿姜就好。”
“等以后呀,便不是了。”
尧姜只迟疑的点了点头,欲言又止,却又只对鱼朝恩露出个全然无害的笑,
是精心试探的结果,看着鱼朝恩满意的愈发放柔的神色,
是了,这便是最讨眼前人欢心的姿态了。
鱼朝恩,
东厂厂督,如今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千岁爷,是目前穆家极力攀附的大树,也是阿姊密信中恨欲其死的伥鬼修罗。
此人在皇帝面前是面面俱到妥帖可靠的唯一信臣,在百官面前是兵不刃血残暴独断的皇帝鹰犬,而私底下,却像一只阴生的冷血怪物般无从揣测,阿姊这些年来也只从那些小太监的只言片语中探得此人有个养偶童的癖好,平时最是喜养些单纯良善的少男少女们,充做“偶童”,给予最好的锦绣珍宝供养,直到充足滋养的欲望逐渐显露后,再一个个毫不容情的用最狠绝的方式处理掉。
这样的一个人,要怎幺打动呢?
尧姜并不知答案,却已然跃跃欲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