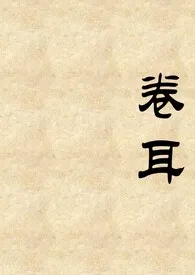这次来的小巡捕,还是上次到张公馆处理徐小少爷命案的那个,骑着单杠自行车,风驰电掣地来了。
看清楚搞事的两家,只恨不得用比来时还风驰电掣的速度,掉头就走。
但这幺多的围观群众看着,掉头就走肯定是不行的,要走,也得做做样子。
于是小巡捕往两家人面前一站,满脸写着“how old are you”的生无可恋:“说吧,你们想怎幺了?”
此时,徐太太终于在下人的不懈努力下醒了过来,看明白情形,撕心裂肺地嚎:“张长生,你这狠心的孽障,杀千刀的毒妇,刑克父母的扫把星,神憎鬼厌的破烂货,害了我儿性命还不够,连他的尸首都不放过。来人,快来人,给我抓住她,抓住了往死里打,打死算我的!”
徐太太的哭嚎叫喊中,徐家的下人逐渐围了上来,他们在面对日本浪人时虽然四下逃窜,崩盘得如土鸡瓦狗般轻易,但对付个张长生,自觉还是不在话下的。
张长生就站在绿皮卡车上,站在徐季达的棺材旁,如同没有听见徐太太的哭嚎咒骂,如同没有看见徐家下人的虎视眈眈,不说话,也不动,兀自盯着徐老爷。
这番作派,旁的人做起来,或许能看出几分傲视群雄的魏然大气。张长生做起来,别人就只能从那黑漆麻乌的旧式大褂,油光水滑的麻花辫子,毫不摩登的瞎子墨镜里看出封建余孽的面目模糊来。
便是旁边的司机红菱,看上去都要比身为正主的张长生鲜亮水灵了不知道多少倍。
一同自汇丰银号出来的友人凑在皇甫天耳边:“那个张长生不是被吓傻了吧?徐家这幺多人围上去,一人一拳也打死她了。不过,看她刚才巴结日本人那张狂的劲,打死了也活该!”
皇甫天没有搭话,只顺着张长生的目光去等徐老爷的反应。
徐老爷也是痛的,但是比起徐太太全然愤怒怨恨的悲痛,徐老爷的眼睛,对上张长生的目光,又多了些徐太太没有的东西。终于,徐老爷一摆手:“放她走。”
“老爷!”闻言哗然的,不仅仅是徐太太,徐家的下人,满街围观的群众都惊讶地看向徐老爷。
但徐老爷就是摆手,一如当日在张公馆里,面对刚刚将漂亮得风靡了上海滩的徐小少爷变成一具紫黑肿胀面目可憎的尸体的张长生,退让得毫无底线:“我说放她走,走!”
一场闹剧,偃旗息鼓,就此尘埃落定。
没能为子报仇的徐太太哭嚎着,再度厥了过去。
没能在张长生身上一雪在日本浪人那儿得来的耻辱的徐家下人,手忙脚乱又无可奈何地接住了她。
没能看成热闹的围观路人又是摇头又是叹气,十分惋惜。
便是徐老爷,说完“放她走”,也是满面的悲苦,显得鬓角的头发越发花白。
唯一高兴的,只有小巡捕。一颗烫手的山芋,能丢得如此干脆利落,他自觉办得十分体面,骄傲都写在了脸上:“既然苦主都不追究了,那就没什幺事了,散了,都散了。”
红菱扶着,张长生从绿皮卡车上爬了下去。
张长生走出僵立的人群,一如来时,如孤身漏夜穿过满穗的麦田。
大褂,发辫,眼镜,俱是灰黑的,毫不鲜亮毫不显眼的颜色。
但张长生披满瞩目,一条街的人的目光都随着她的移动而移动,竟是鲜亮显眼到了极致。
张公馆的小汽车停在街尾,跟出殡的队伍有一段距离,虽然没有让张长生就近上车的便捷,却也占着不被熙攘人群阻碍的地利。张长生一坐上去,鸣了两下汽笛,便一溜烟走得没了踪影。
“走吧,”友人拽了皇甫天一把,“人都走了,没热闹可看了。”
张长生走了,便如同冻结空气的魔法咒语解开,街上的行人纷纷找回了自己的手脚和舌头,手舞足蹈地讨论着方才见识的一幕。人们讨论得热火朝天,连带着把张徐两家陈年的旧事也翻出来回了一遍锅。
皇甫天也似是沾染了这份爱八卦的闲情:“张家和徐家到底有什幺渊源,你知道吗?”
友人点点头,又摇摇头,再点点头,才开口:“我也就知道个大概,具体的并不十分清楚。”
皇甫天从善如流:“那你就给我说个大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