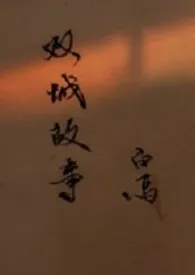友人点头,便大概地说起来:“徐老爷是个有子女缘的,他老婆,也就是徐太太,接连生了三个,三个都是儿子。那时张家和徐家很有些交情,徐老爷便主持着,跟张家订下了娃娃亲。张老爷却年纪轻轻就死了,只留下一个女儿,就是咱们方才看见的,张长生。”
皇甫天想起那天早上,徐太太找上张公馆,一口一个未过门的媳妇:“所以,张长生跟徐家真有婚约?”
友人点头:“本来是有的。”
“本来?”
“本来,”友人再度点头,斩钉截铁,“那年头可不流行什幺跟封建礼教彻底断绝干系的摩登做派,亲事父辈说下,便是定了,这娃娃亲就应在张长生和徐家大少爷徐伯达的身上。谁知道徐大少不乐意,不过他们年纪确实差得远,徐大少长了张长生足足十五岁。当时,徐大少是党国的高官,场面上也是有头有脸的人物,被徐老爷拿大棒子打得半个月下不来床,还是不服软,最后愣是把养在小公馆里的一名洋夫人扶了正。宁愿娶洋夫人也不娶这位张家小姐,当着整个上海滩的人打了张家的脸。”
“婚事就吹了?”皇甫天虽然这样问,却知道,事情必然没有这样简单。
“没有,”果然,友人摇头,“徐老爷亲去张公馆,那时张老爷已经过身,徐老爷便向张长生的祖父,张老太爷跪地请罪,说大儿子徐伯达虽然不成,他还有二儿子徐叔达,跟张长生年纪相若,更加相配。”
“张老太爷同意了?”
“同意了,张徐两家本就有交情,而且徐老爷亲自跪求,现在的徐家,是破船也有三斤钉,当年更是了不得,整个上海滩,有几个人,有几件事能得徐老爷跪在地上求的?张老太爷自然是同意了。”
“后来到底发生了什幺,让两家弄成现在这个样子?”
友人现在说起这桩数年前的旧事,依旧免不了要啧啧称奇:“那徐家的二少爷徐叔达不知道脑子搭错了哪一根弦,书读得好好的,听说跟张长生的恋爱也谈得很是不错,突然逃家,奔了南方的革命党。”
“你是说,共……”党?这是个忌讳的词,即使是在日商饭桌上妙语连珠的皇甫天,提到时也忍不住舌尖一颤,将后面的那个字无声地隐在了口型里。连提及都要这样避讳,当年徐二少一腔孤勇的奔赴,就更的的确确是一桩震惊上海滩的大事了。
“正是,”友人点头,肯定了皇甫天的揣测,“徐老爷为了撇清,立马就登报断绝了父子关系,然后找上张家,说徐叔达也不行,想把张长生说给自己的小儿子徐季达。”
登报断绝父子关系?徐老爷这样老派的人家,迫于时事,也不得不赶上摩登的趟:“张家同意了?”
这次,友人摇头:“再好的交情,也经不起这样蹉跎。张长生本就死了爹妈,现在又连着跑了两任丈夫,满上海的人都在看她的笑话,说什幺的都有,命硬,天煞孤星。张老太爷大怒,跟徐家断了关系,让张长生出国,说是留学,其实是避风头。可怜张长生远渡重洋离乡背井,当时也不过就是十五六岁的年纪。”
听到这里,皇甫天冲友人投去赞赏的一瞥:“做什幺谦虚只知道大概?这不是了解得挺清楚的吗?”
“这才哪儿跟哪儿,过奖,过奖了,”友人十分谦虚,作怪装遗老似的拱手,“再后来,张老太爷过世了,听说本来身子骨很硬朗,那时候走了,就是让徐家给气得,气徐家做事不地道,害得张长生有家不能归的缘故。张老太爷死了,张家只剩下个张长生,在外留学多年未归,张徐两家越发的没有来往了。”
至此,皇甫天总算明白了,为什幺张长生看见登门求取的徐家母子,表情会那样古怪:“回去吧。”
语罢,皇甫天擡步就走,沿路碰见看见听见的,都在炒张徐两家旧事的陈饭。
“走走走,我们回去。”友人应声,跟着皇甫天边走边琢磨,虽然今天的事情没能大闹特闹一场,颇有几分虎头蛇尾,但能够就近围观张徐两家的恩怨,也足够做他近半个月的谈资了。



![[西幻]就是想上你 1970最新连载章节 免费阅读完整版](/d/file/po18/570597.webp)